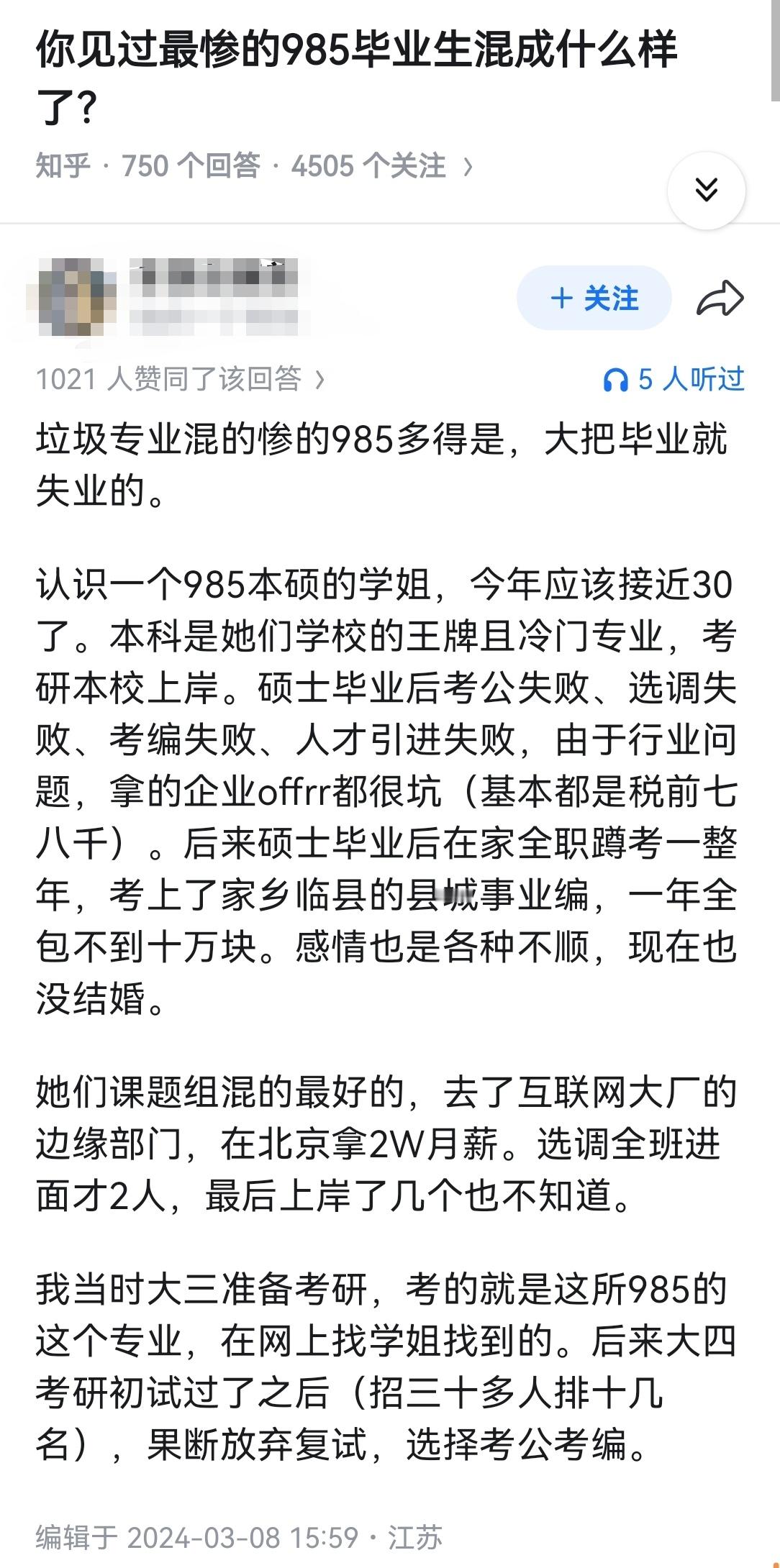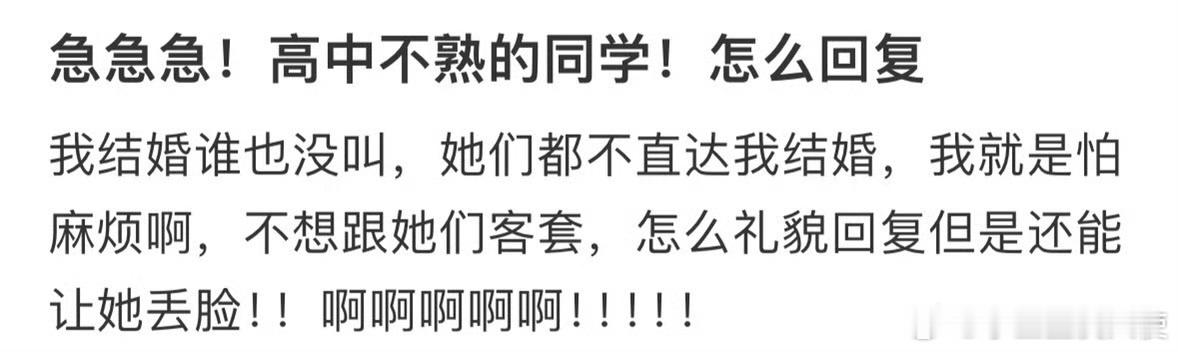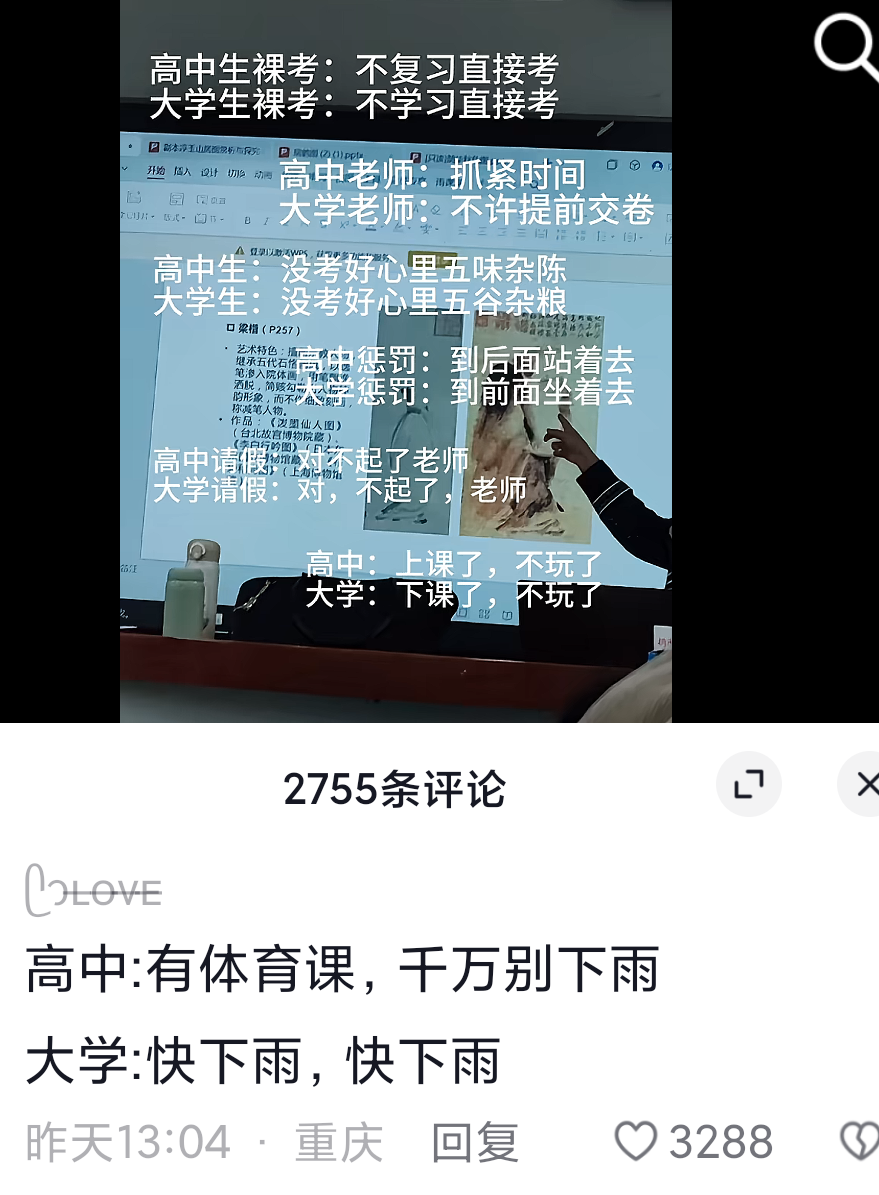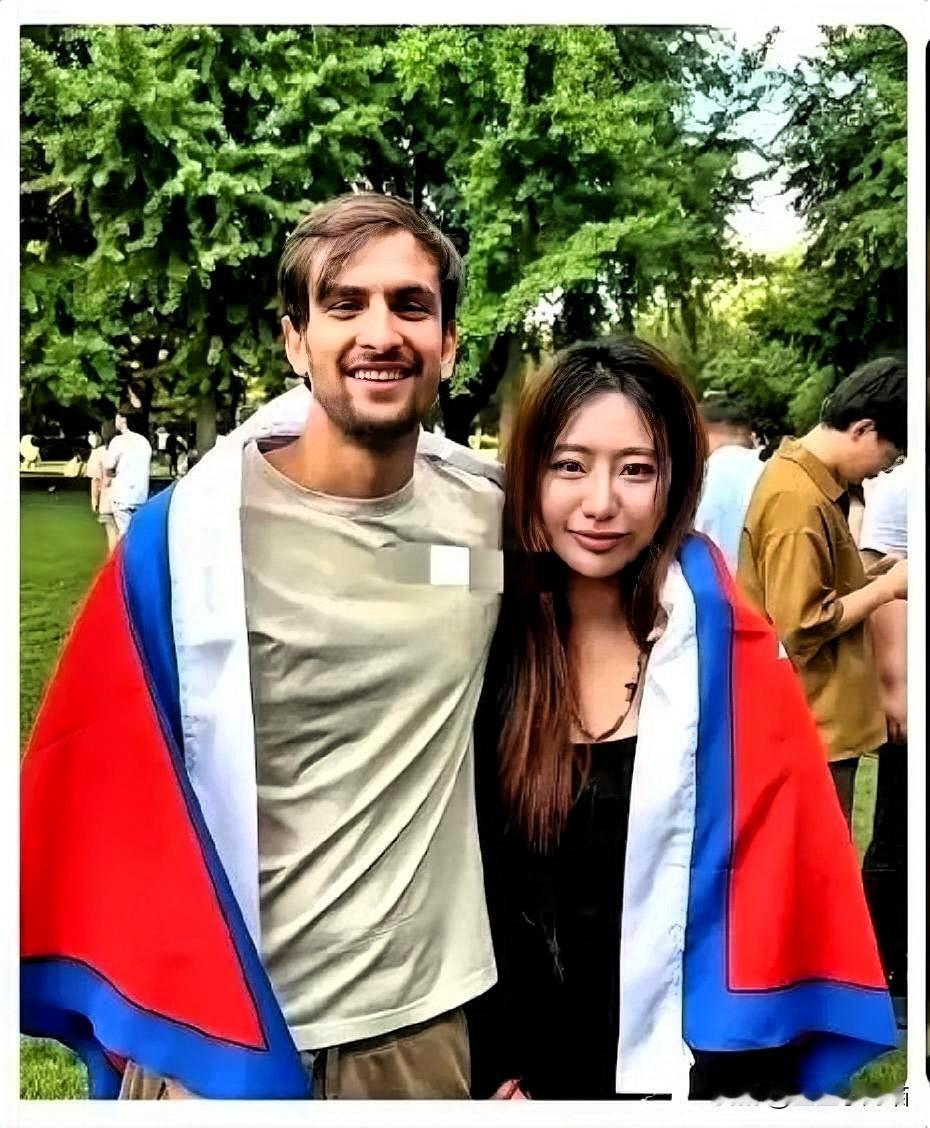已经高中毕业 40 年了,这差不多4040 年中,我一直在外地工作,颇少回老家,和当年一个班的同学全部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巧遇一个同班同学,她当即把我拉进同学群。我点开群的那一刻,眼睛先花了一下 —— 群名叫 “八五届高三(二)班永存”,后面还跟了个小红旗表情,跟当年黑板上老师写的 “冲刺高考” 四个字似的。 高中毕业四十年,我像棵被风吹远的蒲公英,扎在外地的城市里,老家的方向,一年也望不见几眼。 当年的同班同学?早散在岁月里了,连名字都像蒙了层灰,擦半天才能想起个轮廓。 去年秋天在菜市场挑白菜,弯腰时听见有人喊:“瘦猴!你是不是王建军?”我直起身,看见个头发烫成波浪卷的阿姨,手里还攥着根胡萝卜——是当年坐我前桌的李红梅,她当年扎俩麻花辫,跑起来辫子能甩到我桌子上。 她二话不说把我拽进个群,手机“叮”一响,我点开的瞬间,眼睛先酸了。 群名叫“八五届高三(二)班永存”,后面跟个小红旗表情,红得晃眼,像极了当年黑板右上角,班主任用红粉笔写的“冲刺高考”,粉笔灰簌簌往下掉,落在我们摊开的课本上。 进群头三天,我没敢说话。 看着他们聊谁家孙子刚上幼儿园,谁家在老城区买了带院子的房,谁的退休金比去年涨了两百块。有人发现在海南过冬的照片,穿花衬衫戴墨镜,底下立刻有人接:“张胖子你当年运动会跑八百米,跑一半蹲地上哭,现在倒能扛着行李满世界跑了?” 你说,四十年够不够让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的声音? 直到上周三,群里突然有人发了张泛黄的毕业照。像素糊得厉害,我放大再放大,看见最后一排角落里,有个瘦得像根豆芽的男生,穿着洗得发白的蓝校服,领口还别着个歪歪扭扭的校徽——那是我。 “这不是瘦猴吗!”李红梅立刻@我,“当年你上课偷吃辣条,被老班抓包,还嘴硬说是橡皮擦味儿的,记不记得?” 我盯着屏幕笑,眼泪却掉在手机壳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原以为四十年的风霜,早把少年时的热乎气吹散了,没想到那些藏在课桌缝里的纸条、课间抢着喝的半瓶橘子汽水、运动会上递过来的皱巴巴的纸巾,都好好收在时光的抽屉里,一拉开,还是暖烘烘的。 上周六跟当年的同桌赵磊视频,他举着手机在他家阳台转了一圈,“你看,我在这儿种了棵石榴树,跟当年学校操场边那棵一样,秋天结的果子甜得很。”我看见他眼角的皱纹,比当年笑起来的酒窝还深,他却说:“你头发白了大半,倒比当年戴眼镜装斯文时顺眼多了。” 有些联结就是这样,不管隔了多少座山、多少条河,不管岁月在脸上刻了多少道痕,只要一句“还记得吗”,就能立刻回到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 下次回老家,我跟李红梅约好了,去校门口那家老摊子吃鸡蛋灌饼,必须加双份辣条——就像当年逃课去吃时那样,辣得龇牙咧嘴,却笑得比阳光还亮。 现在手机顶端,那个带着小红旗的群名总在闪,有时是凌晨五点有人发晨练的照片,有时是半夜十二点谁分享怀旧的老歌。 这面小红旗,倒比当年黑板上的粉笔字活得久——粉笔字会被黑板擦抹掉,可这群里的热闹,这群里的人,早长进了心里,成了一辈子的暖。
已经高中毕业40年了,这差不多4040年中,我一直在外地工作,颇少回老家,
昱信简单
2025-12-22 19:51:18
0
阅读: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