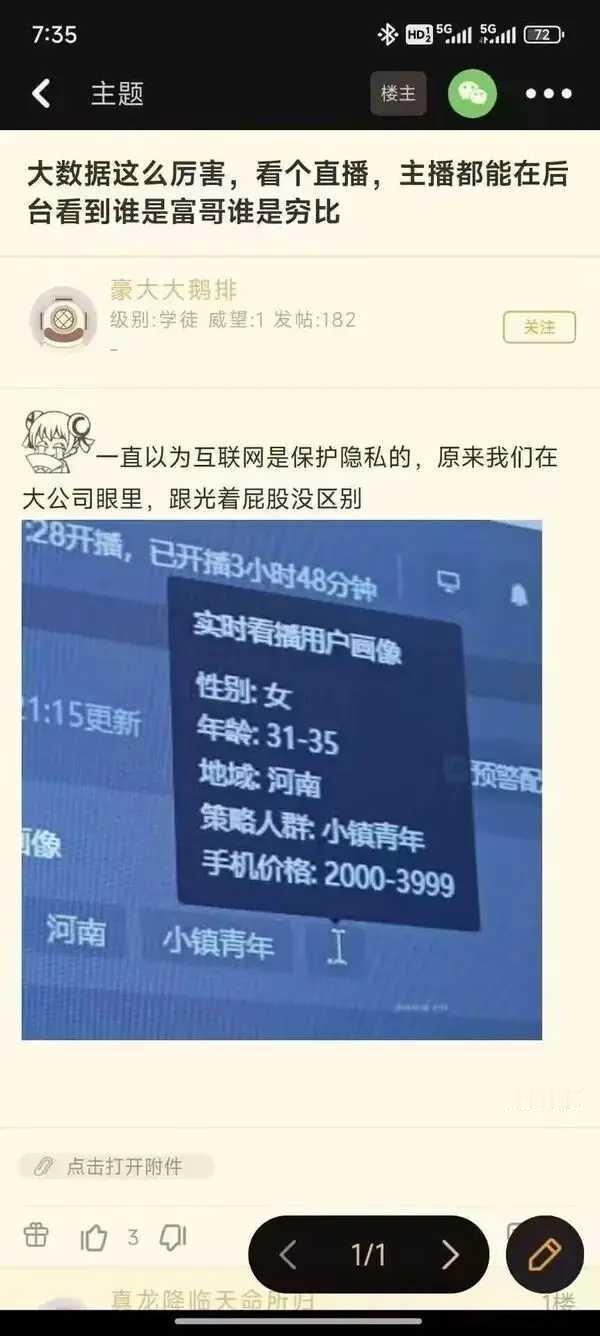下午,村里干部给我打电话了。这个干部其实也是我们家族的一个长辈。一看是他打给我的电话,我接通后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电话那头传来电流的滋滋声,夹杂着他熟悉的烟嗓:“大侄子,你有空不?回村来趟呗,咱祠堂那几棵老柏树,得找人修修了。” 下午三点,手机在裤兜里震。 掏出来看,屏幕上跳着“三叔公”三个字。 我在五金店仓库里蹲着想接,信号不好,跑到门口台阶上划开屏幕。 “喂?叔。” 电流滋滋响,像祠堂屋檐下漏雨的铁桶,混着他标志性的烟嗓——不是呛人的辣,是老旱烟特有的焦香,我仿佛能看见他靠在祠堂的木门框上,蓝布褂子沾着灰,指间的烟卷明明灭灭,烟灰积了长长一截都没弹。 “大侄子,你有空不?”他顿了顿,“回村来趟呗,咱祠堂那几棵老柏树,得找人修修了。” 我愣了愣。 三叔公是村支书,也是我亲三叔公,我爹的堂弟。小时候他总背我去祠堂玩,说那三棵柏树是明初栽的,树龄比村史还长。我爬树掏鸟窝,他就在底下喊“小心枝桠,别踩断了祖宗的念想”。 “修树?村里没人了吗?”我这话问得急,像在撇清什么——其实是心虚,我已经三年没回村了。 “有是有,”他声音低了些,“老匠人说树心空了半截,得找懂行的来,你在外面见得多,路子广……” 我捏着手机,指腹蹭过屏幕上三叔公的名字。 去年清明视频,他举着手机绕祠堂转,镜头扫过柏树时,我看见最粗那棵的树干上,有我十岁刻的歪歪扭扭的“小军”,刻得浅,被树皮盖住大半,像道快要长合的疤。当时我光顾着说城里的事,没问树怎么样了。 “我当时怎么就没听出来呢?”挂了电话,我蹲在台阶上盯着地面,仓库门口的水泥地裂了缝,长着几丛野草,跟祠堂墙根的一模一样。他说“得找人修修了”,说的是树,还是我们这些年被日子磨得生分了的亲近?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不是没年轻人,是他挨个打电话,从堂哥问到表姐,都说“忙,回不去”。他最后打给我,没说树再不修要倒,没说他上个月爬梯子够枯枝,差点摔下来——只说“你路子广”。 第二天我请了假,买了最早一班高铁。 车过长江时,我给三叔公发微信:“叔,下午到,带了城里的修树师傅,顺便……给你捎了条软中华。” 他回得快:“烟不用,你人到了就行。对了,祠堂后墙的喇叭花,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这几天开得正旺。” 我靠在车窗上笑,眼泪却下来了。 原来有些牵挂,从来不用明说——就像那几棵老柏树,根扎在土里,枝叶伸向天,而我们这些在外的人,不管走多远,只要回头,总能看见那片浓荫,在等我们回去歇脚。
刷到一个视频,看得我后背发凉。旁白就四个字:这就是命。两个小女孩,蹲在马路牙
【16评论】【8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