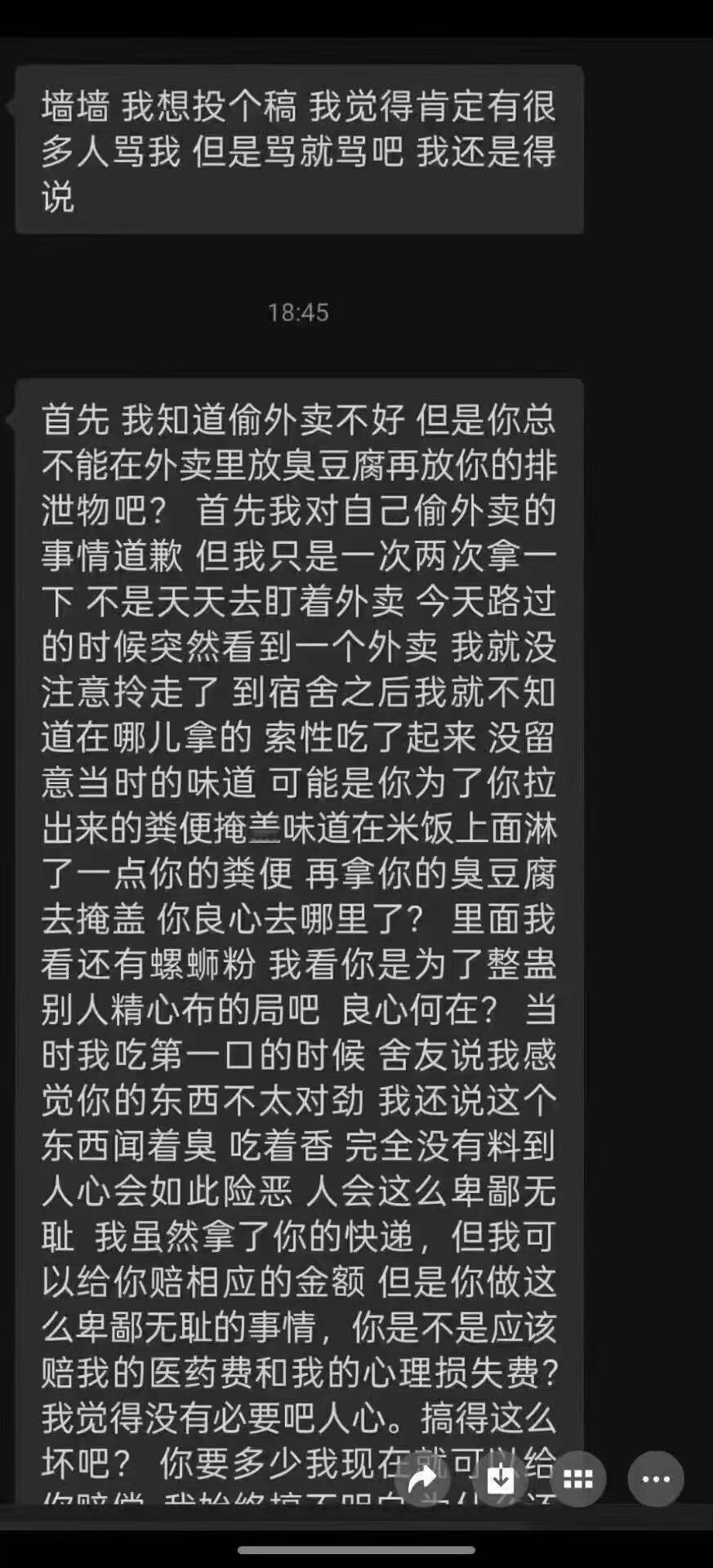1956年,92岁齐白石突然得知好友徐悲鸿已去世3年,他立刻赶到徐家。一进大门,他就弯腰下跪,吓得徐家人急忙阻拦。齐白石推开众人,大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咱们先得解开这个“迟到三年”的谜团。 1953年9月,徐悲鸿因脑溢血突发离世,年仅58岁。这在当时的文化界是个惊天噩耗。但是,所有人都达成了一个默契:绝对不能让齐白石知道。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齐白石已经90岁了,身体虽硬朗,但最怕大喜大悲。徐悲鸿对他而言,不仅仅是朋友,那是他在北京唯一的“靠山”,是他精神上的支柱。大家怕老爷子受不住这个打击,一命呜呼。 于是,徐家联合了周总理、文化部,甚至齐白石的家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保护网”。 直到1956年,或许是心灵感应,或许是有人说漏了嘴,老爷子执意要来徐家看看。这一看,看到了遗像,看到了灵位,一切都明白了。 那一刻的崩溃,不是因为被骗,而是因为痛失我爱,举世茫茫,再无知音。 咱们常说“莫逆之交”,但齐白石和徐悲鸿,原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这事儿得从1928年说起。那时候的北平画坛,讲究的是出身,是师承。齐白石是啥出身?湖南湘潭的一个老木匠。27岁才开始学画,画风大红大绿,走的是民间路子。当时的所谓“正统派”画家,根本看不起他,骂他的画是“野狐禅”,甚至有人恶毒地说他的画全是“灶火气”,登不得大雅之堂。 那时候的齐白石,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憋屈。他在诗里写:“一切画会无能加入”,甚至挂个牌子说“人骂我我也骂人”。这种孤愤,咱们现代人听着解气,但放在那个环境下,就是一个老艺术家的凄凉。 这时候,徐悲鸿出现了。 徐悲鸿是谁?留洋归来的天之骄子,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英俊潇洒,穿西装打领带。他和齐白石差了整整32岁。 按理说,徐悲鸿应该也看不上这种“土法子”画画的。但徐悲鸿偏偏有一双毒辣的眼睛。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些模仿古人、死气沉沉的“文人画”没有任何前途,而齐白石这种甚至带着泥土味儿的生命力,才是中国画改革的希望。 这就是著名的“草庐三请”。 徐悲鸿哪怕身为院长,也要放下身段,一次次跑到齐白石那个破旧的跨车胡同家里,请他去当教授。齐白石一开始不敢去啊,他说:“我一个乡巴佬,怎么能去洋学堂教书?” 徐悲鸿怎么做的?他不仅坚持请,还在齐白石去上课的时候,亲自坐着马车去接,下课了再送回来。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这给足了齐白石从未有过的尊严。 如果你以为徐悲鸿只是请齐白石教教书,那你就太小看这份交情了。徐悲鸿是在拿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在这个排外的北平画坛,硬生生给齐白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咱们讲个细节,特别真实。 当时艺术学院里那些保守派教授,联合起来排挤齐白石,说要是让一个木匠当教授,他们就集体辞职。面对这种逼宫,徐悲鸿拍了桌子。他说:“齐白石的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你们谁不服,拿作品出来比一比!” 还有一次考试,徐悲鸿出的题目是《白皮松》。这题目很有讲究,白皮松是北京特有的树。徐悲鸿这是在暗暗支持齐白石的写生风格。考试结束后,徐悲鸿把所有考卷拿给齐白石评定,齐白石说哪个好,哪个就是第一。 这叫什么?这叫绝对的信任。 在生活上,徐悲鸿更是细致得像个保姆。咱们都知道齐白石爱钱,卖画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还要算算黄金和法币的汇率。但这真不能怪老爷子,他也是穷怕了,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 徐悲鸿懂他。每次徐悲鸿帮别人求画,那是先给钱,后拿画,而且价格只高不低。 在艺术上,这俩人更是绝配。 徐悲鸿画马,讲究的是解剖结构,是西方的科学写实;齐白石画虾,讲究的是水墨意趣,是东方的神韵。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他们都痛恨那种死临摹、没灵魂的画法。 齐白石有一首诗,是专门写给徐悲鸿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什么意思?就算全天下有一万张嘴在骂我的画法,但只要有一个徐悲鸿懂我,哪怕把胆掏出来给他,我也愿意! 徐悲鸿在给齐白石画集的序言里,直接把齐白石捧上了天。他说齐白石是“致广大、尽精微”,把那些嘲笑齐白石粗俗的人驳斥得体无完肤。 要知道,当时徐悲鸿推崇的画家很多,但能让他如此毫无保留、甚至带有崇拜色彩去推广的,唯独齐白石一人。 说回到1956年的那一跪。 当齐白石站在徐悲鸿的遗像前,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朋友,而是那个在他最落魄时拉他一把的人,是那个在他被围攻时挺身而出的人,是那个真正读懂他灵魂深处孤傲的人。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 这句话,改自管仲和鲍叔牙的典故。但在那一刻,从这位92岁的老人口中喊出来,分量比千金还重。 那天之后,齐白石的精神头明显垮了。因为他知道,这世上再也没有那个坐着马车、笑着喊他“白石翁”的人了。一年之后,1957年,齐白石也追随老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