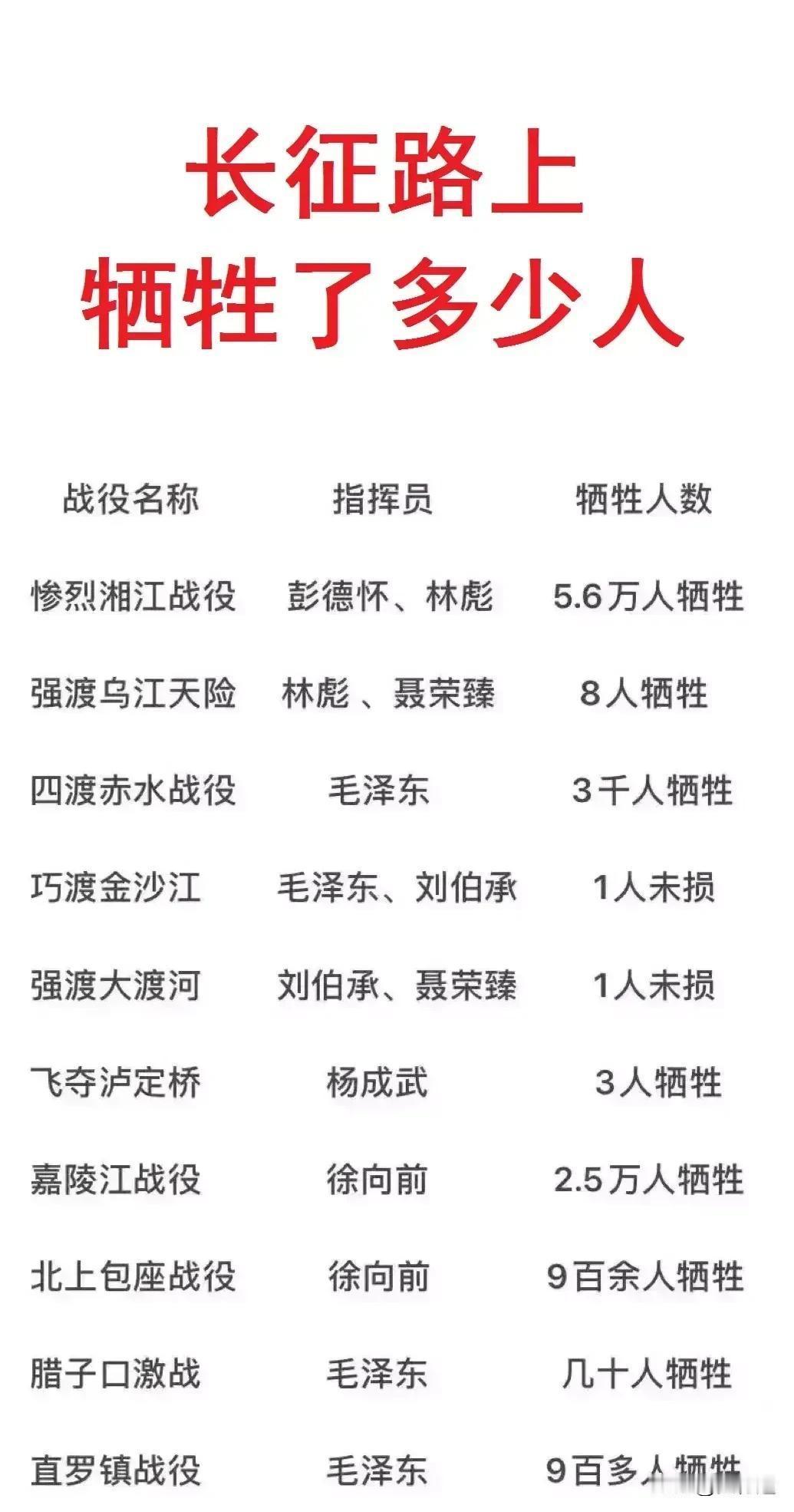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一九六〇年,英国老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主席,夸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摆摆手,说那几仗算不了什么,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外人看见的是大城市、大会战,在他心里,几万红军在山沟和河谷里拧出来的一条活路,更值一声点头。 时间拧回一九三五年春天,乌江边的风又冷又硬。 三月三十一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口、大塘、梯子岩一带南渡乌江,河面漆黑,船在水里打晃,北岸山坡上,摆着蒋介石亲手织起的重围:正规军近四十万,加上各地民团凑出七十万人,按地图推演,是要在这里把这支三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压扁。 天亮后,红军已经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地乱糟糟的脚印。 要走到这一步,前头每一脚都踩得发虚。遵义刚拿下,蒋介石就调来一百四十八个团,企图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一口吃掉中央红军。红军这边,底牌摊出来也就那点儿:三万七千出头,对上几十万围追堵截,谁都明白天平往哪边倾斜。 土城那一仗,把这种悬殊敲得特别响。 正月里,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赶到土城,前线来的数字说,尾追的川军只有两个旅四个团,青杠坡地形顺手,干掉郭勋祺这一股,渡江路就能松一口气。 朱德亲自盯红三军团前卫师,刘伯承守红五军团,一月二十八日清早,山坡上火光乱窜,红军顶了三四个小时,确实把对面打疼。局势翻脸也快,川军增援像涨水一样往上灌,红五军团阵地被撕开口子,白马山高地落到敌人手里,枪声压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朱德带着几个军团连番反击,好不容易把阵地稳住。 毛主席盯着地图算数,发现尾追的不是四个团六千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同红军投入兵力差不多,这仗再恋战,后面那张四十万的大网就真要合拢。 土城附近那次紧急碰头,其实就是一场“掉头会”。 毛主席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叫到一起,当面把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合上,换成一条新路:趁红军还没被咬死,从土城、猿猴场、太平渡一线撤出火线,西渡赤水,经古蔺、叙永往北挪,再去金沙江边找渡口,设法和川西、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搭上手。 一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分批渡过赤水河,一渡算是开局。 红军身影一出现在川南,重庆那边电报机就跟打雷似的。蒋介石命长江沿岸赶筑工事,从滩头到宜宾、江津一溜碉堡钉在山上,军舰、装甲商船在江面来回晃,又叫潘文华在南岸布防,孙渡、周浑元、王家烈、吴奇伟带着各路人马,从毕节、昭通、修文、桐梓一圈压过来,企图把中央红军围在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那块夹角里。 二月七日,中央干脆把北渡长江的念头按下,定下在川黔滇边打运动战的主意,不久又发出《告全体红军战士书》,把规矩讲得明白: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只认一点,在合适的时候把仗打赢。 二月十八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东渡赤水,算是二渡。 红一军团抽出一个团往古蔺方向晃,故意放出“打过长江去”的风声,川军南下脚步慢了半拍,主力掉头扑向黔北,横扫一千一百里,桐梓拿到手,娄山关这个老关口再次换上红旗,遵义城再度易主,两个师八个团被打得七零八落。 三月初,他发通令,把驻川、驻黔各军都收在自己手里,又在行营里摊开地图,口口声声“一揽子计划”,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老路,用堡垒推进、重点进攻,把红军挤死在乌江西边、川黔大道以东那一片山地。 部署铺开,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吴奇伟,还有第五十三师、湘军各师分占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金沙、土城、乌江沿岸和石阡等要地,看上去只差一把劲就能把红军按住。 三月十五日,红军在鲁班场发动总攻,周浑元汲取教训,把部队缩在碉堡里不肯出来,大仗打不成,歼敌机会也不肯露头。 这时候,四渡赤水那口气已经在心里憋足。 蒋介石最怕红军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就偏在这个方向上做文章。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茅台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旗帜和号声都摆在明处,白天过河,做足了要北渡长江的样子,消息飞回重庆,大批部队被拖向西岸。 等到对面被引得差不多,三月二十一日,主力再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东渡赤水,第四次上岸,重回黔北,红九军团在金沙县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扮作“主力”,三天两头点火、集合、出动,把不少敌军晃了过去。 真正的中央红军顺着遵义、仁怀大道一路向南,穿过鸭溪、白腊坎的封锁,连夜往乌江边急行军,才有了三月三十一日那场黑水里的渡江。 再看这一串脚印,一边是蒋介石握着几十万兵力,在重庆对着地图画圈圈,堡垒推进、纵队番号排得密密麻麻;另一边是毛主席带着三万七千来人,在赤水河畔、乌江两岸一次次掉头,把对方的圈一圈圈拆开。 说他“用兵如神”,说的不是神话,而是在最难的时候敢拐弯,在最凶的包围里敢算细账,这种本事,很难说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