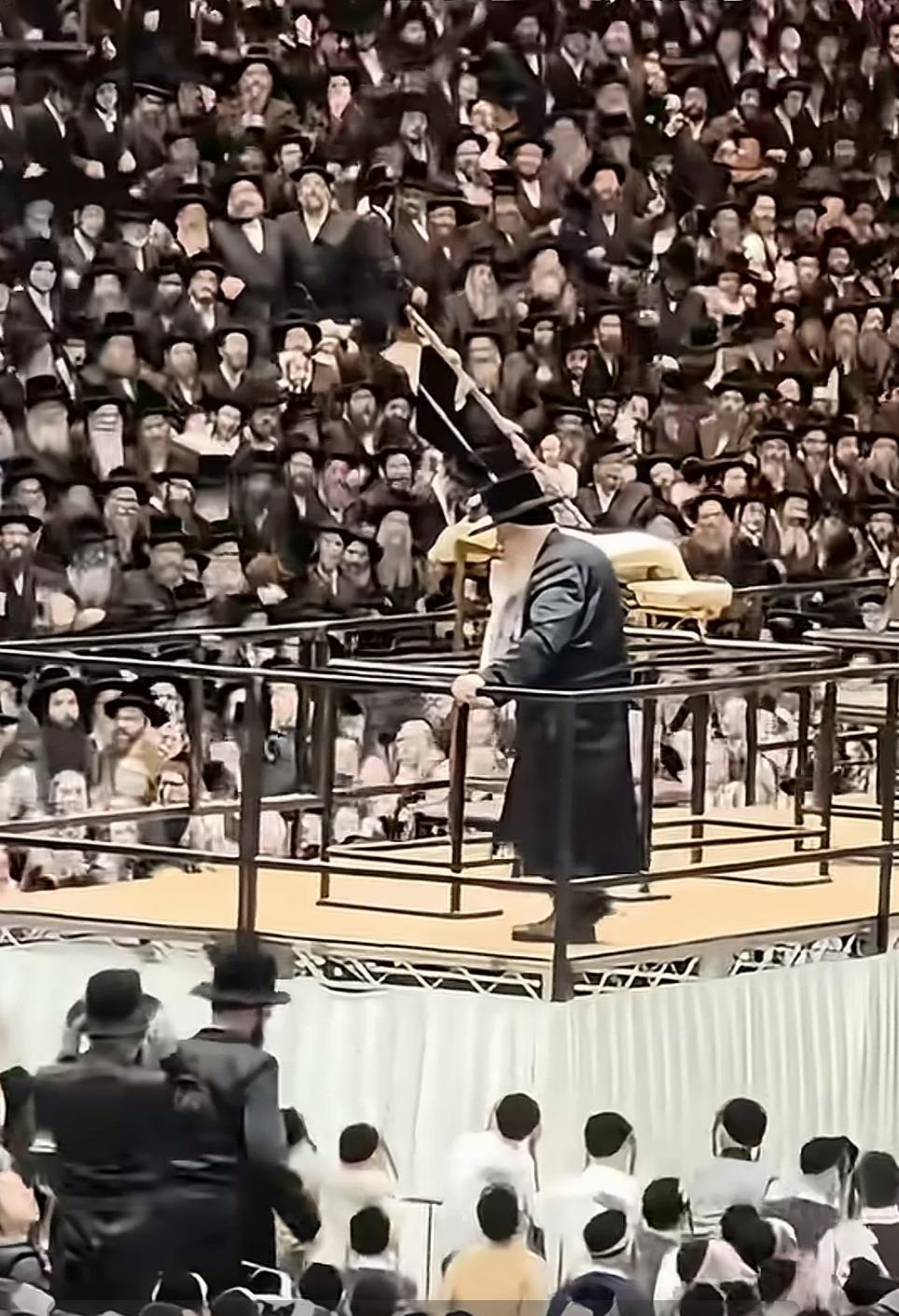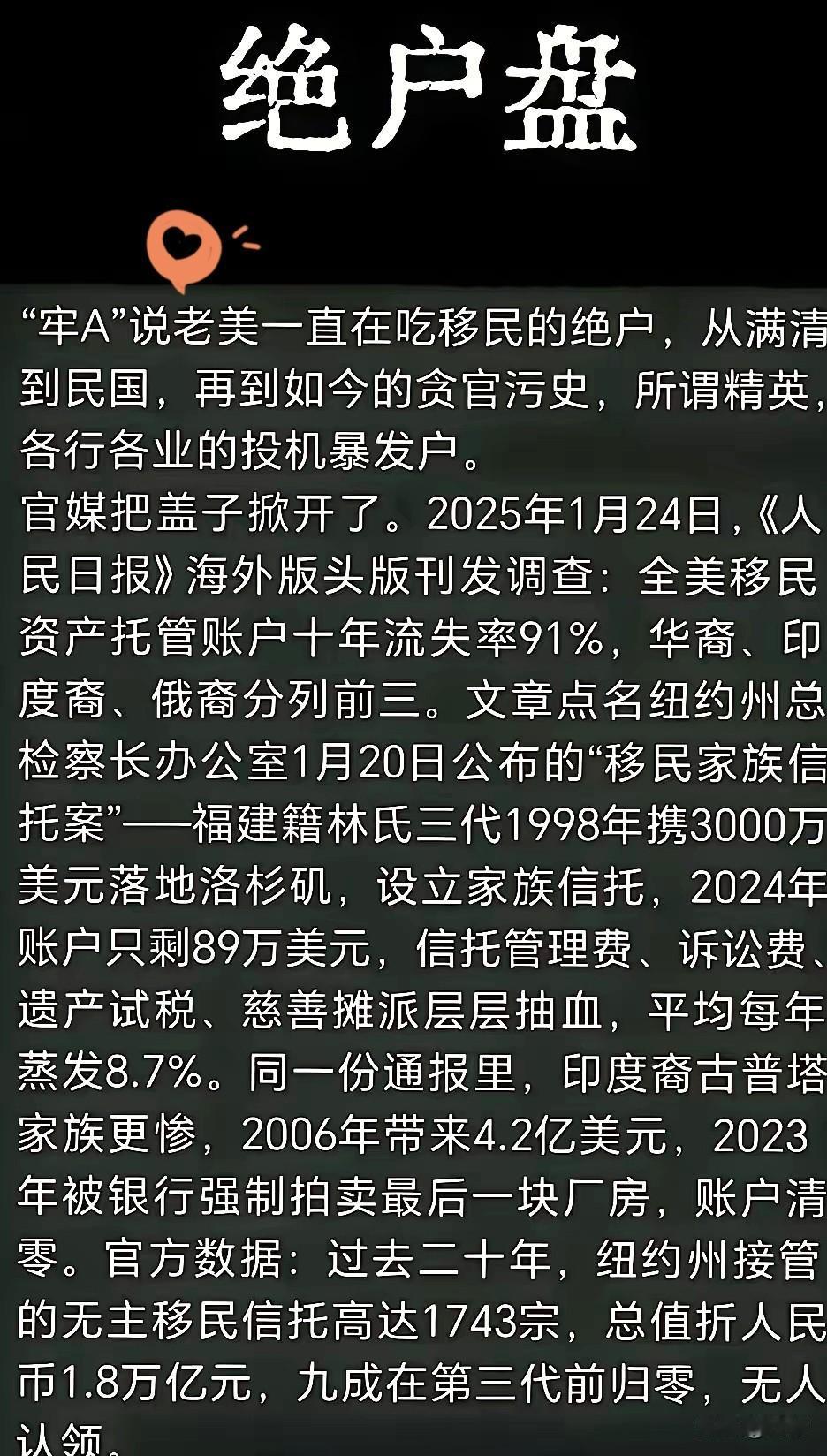1626年后,有50万名黑人被卖到美国做黑奴,女黑奴被迫和奴隶主发生关系后,生下的孩子也是奴隶,奴隶主根本不会承认这些孩子,就算有的私生子长得很白,甚至和白人无异,他们也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直到现代,一份DNA报告寄到普通美国家庭的信箱,才发现白人男子,祖上赫然有非洲血统。 这事搁两百年前,放在南方哪个大庄园里,如果逃不脱那部脏兮兮的法律,这位看起来白到发光的“先生”,祖母可能就是棉花地里被拖出去的一个女孩。 在几百年的混血之中,肤色可以消失,但身份不会。 因为生来是奴隶,死后才有名字。 这是一道长期压在人性上的公式:黑人女性和白人奴隶主生下的孩子仍为奴,姓什么不重要,永远没资格站在前排。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切从1662年那条法律开始有迹可循。 当时的弗吉尼亚,白男与黑女的“不可说之事”越来越频繁,本该尴尬的局面,却被写进了殖民地的法典。 他们抛弃了英国那套孩子随父姓的规矩,抄起了一条老掉牙的罗马法:孩子是谁生的,就跟谁走。 如果母亲是奴隶,那孩子一出生也就是了。这下好,奴隶主不但可以“合法”占有女奴,连对后代都直接省心,不用吵身份、争继承,把人当牲口,连账都算得刚刚好。 而这种玩法雷厉风行。不光弗吉尼亚搞,1671年马里兰也紧随其后,外加一条狠的:哪怕是自由白女,碰上黑奴也不行,孩子照样脱不了身。 从这以后,生孩子在奴隶制度里就成了一门生意,女奴青春的身体,是钱袋的底色。 1808年,美国对海外奴隶贸易画了句号,但这根藤却长出了更阴暗的果。 那些“上南方”的州,比如弗吉尼亚,摇身变成南方种植园的“人肉供应链”。不再靠船运黑人,他们干脆用女奴“自产自销”。 年纪轻的漂亮些的女奴,价格翻上去,种植园主一边打算盘,一边关起门强迫她们生孩子,还美其名曰“提高繁育率”。 一些记录干脆赤裸地讲,把女奴当“母牛”对待,还说什么“奖励布料”,听着一点不比牲畜市场高明。 真正令人发冷的,是那些账簿上光鲜的“入账”明细,其实是隐喻着侵犯的痕迹。 当时的植棉经济要生得快、活得久、干得动的人。女奴悔不掉,孩子逃不了,一条命能拆出几根棉线,全靠庄园主算盘打得响。 那些孩子也不是没想过逃。 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托马斯·杰斐逊和萨莉·海明斯。 他是美国总统,她是他的女奴,还是他妻子的同父异母妹妹。他们的孩子至少有六个,其中几个皮肤白得像乡下教堂合唱团的首席。 可就算这样,他们仍是奴隶。他们的父亲不在族谱上,他们的存在成了家族羞耻。 长子贝弗利、女儿哈丽雅特,在杰斐逊临终前偷偷离开庄园,一边逃一边学会在白人社会中“伪装”成白人。没错,“当白人”要偷偷进行,还不能被发现“有一滴非洲的血”。 这个“一滴血规则”,是后来奴隶制废除后,被“合法”沿用的社会分类武器。你祖上只要有一丁点黑人血统,那你就是“有色人种”,再白都没用。 但令人讽刺的是,这种对血统的“神秘检测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全凭恐惧驱使社会立法。 一项1903年的条例还明确表示,可以忽略掉印第安血统,最多到1/16都不当回事,但黑人呢,连一滴都容不下。 美国社会就像一台精密的筛子,过滤着那些“长得不够白、血统不够纯”的人,让他们一代代掉到底层。 而那些长得够白躲过筛子的人,连回头认祖归宗都成了个笑话。 2022年的研究显示,现代非裔美国人平均有24%的欧洲血统。 这数据是过去几百年那些“非自愿同床共枕”的直接证词。 很多家庭查完家谱后,发现曾祖母其实是白人庄园主的“隐秘女人”,身份证上叫“无名氏”,墓碑上连姓氏都没有。 而到了今天,黑人家庭常常卡在追查1870年之前的那一栏,因为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人口普查中给黑人全名登记。在那之前,再多的故事都只剩一句话:“某某的母亲是奴隶。” 就是这条线,隔开了“有没有根”的人。 2019年,蒙蒂塞洛庄园举办了一场相当罕见的纪念仪式,正式承认萨莉·海明斯的后代。在那草坪上,几百名混血后人第一次堂堂正正地站在“家族”的位置。 这算堪称历史的一次修补吗?从某个角度看,是。但更多未被承认的名字,仍沉在记录之外。 从1662年的“血随母走”,到“繁殖当买卖”,再到“一滴血就打回原形”,美国社会的底色被层层刷成了不容混淆的种族隔离。 那50万人,是个数字。 但在母亲、孩子、皮肤、名字这些词中交错的人生,是几十万段被撕掉的家谱,是在权力、法律、经济结构合谋下,维持了几百年的沉默链条。 信息来源:《弗吉尼亚殖民地法典》《美国种族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