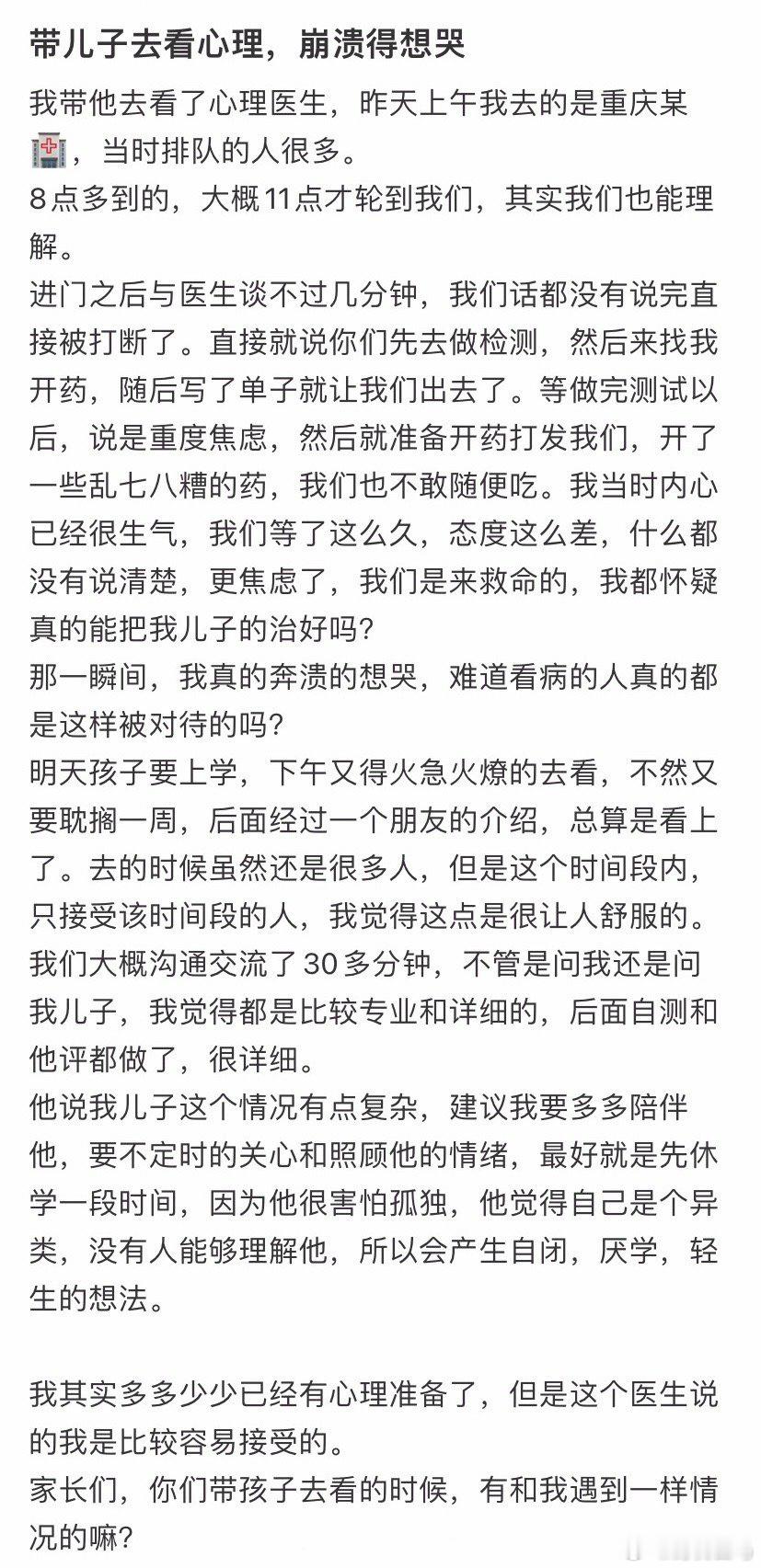我侄女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她说:监护室的病人,多数都没有清醒的意识,浑身插满管子,偶尔有清醒的时候,每天听着嘀嗒嘀嗒仪器的声音,也会让人窒息。每次跟侄女视频,她眼底的红血丝都藏不住。 我侄女在ICU当护士,三年了。 每次视频,她都坐在护士站的角落,背后是永远亮着的白炽灯,把她眼底的红血丝照得清清楚楚——像没擦干净的水彩,晕在眼白上。 她总说监护室的空气里永远飘着两样东西:消毒水的清苦,和仪器的嘀嗒声,一声接一声,敲在人的心尖上,久了连呼吸都跟着发紧。 病人多数没清醒意识,浑身插满管子,偶尔睁眼,就那么盯着天花板看,看很久很久,久到你以为他们在数仪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其实后来她才知道,有个奶奶是在想“阳台的茉莉该浇水了”。 “你说,人在最虚弱的时候,是不是反而能抓住最实在的东西?”有次视频她突然问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护士服袖口,那里沾着点没洗干净的药水渍。 我还没答,她就自己笑了,说上周三夜班,12床爷爷突然醒了,迷迷糊糊抓着她的手,捏了捏,又捏了捏,像小朋友攥着舍不得吃的糖。 “他没说话,就捏了捏,可我知道,他是说‘谢谢你啊’。”她眼里的红血丝还在,却比往日亮了些,像揉进了碎星星。 外人总说ICU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她却摇头,说这里其实最容易撞见“活着”的证据:3床阿姨醒了会哼年轻时的歌,跑调跑得厉害,可旁边床的大爷居然跟着打拍子;7床爷爷无意识抓着她的白大褂角,手背上的针眼还在渗血,指节却攥得发白,后来家属说他年轻时总这样牵老伴儿过马路。 她抽屉里永远备着润眼液,却总忘了用——抢救时要盯着监护仪上的曲线,换药时要核对三遍姓名床号,连吃饭都得竖着耳朵听仪器的动静,哪有空揉眼睛。 有次我心疼,说“要不换个轻松点的科室?”,她正往保温杯里倒热水,闻言动作顿了顿,杯沿的热气熏得她眨了眨眼,红血丝更明显了:“可这里的人,更需要人牵着啊。” 那天之后我再没提过换工作的事。 有些累,是因为托着别人的希望在走。 前几天视频,她突然把手机举高了些,镜头里映出她的手腕——贴着块卡通创可贴,是粉色的小兔子。 “今早5床小姑娘醒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非要把这个给我,说‘护士姐姐戴这个,眼睛就不疼了’。”她边说边笑,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比背后的白炽灯还暖。 我看着她眼底的红血丝,突然觉得那不是疲惫的痕迹,是无数个“活着”的瞬间,在她眼里刻下的温柔印记。 挂了视频,我翻出购物车囤了三支她常用的薄荷护手霜——听说薄荷味能提神,下次见面给她,顺便告诉她,我家阳台的茉莉开了,香得很,等她休息,带她来闻闻。 毕竟,能让她在消毒水味里,撞见点甜,也挺好。
带儿子去看心理,崩溃得想哭医生禁止把玩患者
【20评论】【4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