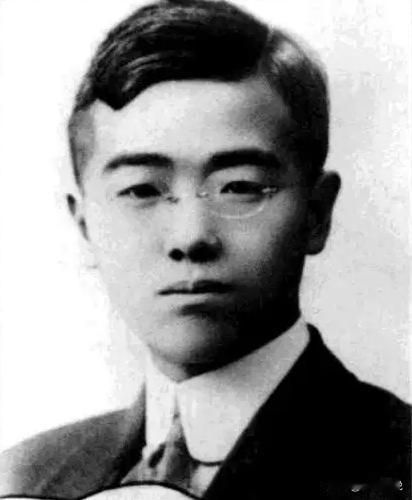1966年8月,大庆油田发现者谢家荣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在睡梦中离世,第二天,妻子吴镜侬在他身边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短短十个字令人泪目。 1966 年秋,谢家荣夫妇离世后,子女在遗物里发现一筒阿胶和五个木箱。 阿胶是吴镜侬留给女儿补身体的,木箱贴着子女名字,装着旧物当念想。 没人想到,这些温柔的遗物背后,是改变中国 “贫油” 命运的地质传奇。 谢家荣用 “陆相生油” 理论找油,吴镜侬用一生撑起他的科研后盾。 在南京地质博物馆的展柜里,放着一本泛黄的野外勘探笔记,扉页有谢家荣的字迹。 “1923 年,玉门戈壁,水尽粮绝,得牧民赠奶,始抵油苗区。” 寥寥数语藏着艰辛。 这是他独自勘查玉门石油时的记录,当时他背着几十斤设备,徒步穿越无人区。 白天在烈日下测绘岩层,夜晚借篝火整理数据,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 正是这次勘查,他发现玉门油苗的独特地质结构,推翻 “西北无大油” 的说法。 1924 年,他在《地质汇报》发表补充报告,详细标注油苗分布与储油层特征。 这份报告后来被玉门油田开发团队反复翻阅,成为钻井选址的重要依据。 鲜少有人知道,为获取准确数据,他曾冒着塌方风险,下到 30 米深的探井观察。 1935 年,谢家荣在淮南考察时,发现八公山一带的岩层有特殊反光。 他蹲在山坡上连续三天观察岩层走向,用放大镜辨认矿物颗粒,最终确定是煤层。 当时国内煤炭紧缺,他立刻组织当地村民用简易工具试挖,果然挖出优质无烟煤。 随后他绘制详细煤田分布图,推动淮南煤矿开工,缓解华东地区用煤紧张。 抗战期间,科研条件极其艰苦,谢家荣的 “陆相生油” 理论研究一度停滞。 实验室被炸毁,珍贵的地质标本只能装在木箱里,跟着他辗转多地。 吴镜侬就用粗布把标本箱裹起来,怕颠簸损坏,搬运行李时总把箱子抱在怀里。 在云南避难时,没有电灯,谢家荣就借着煤油灯写论文,吴镜侬在旁缝补衣物陪他。 1947 年,谢家荣在福建漳浦考察时,发现当地土壤呈红褐色,且比重异常。 他取样带回实验室分析,反复测试后确定是铝土矿,且储量可观。 当时中国铝工业刚起步,几乎全靠进口铝土矿,这个发现意义重大。 他立刻撰写报告上报,却因战乱未能及时开发,直到 1953 年才启动开采。 1956 年,谢家荣带队前往松辽平原踏勘,当时不少国外专家认为这里无油。 他顶着质疑,带领团队用 “重力勘探法” 测量地下岩层密度,寻找储油圈闭。 白天在零下 20 度的野外布设测线,仪器冻得失灵,就用体温焐热再测。 夜晚在简陋的帐篷里计算数据,他发明的 “分层对比法”,大幅提高找油效率。 吴镜侬此时在后方忙着为团队准备物资,知道东北寒冷,就发动家属缝棉衣。 她还特意把谢家荣的降压药分成小份,装在防水袋里,怕在野外受潮失效。 有次团队断粮,她托人辗转把馒头和咸菜送到前线,自己在家却吃红薯充饥。 谢家荣后来在日记里写:“无镜侬,吾难成一事。” 1959 年,大庆油田第一口井出油的消息传来,谢家荣正在医院养病。 他拿着报纸激动得手发抖,让家人读了一遍又一遍,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这口井的选址,正是基于他当年在松辽平原绘制的地质剖面图。 他多年的理论终于落地,中国从此不用再依赖 “洋油”。 谢家荣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总说 “是团队的力量,是国家的支持”。 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把珍藏的 200 多件地质标本捐赠给地质院校,供学生学习。 还经常去学校讲课,用自己的勘探经历,鼓励学生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吴镜侬就帮他整理讲课笔记,把复杂的地质术语改成通俗的语言。 1966 年,谢家荣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开始整理毕生科研资料。 他把 “陆相生油” 理论的补充手稿交给学生,叮嘱 “要继续完善,为国找更多油”。 吴镜侬看他身体虚弱,就每天熬汤药,陪他一起整理资料到深夜。 离世前一晚,他还在修改松辽平原地质报告的批注,希望能帮到后续勘探。 吴镜侬在谢家荣身旁发现空安眠药瓶时,指尖先触到一张叠得整齐的字条。 展开泛黄的纸,“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十个字,让她瞬间红了眼眶。 如今,谢家荣捐赠的地质标本仍在滋养着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大庆油田的展览馆里,专门设有 “谢家荣与陆相生油理论” 展区,播放他的事迹。 他的孙子谢明是地质工程师,经常带着爷爷的勘探笔记去野外,传承科研精神。 谢家荣夫妇虽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像地下的石油与矿产,永远滋养着祖国大地。 信源:面对不敢面对的历史 ——缅怀“文革”中被逼自尽的地质学家——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