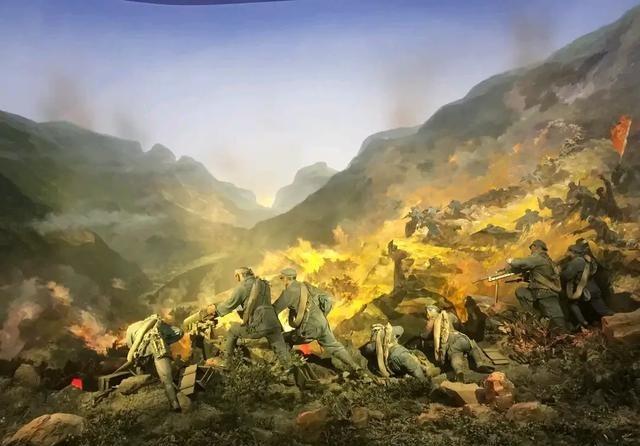吴亮平问毛泽东:“像瞿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的摆布?” 毛泽东说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吴亮平又去问张闻天,张闻天说,这是中央局决定的,他一个人做不了主。 吴亮平是在苏联学习时与瞿秋白成为好朋友的,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转移。 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了随主力转移和被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瞿秋白被留下。 瞿秋白是谁?他可不是一般干部。他是党早期的总书记,一个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理论家、文学家。按理说,这样的人才,走到哪儿都是宝贝,怎么就成了被“优化”掉的对象? 表面上的理由很充分:瞿秋白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身体垮了,根本撑不住长途跋涉的苦。这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让人没法反驳。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恰恰是为了掩盖桌子底下的真正原因。 要理解瞿秋白为什么被留下,就得明白当时中央苏区那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那时候,说了算的不是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而是从苏联回来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推行的是一套“左”倾路线,打仗讲究“正规战”,要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堡垒战。 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一败涂地,中央苏区从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被压缩到只剩下瑞金周边几个地方。 毛泽东因为反对这套打法,早就被排挤出了军事决策核心。他和张闻天当时都住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一座叫“云山古寺”的小庙里。两个失意的人,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坐在一棵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天。他们聊的,全是心里的憋屈和对前途的担忧。张闻天甚至跟毛泽东坦白,他感觉自己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已经被架空,“处于无权的地位”。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决定谁走谁留的名单,成了一次权力的筛选。说白了,带走的,是“自己人”;留下的,自然就是那些不被信任,或者说,在政治上“不合拍”的人。 瞿秋白恰恰就属于后者。他虽然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他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后来又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格格不入。他在中央苏区实际上也是被边缘化的。在博古他们看来,瞿秋白这样一个文人,思想上跟自己有分歧,身体又不好,带上他,既是个累赘,又可能是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当张闻天同情瞿秋白,亲自去找博古求情时,博古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口就回绝了。 这就是当时残酷的现实:你的价值,不是由你的才能决定的,而是由手握权力的人对你的观感决定的。 做出这个决定,对瞿秋白本人意味着什么?他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留下,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苏区就那么大点地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得跟铁桶一样,主力红军一走,留守部队根本挡不住。 被俘,只是时间问题。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多余的话》,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坦诚甚至有些残酷的剖析。他说自己本质上只是一个“文人”,一个“半吊子”的政治家,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年仅36岁。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个背影,定格在了一张照片上:身着中式对襟白褂,黑色长裤,背着双手,平静地走向刑场。那份从容,至今看来,依然让人动容。 我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心里五味杂陈。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指责博古或者李德冷酷无情。在那个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关系到整个队伍的生死存亡。从他们的角度看,放弃一个病人,保全大部队的机动性,或许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但历史的评价,从来不只看动机,更看结果和人心。 这个决定,让中国革命永远失去了一位卓越的理论家和文化旗手。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当时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一个正确的决定,需要一个健康的决策机制。当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人,当不同意见被压制,当人情和同志友谊在冰冷的“组织原则”面前不堪一击时,悲剧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好在,历史有它自己的纠错能力。仅仅三个月后,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那种“不顶事”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毛泽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那条差点把红军带入绝境的“左”倾路线被终结。 只是,瞿秋白再也看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