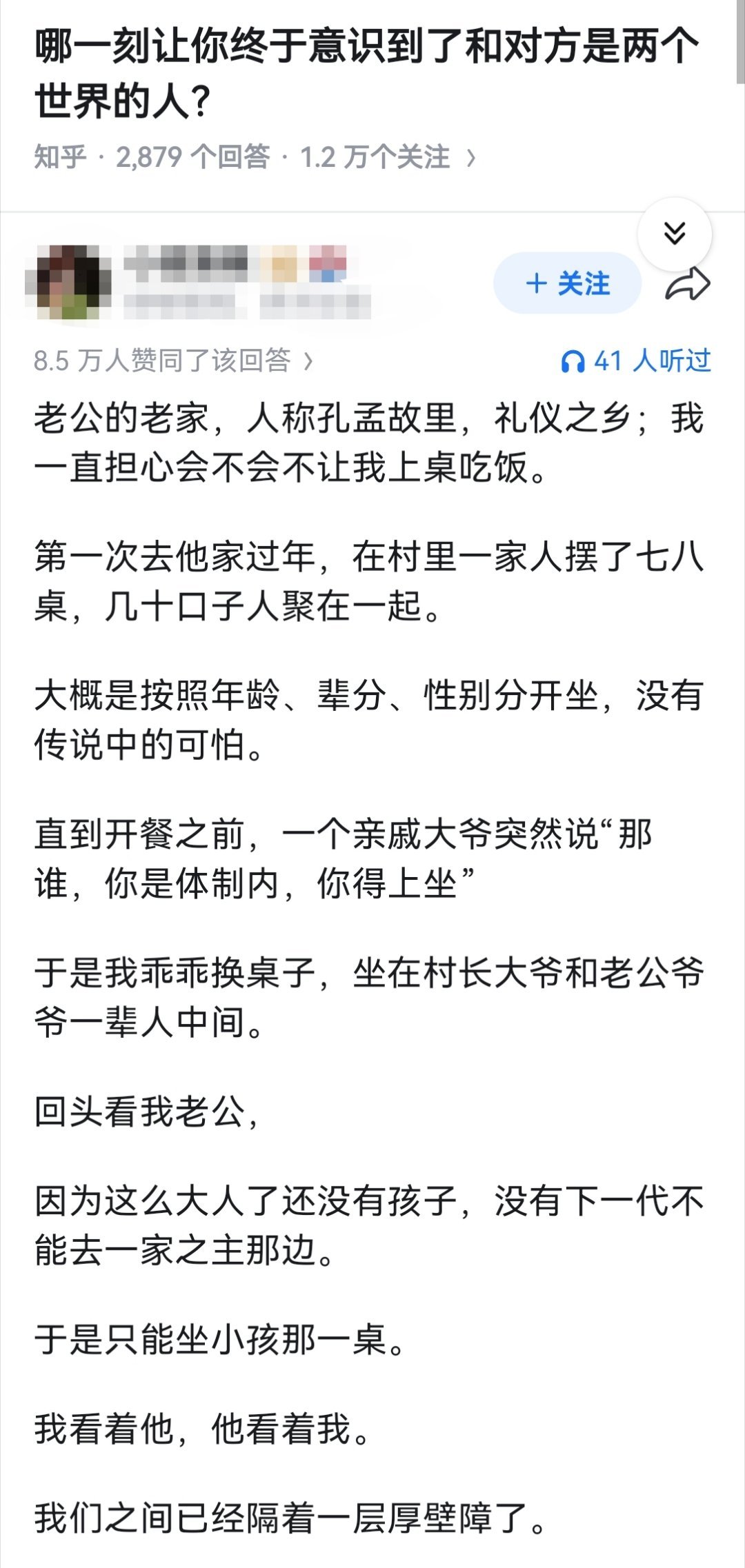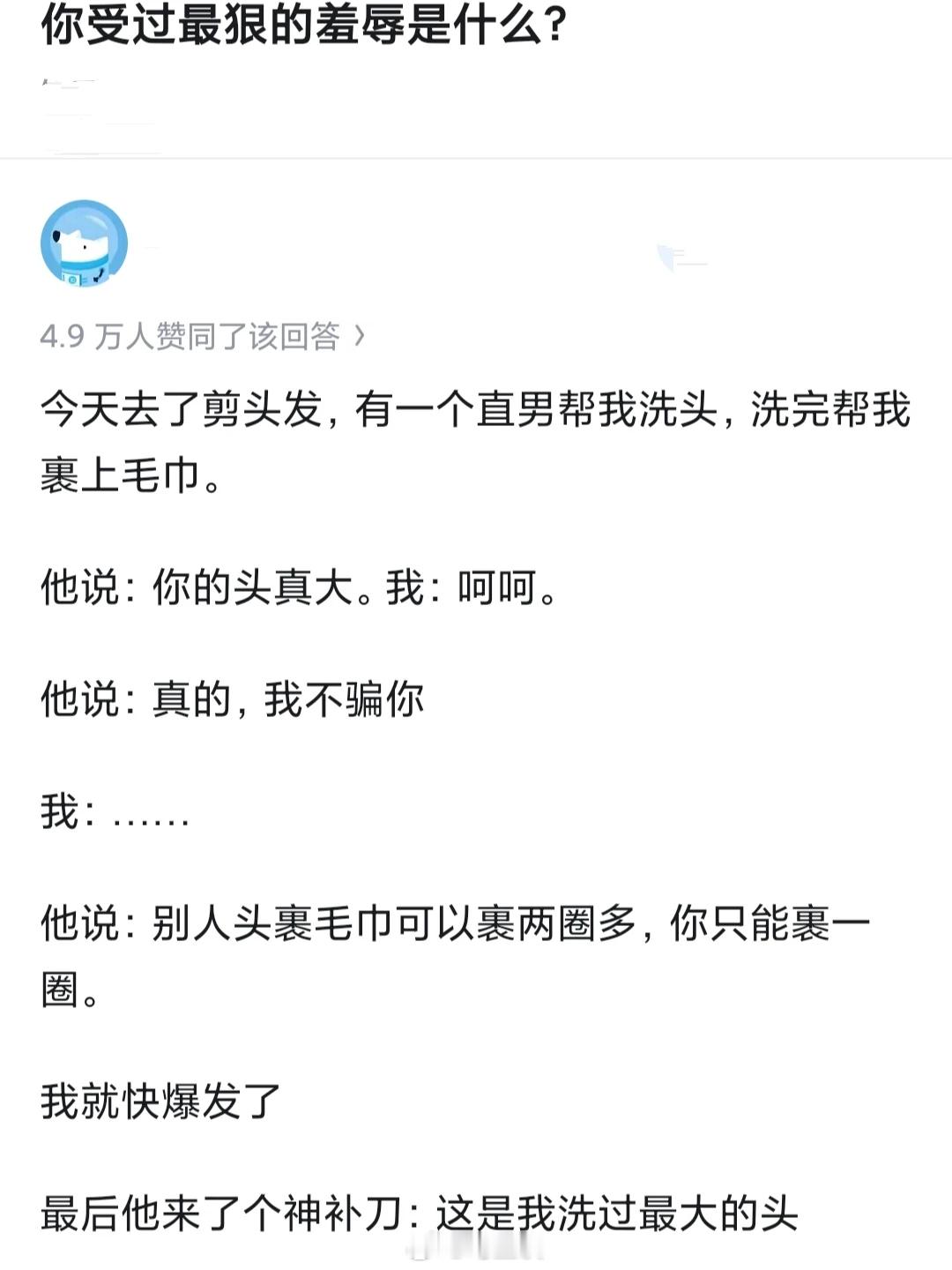[微风]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朱梅馥这个名字,其实是傅雷给改的,她原名“梅福”,1913年阴历元月十五生在腊梅盛开的院落里,父母盼她有福气,但傅雷把“福”改成了“馥”,意为芬芳。 这仿佛是一个隐喻:傅雷希望她从一个俗世的幸福女子,变成一个富有精神芬芳的完美伴侣,然而,要维持这股“芬芳”,朱梅馥付出的是碾碎自我的代价。 这桩婚姻的底色从一开始就埋着一颗未爆的炸弹,两家虽是远亲,自幼青梅竹马,但在14岁订婚后,傅雷去法国留学,那里并没有等待他的“守身如玉”。 一朵名为玛德琳的金发“红玫瑰”点燃了傅雷的热情,那种异国的热烈彻底冲垮了他对表妹的回忆,傅雷甚至写好了退婚书,大谈恋爱自由,信交给了好友刘海粟。 如果不是刘海粟当时多了个心眼,把这封可能毁掉两家交情的信扣下没发,朱梅馥的人生或许会截然不同。 大洋彼岸的玛德琳受不了傅雷的性格缺陷走了,失恋的傅雷甚至闹过自杀,等这阵风暴平息,刘海粟才告诉他信没寄出。 1932年,毫不知情的朱梅馥迎回了表哥,在上海披上婚纱,她以为是水到渠成的良缘,实际上是捡回了一段破碎后修补的余温。 婚后的日子,朱梅馥活成了一尊“菩萨”,这不是夸张,是朋友们送她的称号,因为傅雷太难伺候了。他在外是才华横溢的翻译家,在家却是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孩子稍微淘气一点,他抄起家伙就砸过去;在社交场合,哪怕是对着杨绛先生这样的友人,因为对方一句谦虚的话,他也能当场翻脸,让人下不来台。 而每一次暴风雨后,出来收拾残局、抚慰受伤心灵的,永远是朱梅馥,她不仅要精通钢琴,能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得入味以迎合丈夫的审美,还要在丈夫深夜工作时做秘书、查资料,更要在丈夫感情出轨时,做一个不可思议的“旁观者”。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在傅雷迷恋上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的时候,那时,因为无法和“缪斯”相守,傅雷在家暴躁异常,看什么都不顺眼,整个家充满了火药味。 看着丈夫在自我折磨中发狂,朱梅馥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她主动把这位情敌请到了家里。 不是为了谈判,仅仅是因为只有那个女人来了,傅雷的情绪才能安定,家里的硝烟才能散去,那位女高音坐在客厅里,看着朱梅馥端茶倒水,看着这个妻子平静地操持家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成全他们的“精神恋爱”。 这种无声的包容最终让成家榴感到了巨大的羞愧和压力,再加上后来张爱玲等人的文字揭露,这位“红颜知己”最终主动退出了这场拥挤的三人行,她甚至对人感叹,如果是自己,绝做不到朱梅馥这般。 朱梅馥这种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或许源自她灰色的童年,4岁那年,父亲朱鸿因冤案入狱,母亲为了洗清冤屈四处奔波,家里的孩子接二连三生病,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没保住,最后只剩她一个独苗。 在那段漫长而孤寂的时光里,母亲也是这样,没有笑容,只是麻木地轻拍着她,在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并没有让她变得反叛,反而让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旧式坚韧与新式的知性奇怪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种融合让她成了傅雷一生的“容器”,傅雷曾说,离开朱梅馥他一天也过不下去,这不是情话,是实话,没有这个女人在底下像垫棉胎一样托着他,他那尖锐的棱角早就把自己撞得粉碎。 直到那最后的一天,当外界的风暴再也无法阻挡,傅雷选择了这一生最后一次任性,而朱梅馥,依然是那个最为妥帖的执行者,她没有恐惧,没有退缩,如同当年看着情敌进门一样,平静地配合着丈夫的死亡仪式。 那撕开床单的声音或许是她这一生中发出的最刺耳的“反抗”,但即便如此,凳子下的棉花还是出卖了她的温柔——直到最后一刻,她还在为这个世界着想,哪怕这个世界并没有善待过她。 信源:《傅雷家书》《傅雷传》 杨绛《我们仨》《傅雷与他的世界》 上海文联官网《傅雷:翻译巨匠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