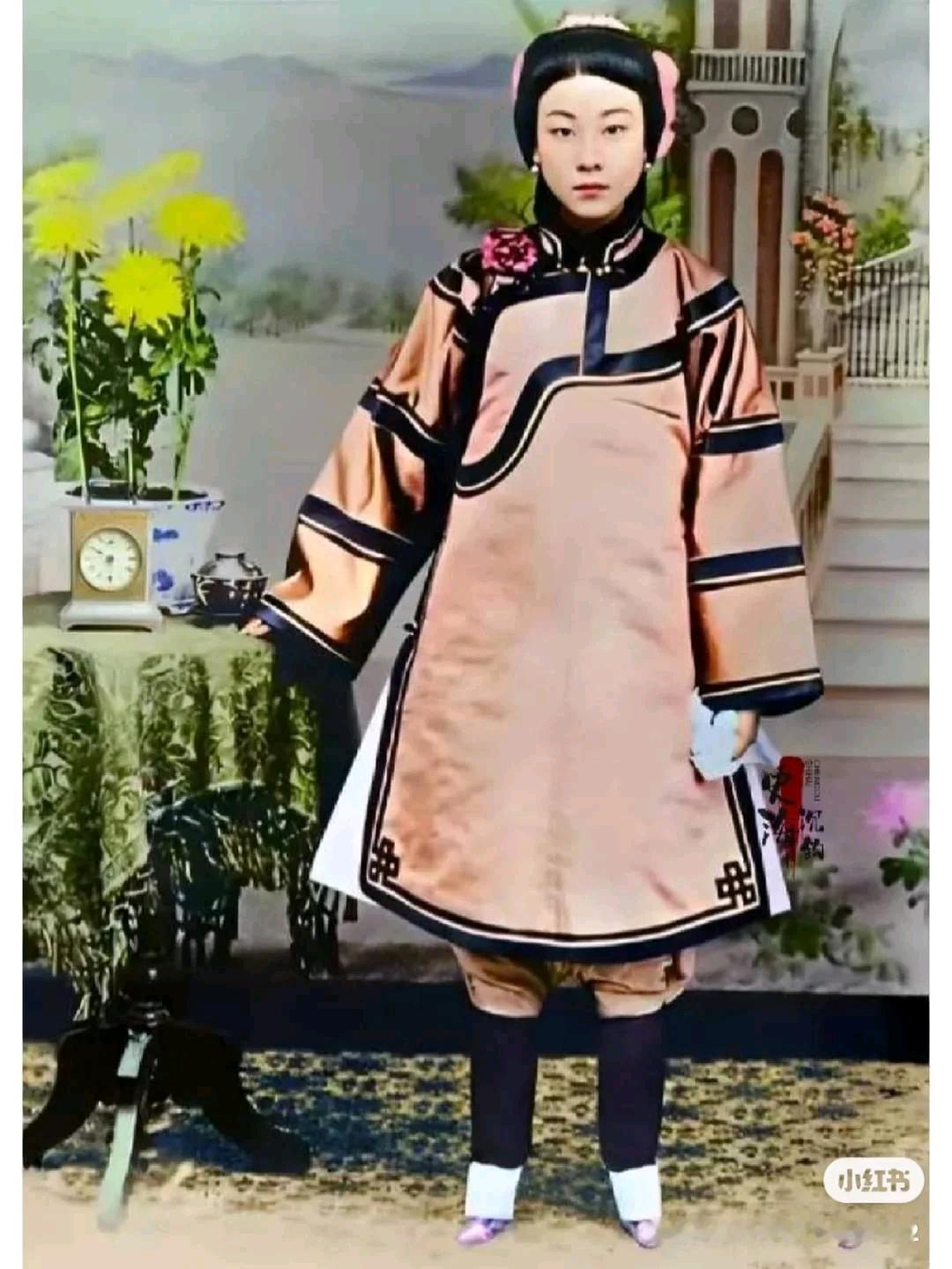1881年, 光绪 在后宫闲逛忽见一宫女姿容秀丽,拉到没人处就临幸。不料,忙活半天竟失败了。 紫禁城的冬天向来冷得干脆。1881年正月,御花园的枯枝上还挂着残雪,十七岁的光绪却走得飞快,像要把寒气甩在身后。他刚陪慈禧用完晚膳,借口"消食"溜出来,其实只是想躲一躲太后那句"皇帝该早立中宫"的老生常谈。他绕过长廊,鞋底踏在青砖上发出细碎的咯吱声。月华门拐角处,一盏羊角灯晃得人影忽长忽短。 灯下站着个穿绛色棉袄的宫女,正踮脚去够梅枝上的雪,袖口滑下去,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腕子。光绪愣了片刻——那截腕子像一截新藕,在雪色里亮得晃眼。你叫什么?"他开口才发现嗓子发干。宫女吓得一抖,雪团子啪嗒砸在脚背,慌忙蹲身:"回万岁爷,奴婢王杏儿,在内织局当差。" 光绪"嗯"了一声,其实没听清。他满脑子都是那只受惊的小鹿——对,就是去年木兰围场里那只,眼睛黑得能映出人影。他抬手示意太监们退到十步外,自己背着手往假山石那边走。王杏儿不敢不动,垂着头跟过去,棉鞋在雪地里踩出两串小坑。 假山石后的风更冷,卷着雪沫子往领子里钻。光绪转身时,袍角扫过石上的残雪,簌簌落了王杏儿一身。他伸手去抓那截记忆里的白腕,指尖触到的皮肤却冰凉发颤,像摸在一块被雪冻过的羊脂玉。王杏儿的身子瞬间绷成了弓弦,连呼吸都放得极轻,发髻上的银簪子磕着青石,叮当作响,在这寂静的角落里显得格外刺耳。光绪突然慌了神,他只知道自己是皇帝,想要的东西就该顺理成章得到,可没人教过他,该如何靠近一个怕他怕到骨头里的女子。他手忙脚乱,脑子里全是慈禧在朝堂上垂着眼帘说"皇帝当守规矩"的模样,那模样像根绳子,死死捆着他的手脚。忙活半天,终究是败下阵来。 他又羞又恼,一脚踹在假山石上,震得石缝里的雪簌簌往下掉。石屑蹭破了掌心,他却感觉不到疼,只觉得一股火气从脚底往上冲,烧得脸颊发烫。王杏儿早已跪倒在地,额头贴着冰冷的青砖,嘴里反复念着"奴婢该死",声音里带着哭腔,却不敢哭出声。光绪看着她伏在雪地里的背影,那身绛色棉袄早已被雪打湿,晕开一片深色的渍,突然觉得自己和她没什么两样。他是皇帝,可连立谁当皇后都做不了主;她是宫女,连抬头看一眼皇帝都算僭越。他们都是被紫禁城的红墙围起来的囚徒,只不过他的囚衣是龙袍,她的是粗布棉袄。 1881年的这一年,对光绪来说本就难熬。三月里慈安太后突然离世,慈禧彻底没了牵制,对他的管控更严了。立后之事被提上日程,慈禧早就属意自己的侄女静芬,可光绪一想到要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共度一生,就觉得胸闷。他溜出来闲逛,本是想躲一时清净,可撞见王杏儿的那一刻,他突然想抓住点什么——抓住一点不属于慈禧安排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他终究是抓不住。临幸失败的尴尬,不止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突然明白,慈禧要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皇帝,而是一个听话的傀儡。连他的身体,他的欲望,都要受着无形的控制。 王杏儿后来的下场,没人知道。紫禁城的宫女太多了,少一个两个,就像枯枝上落一片雪,没人会在意。或许她被发配到了冷宫,或许她被秘密处理了,或许她侥幸活了下来,却再也不敢靠近月华门的拐角。而光绪,回到养心殿后,坐在龙椅上,看着桌上的奏折,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他脑子里全是那截白生生的腕子,和自己踹在假山石上的那一脚。那一脚,踹的是假山石,更是他自己的无力。 有人说光绪懦弱,可谁又想过,他从四岁被抱进皇宫起,就没尝过一天自由的滋味。慈禧教他帝王之术,却没教他如何做自己。1881年的这场尴尬,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整个晚清朝廷的悲哀。一个连自己的私生活都做不了主的皇帝,又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挽救一个走向灭亡的王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