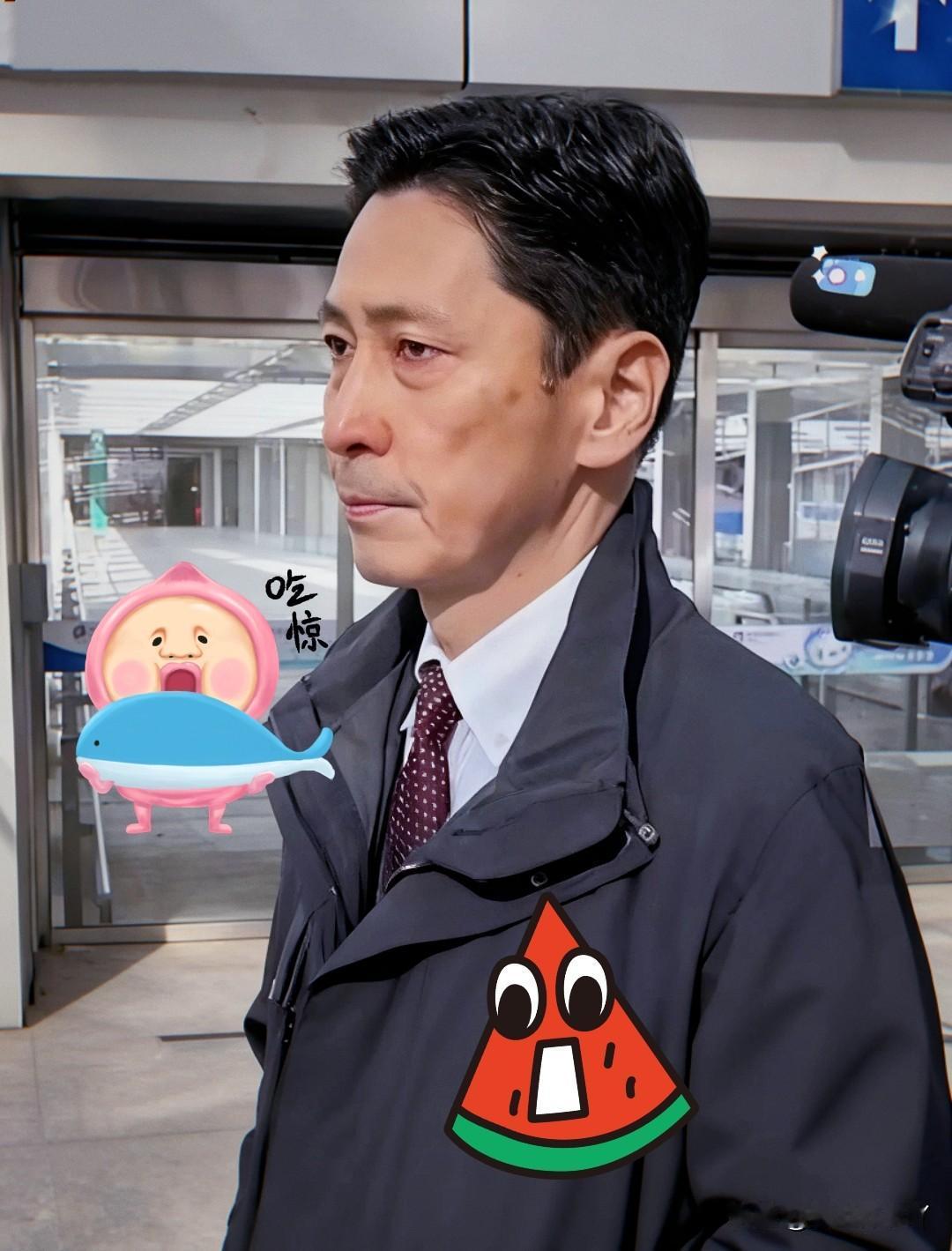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中日一有冲突的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没听说抢着回日本的,起码表面上看,依然该干嘛干嘛。 但在日本的中国人都纷纷要回国内,生怕被日本人打了。 截至2024年底,在华日本人约12万,在日中国人超100万。二者数量存在悬殊,但并非核心原因。该现象的核心诱因,需从70余年前的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事件追溯。 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日侨日俘总数达200余万,其中105万人经葫芦岛港遣返回国。彼时中国民众刚历经战乱,粮食供应极度短缺,却仍将有限粮食调配给日侨。 葫芦岛周边年产量仅400万公斤粮食,供应日侨消耗就达262.5万公斤,当地民众只能以野菜充饥。 有一名日本孩童因严寒濒临失温,一名中国大娘将其抱入怀中取暖,并省下口粮喂食。这名孩童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终其一生感念这份恩情。 这段历史并非感性叙事,而是深植于两国民众记忆的重要印记。在华日本人通过教育等途径接触该段历史,对中国社会包容普通民众的特质形成认知。 反观日本,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当局煽动民众屠杀旅日朝鲜人,这种排外暴力事件形成的历史记忆,使在日外国人长期存在心理戒备。 从当前安全环境来看,日本虽以治安良好著称,但排外情绪的隐性发酵,实则比显性暴力更易引发不安。2025年7月,日本某新兴右翼政党以“日本人优先”为竞选口号,在参议院选举中大幅提升得票率;首相高市早苗也多次表态将收紧外国人政策。 社交媒体上,“外国人抢占就业岗位”“挤占社会福利”等谣言传播甚广,京都、东京等地民众亦有关于游客推高物价的抱怨。 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媒体常放大外国人犯罪案例,但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显示,近30年间在日外国人数量从130万增至377万,犯罪检举数却从1.4万降至9700余起,犯罪率呈下降趋势。谣言的传播速度远快于数据普及,这种信息不对称显著削弱了在日华人的安全感。 中国对外国人犯罪案件坚持依法处理,并未上升至群体歧视层面。2025年上半年,上海一名日本职员因酒驾被查处,媒体报道中仅以“外籍男子”指代,未刻意强调其日本国籍,更未引发针对在华日本人的排斥活动。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处理原则,使在华日本人具备较强的安全感。 经济依存度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华日本人多为企业高管、技术人员或教职人员等高端人才,其专业能力与中国市场需求高度匹配。 以汽车行业为例,丰田、本田在华工厂的核心技术岗位中,日本员工占比颇高。若冲突升级,企业会主动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相关人员无需仓促撤离。 日本的情况则相反,截至2024年底,日本外籍劳工达230余万人,其中大量人员从事建筑、护理、农业等本土劳动力不愿涉足的领域。此类岗位替代性较强,若出现冲突,企业可能优先裁减外籍员工。 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于2025年提高经营管理签证门槛,将注册资本要求从500万日元提升至3000万日元,同时增设本地员工雇佣要求,这一政策调整使部分在日华人对政策稳定性产生担忧,遇局势波动便倾向回国。 另一个易被忽视的因素是侨民管理模式差异。中国对外国人采取“融入型”管理,以上海、苏州为例,当地既设有日本人学校,也积极引导日本侨民参与社区活动,不少日本家庭会参与邻里节庆互动。 日本则呈现“隔离型”特征,外国人聚居区与本土社区界限清晰,语言障碍与文化隔阂叠加,使在日华人难以实现深度融入,遭遇问题时易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有观点以2012年钓鱼岛事件为反例,质疑当时在华日本人是否存在恐慌。据日本驻华使馆统计,彼时仅不足1%的在华日本人临时回国,绝大多数选择留守。 其核心原因在于,他们清楚个别极端行为会受到政府严厉惩处,且中国社会主流对暴力持反对态度。反观同期在日华人,有近10万人临时回国。当时日本街头出现针对华人的游行活动,虽未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但紧张氛围已足以引发不安。 中日侨民在冲突中的不同反应,绝非“胆量”二字可以简单概括,而是历史记忆的沉淀、现实安全环境的差异、经济依存关系的强弱,以及侨民管理与社会融入模式的不同,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华日侨的“镇定”,根植于中国社会对普通民众的包容传统、法治框架下的个体安全保障,以及其自身在经济结构中的不可替代性;而在日华人的“谨慎”,则源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排外情绪隐患、外籍群体较低的融入度,以及职业与政策层面的不稳定性。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日民间交流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青年一代之间的文化互动增多,这种基于历史记忆与环境认知的差异正逐步弱化。 未来,若两国能在民间互信、侨民权益保障等层面进一步发力,或许能构建出更稳定的跨国民众相处模式,让“冲突时的侨民恐慌”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