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再次语出惊人:“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他还强调:“自从我来到美国并于1962年入籍以来,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国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张忠谋那番关于美国的言论,乍听之下够直接,细琢磨其实全是半辈子浸在美国半导体体系里的实在话,毕竟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就是跟着美国芯片产业一起长起来的。 1955年24岁的他刚踏入半导体行业时,就钻进了美国的希凡尼亚公司,三年后跳槽到德州仪器,成了这家后来登顶全球的半导体巨头里第一个华裔员工。 那时候的德州仪器还没成气候,年营业额不足1亿美元,但张忠谋在这里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火箭升迁”,1964年当锗电晶体部门总经理,1965年接掌硅晶体管业务,1966年又管起集成电路,三年连跳三级,30多岁就成了统领四万名员工的半导体集团总经理,手里攥着德仪所有半导体业务的决策权。 关键是德州仪器还出钱送他去斯坦福读博士,签了五年服务合约,等于把他的技术根基和职业前途都牢牢绑在了美国体系里,这种从成长到巅峰都被美国产业力量托举的经历,很难不催生深层的身份认同。 他嘴里美国的“光辉典范”,说白了就是一套能攥住全球芯片产业命门的供应链体系,这可不是空泛的吹捧,全是实打实的技术和资本硬实力。 就说全球芯片厂都得仰仗的ASML光刻机,表面看是荷兰制造,实际上55%的零部件都得从美国采购,连美资都持有30%的股份,荷兰政府的出口禁令说白了就是看美国脸色行事。 台积电就算有最先进的制程工艺,没有ASML的EUV光刻机也玩不转,而这机器能不能拿到手、能卖给谁,最终话语权全在美国手里。 别提芯片设计离不开的EDA软件,全球74%的市场份额被Synopsys、Cadence、SiemensEDA这三家美国公司瓜分,在中国市场他们的占比更是接近80%,台积电设计任何一款先进芯片,都得在这些美国软件搭建的框架里干活,等于命脉直接捏在美国手里。 张忠谋心里比谁都清楚,台积电能从一个技术落后2-3代的新创公司,长成如今的“护国神山”,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美国体系的滋养。 1985年他回台湾接手工研院时,台湾最先进的制程才两微米,比英特尔、德仪的一微米落后整整两代半,唯一能拿出手的不过是落后技术里的高良率。 创办台积电后,看似是开创了专业晶圆代工的新模式,实则是踩准了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节奏——美国公司专注设计和品牌,把制造环节外包出来,台积电正好接住了这波红利。 就连台积电的技术迭代,本质上也是跟着美国的步调走,早期受德仪技术影响深远,后来攻坚3nm、2nm制程,从设备到材料再到工艺标准,没有一样能绕开美国主导的产业链规则。 美国这套体系不仅能造巨头,还能收拾不听话的对手,这一点张忠谋早在德州仪器时就看得明明白白。 他在德仪当总经理时,就把刚成立四年的英特尔当成最强对手,亲眼见证英特尔靠着记忆体产品崛起,更目睹了德仪因为偏离半导体主业、转向消费品而被超越。 后来日本半导体在上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一度抢占全球半壁江山,结果美国直接挥起贸易大棒,通过反倾销调查、技术封锁等手段硬生生把日本企业按了下去,这让张忠谋彻底看清:在半导体行业,谁脱离美国主导的体系,谁就难有活路。 就像当年他在德仪管着四万人的半导体帝国,风光无限,可一旦公司战略脱离美国产业主流,照样被同行甩在身后,这种教训足够深刻。 到了晚年,张忠谋更清楚台积电和美国体系的捆绑有多深。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一出台,台积电就得乖乖去亚利桑那州砸钱建厂,哪怕成本比台湾高得多,也得配合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步调。 最现实的是台积电的客户里,苹果、高通、英伟达这些美国巨头占了大头,营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随时能通过技术限制、市场准入等手段卡脖子。 之前美国要求台积电交出商业数据,台积电再“精明”也只能配合,这种无力感恰恰说明,它早已成了美国体系里的关键一环,却绝非能自主决策的主角。 张忠谋自称美国人、夸美国是“光辉典范”,与其说是立场问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精准判断。 从24岁踏入半导体行业起,他吃的是美国的技术饭,拿的是美国企业的资源,做的是美国体系内的生意,六十多年下来,早就和这套体系长成了共同体。 他比谁都清楚,美国的“光辉”本质上是对全球芯片产业链的绝对掌控力,而台积电也好,他自己也罢,都是这套体系滋养出来的果实,根本没资格也没能力跳出圈子。 这种认知不是凭空来的,是半辈子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在体验,毕竟在半导体这个江湖,美国的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 参考资料:台海时刻《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受访时再次语出惊人:“我真的认为,我的国家——美国,仍然是世界的希望,仍然是世界上光辉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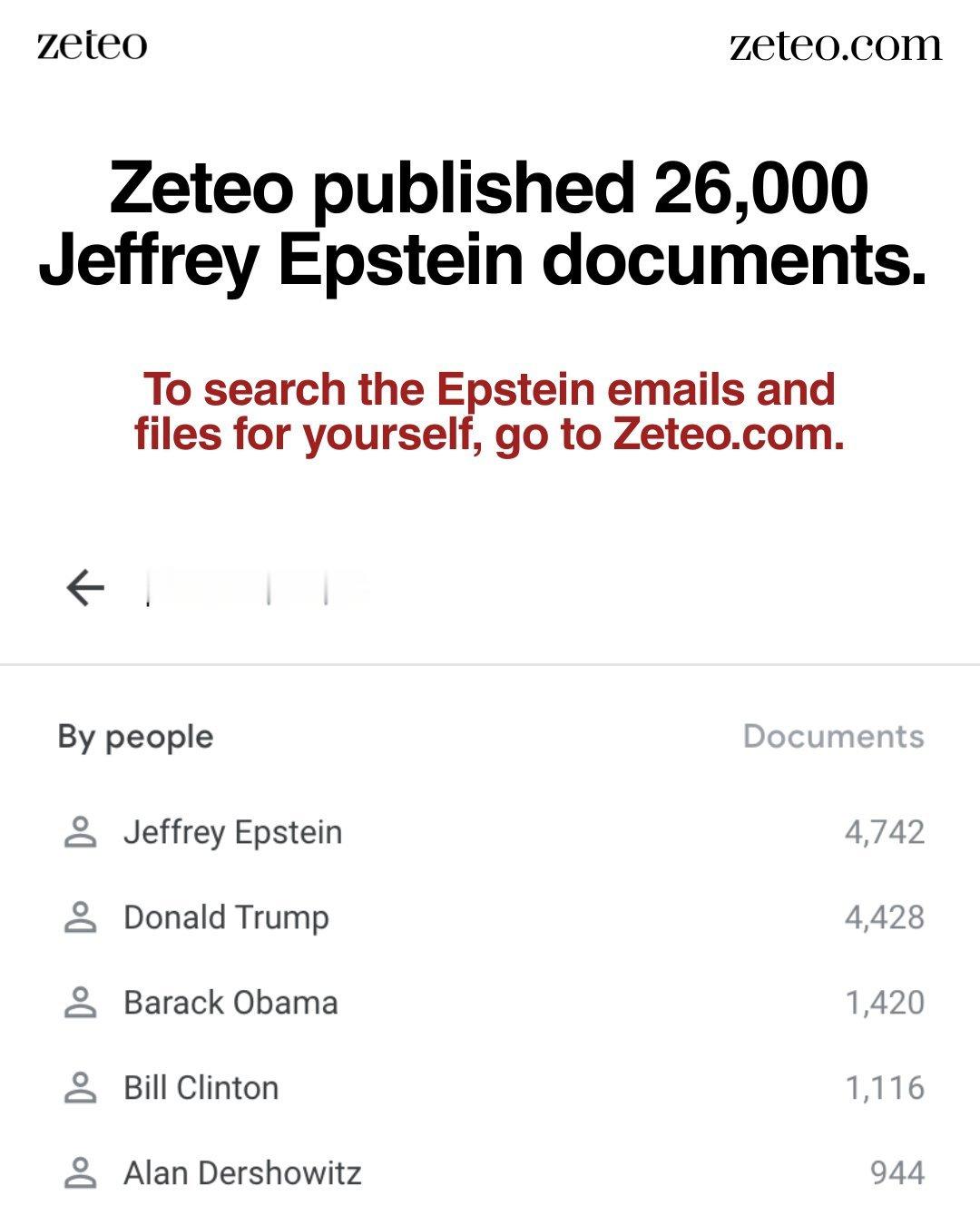

![华为mate80Promax有双层OLED[笑着哭]当然RS也是标配的,备货量反而](http://image.uczzd.cn/13203604754209275157.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