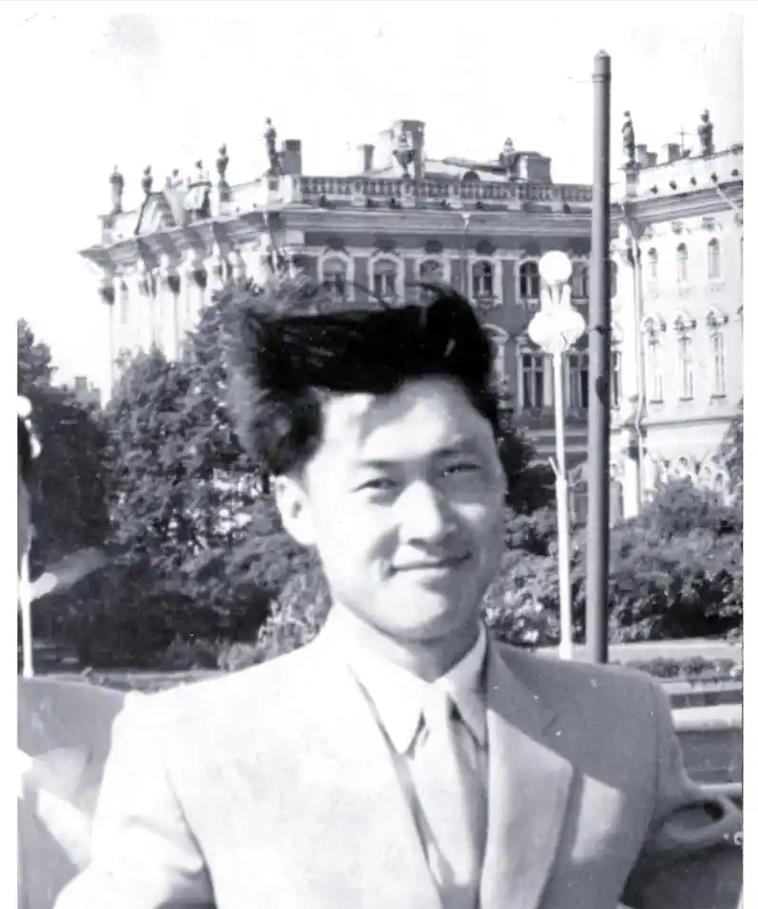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在酒泉的地下会议室,几十名科研人员围坐在图纸前。 桌上摆着厚厚一摞试验数据——推力不足,射程不达标。导弹飞不远,这意味着整个东风2号计划可能被迫推迟。 几乎所有人都指向一个结论:加助燃剂。 “再多加一点燃料,推力就能上去。”这在火箭动力学里,是最直觉的判断。 可就在众人都准备签字时,一个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 他语气平稳,却让全场安静下来—— “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掉六百公斤。” 会场一时寂静。有人以为他听错了,有人盯着他看。 只有坐在前排的钱学森,微微抬头,目光变得凝重。 这场看似简单的技术争论,成了中国导弹史上最惊险的一次逆转。 1950年代末,中国的导弹事业几乎是从零开始。苏联撤走专家后,留下的只有几份模糊的蓝图和一堆零散的参数。钱学森带领几百名年轻人,从发动机、制导到燃烧配比,一项项摸索。 1962年,东风2号进入实质研发。那时,中国的目标很明确——要造出一枚射程上千公里、能自主发射的导弹。 可现实远比理想骨感。第一次试射,导弹在半空中偏离轨道,坠落在戈壁滩。第二次,点火失败。第三次,勉强飞起来,却只飞了几百公里。 问题在哪? 数据摆在那里——推力不足。按设计,这枚导弹应能飞到目标区,可燃烧结束时,速度始终差一点。工程师们分析原因:也许是助燃剂比例不够,也许是推进系统燃尽太快。 于是会议被一场又一场地召开。专家们不断计算、对比、模拟。结论几乎一致:加助燃剂,让燃烧更充分。 钱学森也没有立即否决。他清楚,在那个阶段,中国的液体推进剂研究还远不成熟,很多参数只是估算。加燃料,确实可能带来推力提升。 可问题在于——“可能”只是理想。导弹不是试管实验,重量、气化、燃烧速率、结构强度都可能被改变。 那一年的夏天,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枚导弹为什么总“差那么一点”的答案。 会议在六月初召开。地点是戈壁边的一处地面实验室。几十位工程师坐成两排,墙上挂着推进剂流量曲线和压力表。 钱学森主持。每个人轮流汇报,焦点只有一个:射程不够怎么办。 多数人主张增加助燃剂,哪怕只加百分之一,也可能多飞几十公里。 技术组有人提出,温度偏高导致推进剂气化流失,加多一点可以弥补损耗。所有数据似乎都支持“多加”。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工程师站起来。 他叫王永志,三十岁出头,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不久,是推进系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他说出那句让人心惊的话:“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还要减掉六百公斤。” 会议室的空气顿时紧绷。 他的理由很简单:导弹不是火箭车,多加燃料就能跑更远。重量增加后,结构负担加大,阻力上升,推力反而下降。尤其是液体助燃剂——太多会造成燃烧不完全,喷口效率降低。 更关键的是,他发现发动机燃烧过程中的“混合比”并不理想。过量的助燃剂使燃烧温度下降,推力浪费在无效气体上。按他的计算,真正该做的不是加,而是减。减重、提高燃烧比,反而能提升射程。 这个结论,几乎挑战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在当时的科研体系中,年轻人很少公开否定集体方案,更何况面对的是钱学森亲自主持的会议。 会场一度安静。几位老专家皱着眉,翻着数据。没人再说话。 钱学森没有打断,也没有表态。他低头,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个公式。然后抬头,看着王永志的报告。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会后,钱学森让推进组重新计算燃烧效率曲线。 一连几天,实验台的火焰一次次点燃,温度传感器在风中闪烁。科研人员测算每一秒的压力变化, 把燃烧室内的流速、温差、气化率全部记录下来。 结果出人意料——在原方案中,燃烧确实不够充分。 当助燃剂过量时,部分燃料在喷口未完全燃尽,推力被“浪费”掉。 王永志的推算是对的:减少600公斤助燃剂,混合比更接近理想状态,推力反而提升了3%。 这一发现让钱学森彻底改观。他立即批准在下次试射中采用“减助燃剂方案”,并重新校准喷口参数。 6月下旬,戈壁滩。 东风2号试验箭竖立在发射架上,银灰色的弹体在烈日下闪光。地面气温超过三十度,液氧在加注过程中不断冒白雾。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发成败至关重要。 “5、4、3、2、1。” 轰鸣声撕裂空气,火焰拖着长长的尾迹,导弹离开发射架,直冲云霄。 这一次,它没有偏离轨道,也没有提前熄火。 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一路向前,穿过千里戈壁。 几分钟后,目标区传回信号——命中。 射程,突破1000公里。 那一刻,所有人都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