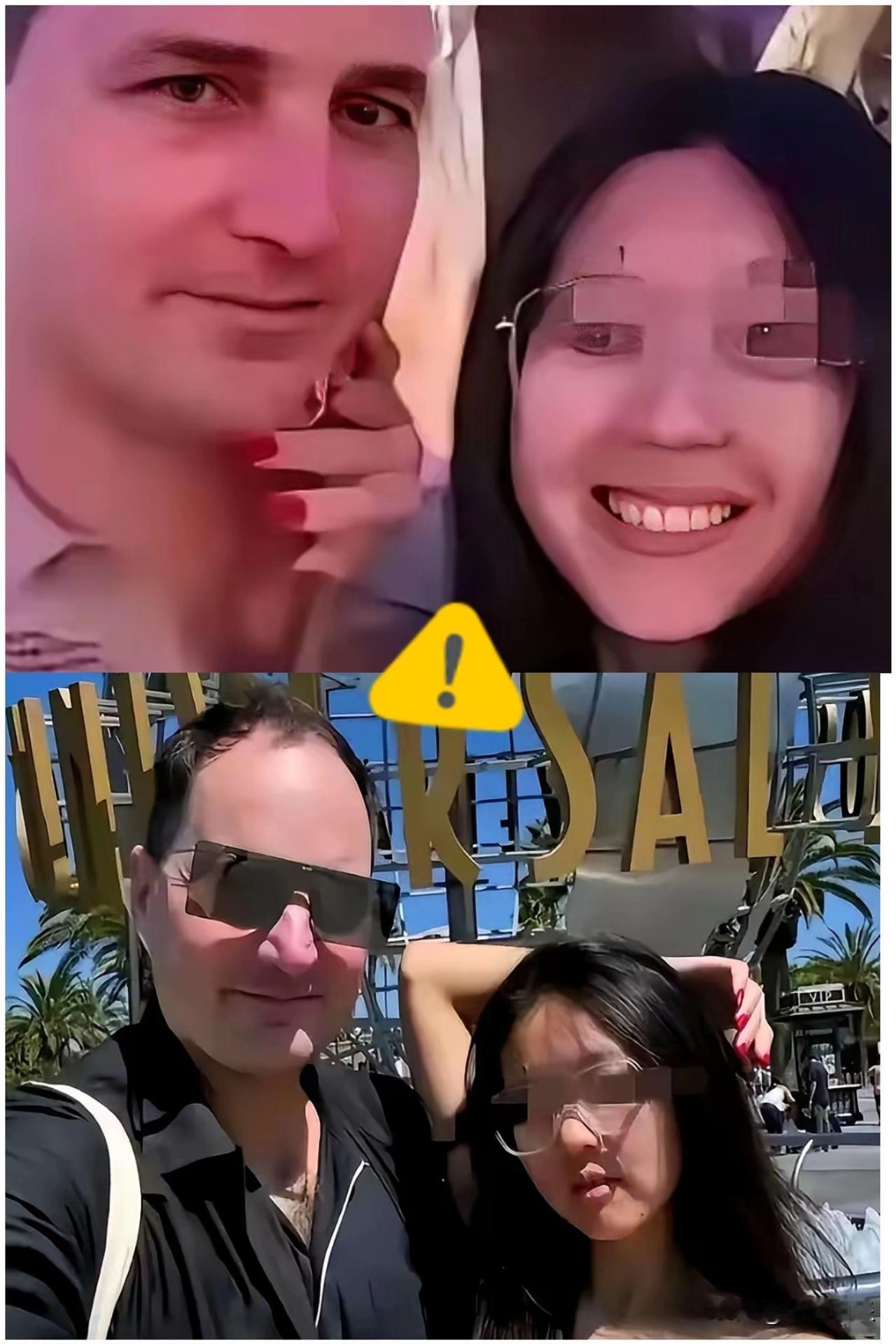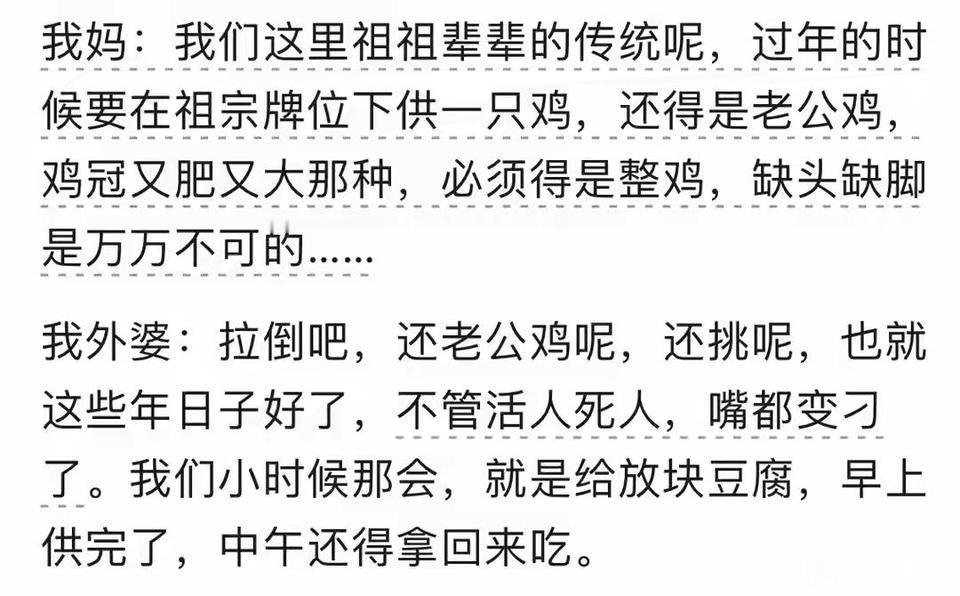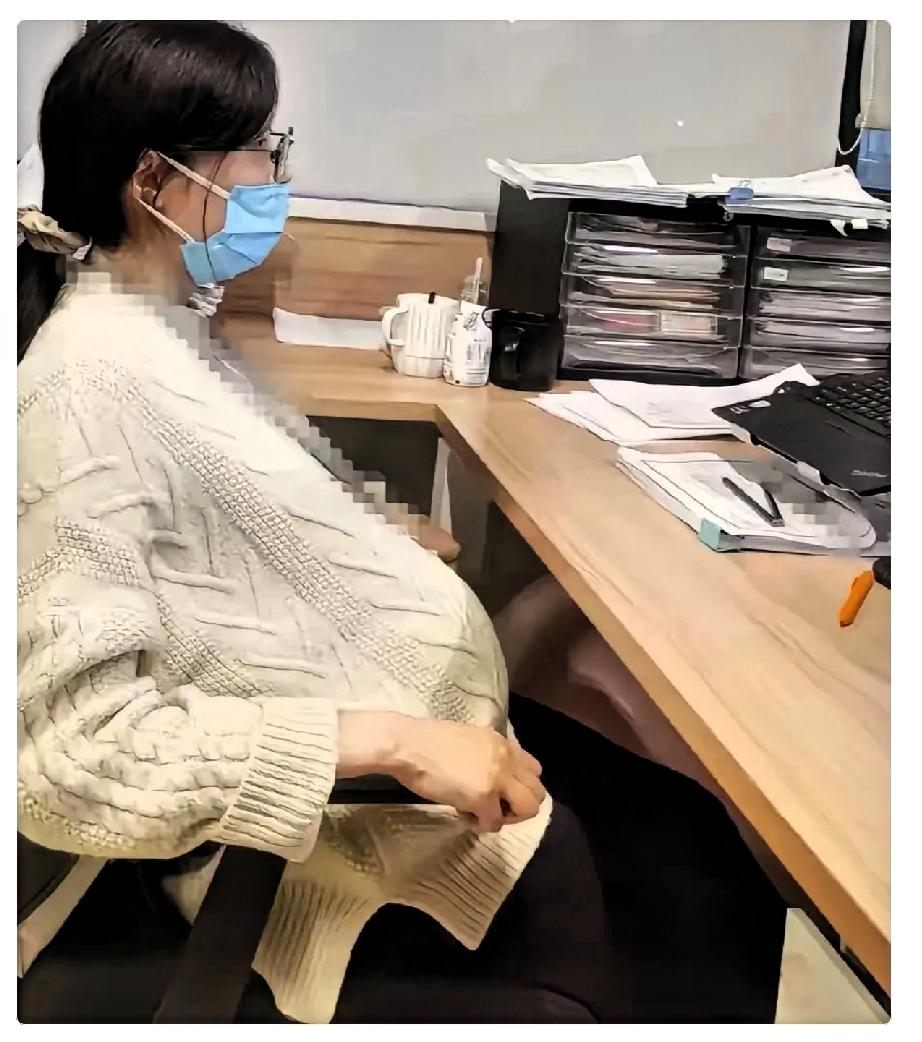莫斯科出生,中文名四十八年没用过,回国后才第一次填上祖父名字。 他不是来认亲的,是来干活的。 签证那天在莫斯科大使馆,他递材料时手指有点抖,不是紧张,是那张表上“亲属关系”一栏,他写了“刘少奇”三个字。旁边工作人员扫了一眼,没说话。他军装笔挺,俄语流利,档案里写的是费多托夫·阿廖沙,可笔尖落下去,墨迹没糊,字很实。 小时候在莫斯科,没人叫他刘维宁。“阿廖沙”就是他。妈妈玛拉给他改了姓,不是不想认,是1957年以后,风声紧,她怕孩子将来出事。五岁那年在列宁山见了爷爷一面,老人送他一套烟具,上面刻着黄山云海,他当时穿着补丁布鞋,手心全是汗,可看见那山水,忽然觉得熟悉,像听过什么歌,调子还在,词忘了。 爸爸刘允斌1957年回中国搞核燃料,走前和妈妈说好:你在莫斯科守家,我在中国守厂。后来爸爸死了,她没告诉孩子们,怕他们夜里哭醒。这事儿瞒了二十年,直到1987年姑姑刘爱琴托人带话,他才明白,原来父亲不是“失联”,是被时代按在了另一头。 他干航天,中校,涉密岗位,俄罗斯不放人。等?他说不等了。1998年主动退伍,不是混不下去,是想把图纸、调度、对接这些本事,换个地方用。回广州不是图舒服,是这儿港口多、翻译多、俄语标牌还能找到,他做事方便。 现在他在做中俄生意,帮内蒙古卖羊肉,替海南推橡胶,办公室挂一张刘少奇画像,二十块钱旧货摊淘的,边角卷了,但天天看见。孙子在广州出生,户口本上写着中国籍,他教孩子喊“爷爷”用中文,喊“奶奶”用俄语,不教谁高谁低,就教怎么叫人。 他开车考的是中国驾照,常去茶楼听粤语讲古,听不懂就点头,反正大家笑,他也笑。加入新四军合唱团不是为了怀旧,是那儿有同龄人,能一起唱《南泥湾》,也能聊孙子发烧该吃啥药。 去年他带儿子回过包头202厂旧址,铁门锈了,标语还剩半句。儿子问:“我爸真在这儿待过?”他点点头,没说话,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发到俄罗斯老同事群里,配文就俩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