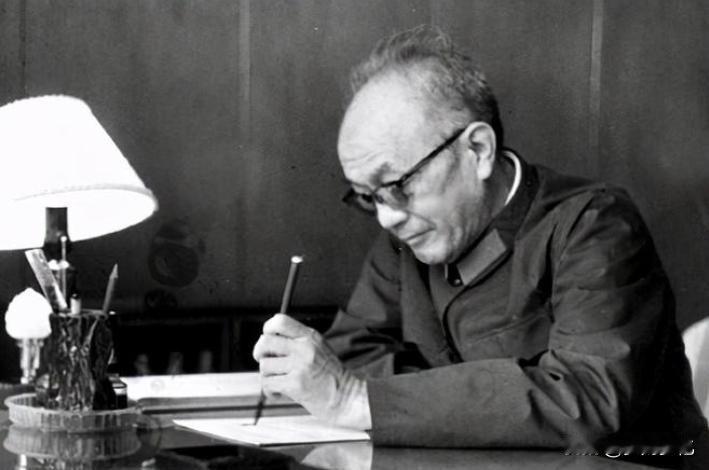1941年,国军团长陈锐霆投奔新四军后,在夜里被人连捅3刀,杀手走后,伤重的他本想起身,但又想到了什么,果断躺地上装死。 血正汩汩地从伤口往外冒,夜露混着泥土味儿直往鼻子里钻。陈锐霆咬紧牙关,愣是没让自己哼出一声。刚才那几下捅得又狠又快,黑影窜出来的时候,他连对方的脸都没看清。刀子扎进身体的闷响,他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不能动——他脑子里反复滚着这三个字。谁知道那杀手走远了没有?万一还在暗处盯着呢?这时候爬起来,不等于告诉人家刚才没捅到位么。 他就这么直挺挺躺着,感觉血慢慢把身下的土浸湿了。疼是真疼,小腹那刀最深,稍微喘口气都扯着疼。可比起疼,更让人发冷的是那股子后怕:这才投过来几天?人还没认全呢,刀子就先找上门了。 月亮从云缝里漏出一点光,刚好照见他右手边半截土墙。陈锐霆盯着那截墙影子,脑子里过电影似的闪过这几天的事。 投奔新四军不是一时冲动。在国军那边干了这么多年,眼睁睁看着上面扯皮推诿、见死不救的事太多了。台儿庄那会儿,他的老营拼得只剩几十号人,等来的不是增援,是一纸“擅自出击”的申斥。心寒不是一天攒下的。 可这边呢?他来之后,接风的晚饭就是红薯稀饭加咸菜,师长却把自己藏的半包烟塞给了他。“委屈陈团长先适应适应,”那位戴着旧眼镜的师长笑得有点歉疚,“咱们穷是穷,打鬼子不糊弄。” 话实在,听得人心里踏实。但也正因为这踏实,今晚这刀子才显得格外刺眼。 是什么人?旧日同僚清理门户?这边内部有钉子?还是纯粹冲着他这个人来的私仇?陈锐霆闭着眼,耳朵却竖得尖尖的。远处好像有狗叫,风吹过高粱地的哗啦声,还有自己越来越重的心跳。 时间一点一点熬过去。大概过了半个时辰,也可能更久,伤重的人对时间的感觉都是模糊的,他终于听见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跑得急,踩得土路咚咚响。 “陈团长?陈团长!”声音压得低,但那股子焦灼藏不住。 是侦察连长老赵,白天还跟他请教过地图测绘。陈锐霆喉咙动了动,想应,又憋住了。直到那几双手碰到他肩膀,他才缓缓睁开眼。 “还活着……”老赵声音都颤了,转头吼,“担架!快!” 后来才知道,是老赵查哨时闻到血腥味,顺着摸过来的。再晚半个钟头,人可能就真没了。 在医院躺了半个月,上面调查的结果也下来了:行凶的是原先国军系统的特务,跟了他一路,就等着他落单下手。刀子捅得那么狠,是得了“务必灭口”的死命令。 “装死这招救了你命啊,”老赵后来蹲在病床边说,“那家伙回头确认过,见你一动不动,以为得手了。” 陈锐霆没吭声。他当时哪想那么多,纯粹是战场上滚出来的本能:遇上埋伏,该装死时装死,该拼命时拼命。只是没想到,从国军到新四军,躲过了明枪,却没躲过暗箭。 伤好后,他肩膀上留了道深疤,但位置反倒更稳了。经历过这一遭,有些原本观望的人看清了,这人连死都不怕往回跑,是铁了心要跟鬼子干到底的。 说起那个年代的选择,很多人觉得是站队,是挑山头。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刀尖对着刀尖的时候,人往往跟着心里那点念想走。陈锐霆图什么?后来有次喝酒,他自己漏过一句:“在那边打仗憋屈,劲儿使不出来;在这儿,穷得穿草鞋,可每一枪都朝着该打的方向放。” 这话糙,理不糙。抗战那会儿,多少人是抱着“劲儿得使对地方”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些选择背后,有热血,有算计,有不得已,也有像陈锐霆这样挨了刀子还要躺地上继续演的坚韧。 活下来不容易,活明白了更不容易。那一夜的三刀和随后无声的装死,成了一个缩影,在时代翻涌的浪头里,个人的去留、生死、信念,都得在最短的时间里掂量清楚。掂对了,命或许能保住,路也能继续走下去;掂错了,故事就到那儿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