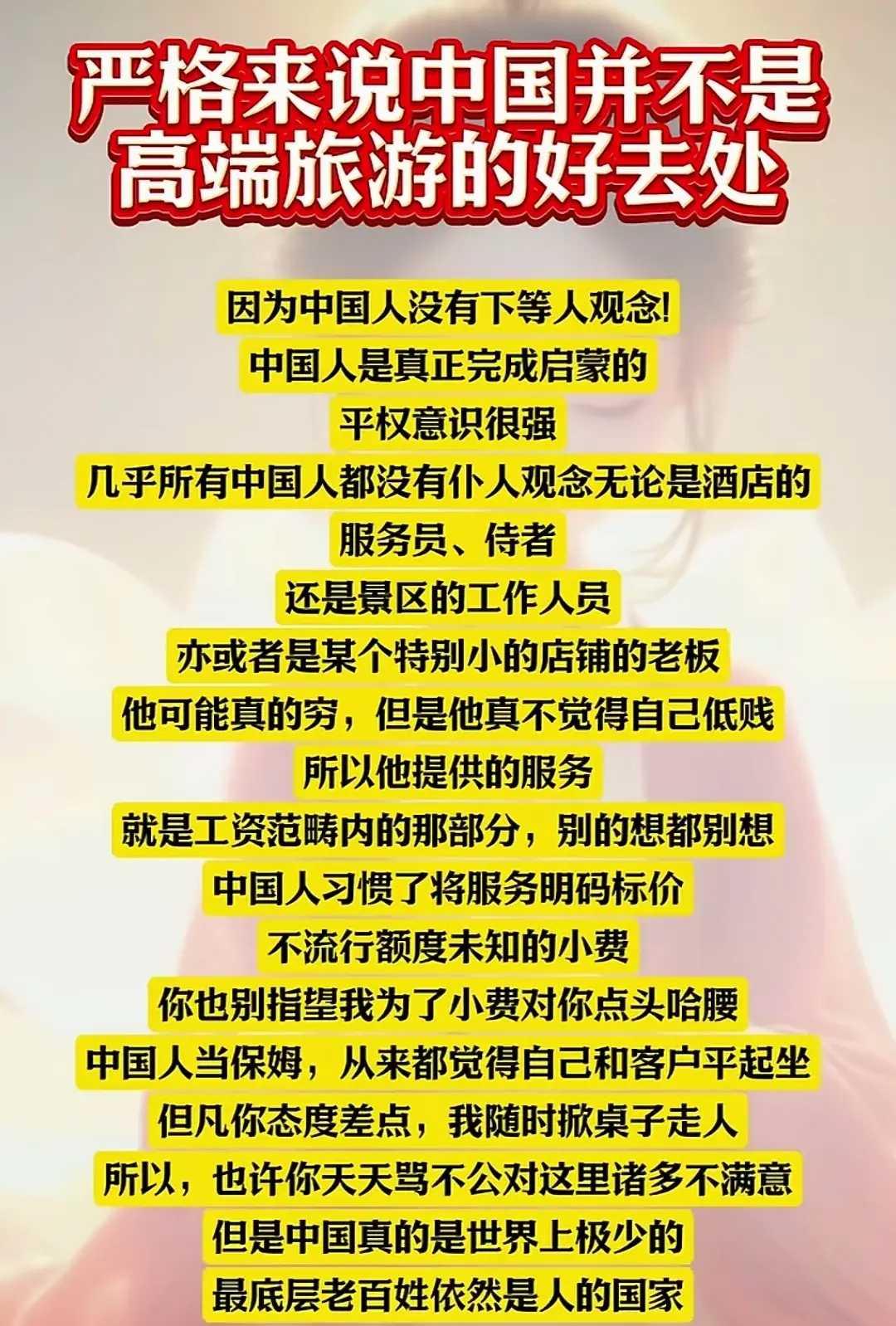它藏得最深的秘密,或许就藏在这样一个清晨:你睡眼惺忪地推开窗,昨夜未干的雨渍在窗棂上闪着微光,楼下早点摊的热气正袅袅升起,氤氲一片温柔的市声。那一刻,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仿佛一切都已就绪。幸福,常常不是攻城略地的占领,而是这般不期而至的发现。它的根须,不在遥不可及的云端,而深植于你与眼前世界真切相处的能力之中。 这能力,首先是一种“凝视”的诗学。木心先生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慢,是时间的褶皱里得以储存意义的空间。当你不再匆匆掠过,而是凝视一片茶叶如何在水中舒展腰肢,看一缕光如何推移地板的刻度,听一阵风摇动树叶如摇动千万片细小的铃铛,你便从时间的囚徒,变成了它的鉴赏家。幸福便在那专注的纹理里,悄然滋生。它不是热烈地“抓住”,而是谦卑地“看见”,看见一碗热汤面上升腾的朴素慰藉,看见陌生人眼角与你相似的疲惫与坚韧。世界在急促的消费与娱乐中变得扁平,而凝视,让它重新恢复深邃的景深与体温。 这能力,更是一种“溶解”的哲学,将生命必尝的涩果,酿成回甘的醴泉。史铁生在荒芜的地坛里,悟出生与死的交界不过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苏轼在黄州的泥泞中,将失意“回首向来萧瑟处”,吟唱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通透。痛苦如一块坚冰,蛮横地梗阻在生命的河道中。而幸福,并非否认这冰块的存在,而是以生命的温度去理解它、融解它,直至它化作活水,重新加入你奔流的河床,成为力量的一部分。它不是对阴影的背过脸去,而是学会与自己的阴影并肩而坐,听它讲述那些被日光忽略的故事。 最终,这能力指向一种“织造”的伦理。约翰·邓恩的诗句响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真正的幸福,往往在“我”与“你”的回响中才能得到确认。一个了无牵挂、自我圆满的神祇,或许强大,却与幸福无关。幸福需要一道投向他人的目光,也需要一道来自他人的目光的照亮。它存在于母亲灯下缝补的针脚里,存在于友人无言却懂的碰杯中,甚至存在于你对楼下流浪猫每日清水的默默放置中。每一次微小的联系,都在广袤宇宙的虚无背景上,绣下一道温暖的针脚。我们以关怀为梭,以善意为线,在冰冷的时空经纬中,为自己也为他人,织就一件可以裹身的温暖意义。 所以,幸福与什么最有关系?它或许与某种境遇有关,但更与凝视境遇的瞳孔有关;它与得到什么有关,但更与如何消化所得到、如何承受所未得有关;它与“我”有关,但更与“我”如何走向“你”、如何在“我们”中确认自身有关。它最终关联的,是你以何种姿态,栖息在这片大地上——是麻木地经过,还是深情地走进;是倔强地对抗所有风雨,还是学会在风雨中听见旋律,并为自己、也为同路人,轻声和唱。
商业航天落幕倒计时!买在无人问津,卖在人声鼎沸。现在的商业航天,无疑已经到了人
【1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