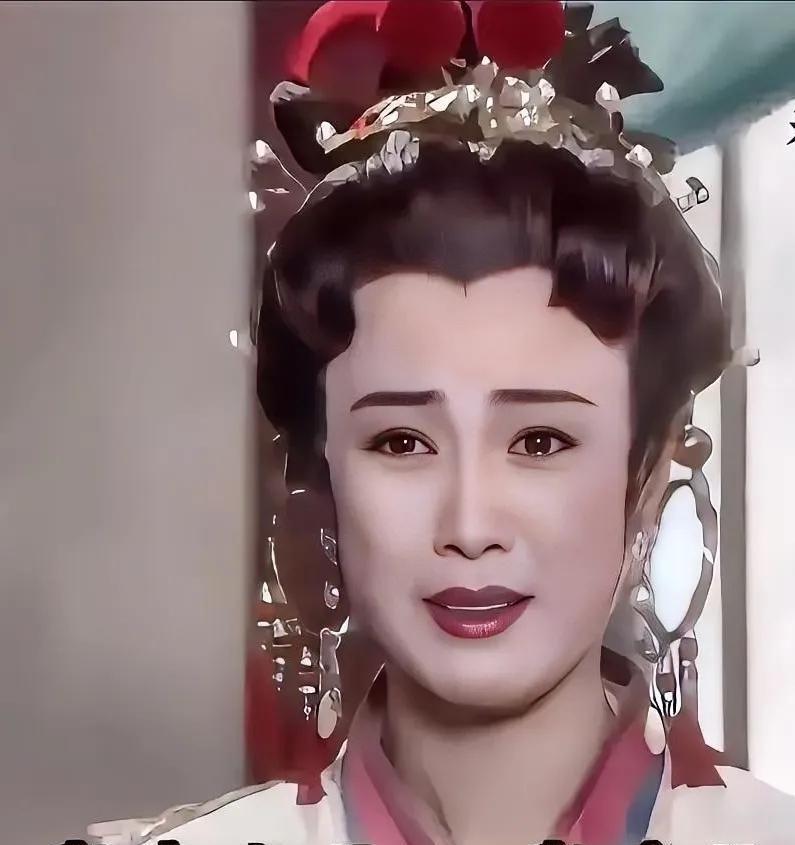620年,李渊迎娶张婕妤。李淳风瞥了一眼新娘,面露惊色,对李世民说道:“此女有凤仪之相,却并非殿下的良配!”李世民听闻,顿生杀意。 彼时的长安城,储位之争早已暗流涌动。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在朝堂内外交织,连后宫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棋子。张婕妤入宫那日,穿着石榴红的嫁衣,行礼时脊背挺得笔直,鬓边银钗折射着殿内烛火,那份不属于寻常秀女的锐利,让李淳风的罗盘指针微微震颤——他看的不是美貌,是藏在从容背后的野心。 李世民的杀意并未立刻付诸行动。他派心腹潜入京兆府查探,卷宗里的记录像藤蔓般缠绕上来:张婕妤的叔父三年前因贪墨被贬,是李建成暗中运作才官复原职;她的兄长现任东宫翊麾校尉,掌管太子亲卫。原来父亲新纳的宠妃,竟是东宫安插在父皇枕边的眼线。 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成了张婕妤第一次露出獠牙的舞台。当李建成被指勾结边将谋反的密报送到李渊案头时,她跪在龙榻前,鬓发散乱,哭称“秦王麾下将领素来与太子不睦,此乃构陷”,腕间玉镯随着叩首声轻响,竟真让优柔的李渊改了主意——最终只斥责太子,反削了李世民的兵权。那晚,秦王府的灯亮到天明,李世民摩挲着腰间佩剑,第一次看清权力场中,女人的眼泪比刀剑更伤人。 有人说李淳风的相术或许失了准头——所谓“凤仪之相”,哪是什么天命所归,不过是乱世中士族女子被推上前台的伪装。张婕妤自幼读的不是女诫,而是《战国策》,家族教她的不是三从四德,而是“如何用恩宠换家族存续”。她借着李渊的宠爱,为娘家谋来京兆尹的职位,甚至插手吏部铨选,连后宫之主窦皇后都要让她三分,可她算错了李世民的狠绝。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的厮杀声传到后宫时,张婕妤正在对镜描眉。螺子黛研得极细,眉笔刚划过眉峰,殿外传来“太子被射杀”的惊呼,她手一抖,笔杆“啪嗒”坠地,墨汁在菱花镜上晕开,像朵骤然枯萎的墨梅。她想起半月前还在为兄长谋官,那时总以为东宫会赢,却忘了李世民的刀,从来不长眼睛。 关陇士族在隋末唐初的势力盘根错节,李建成需要拉拢这些世家巩固储位,张婕妤的入宫便是这场政治交易的注脚。她为家族谋来的不仅是官职田宅,更是让旁支士族在权力天平上压向东宫的筹码;而李世民后来对关陇集团的打压,或许从他看清这枚“枕边棋子”的那一刻,就已埋下伏笔。 李世民登基后,没让张婕妤死,只是把她扔进了冷宫。那里没有菱花镜,只有一扇小窗,能看见墙外的石榴树年年开花。他偶尔路过,会想起李淳风那句话,忽然觉得“良配与否”从不由面相决定——张婕妤若无心依附东宫,或许能安稳度日;自己若不恋储位,或许不必背负弑兄之名。可权力场里,哪有“若”字? 深宫里的石榴花落了又开,张婕妤在冷院里数着日子时,李世民正在太极殿批改奏折。他们都曾被命运的棋盘推着走,一个想靠男人上位,一个想靠刀剑夺权,最后却都困在了自己选的结局里。李淳风当年没说透的,或许正是那句:在帝王家,人心从来比面相更难测,而权力,从来比情爱更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