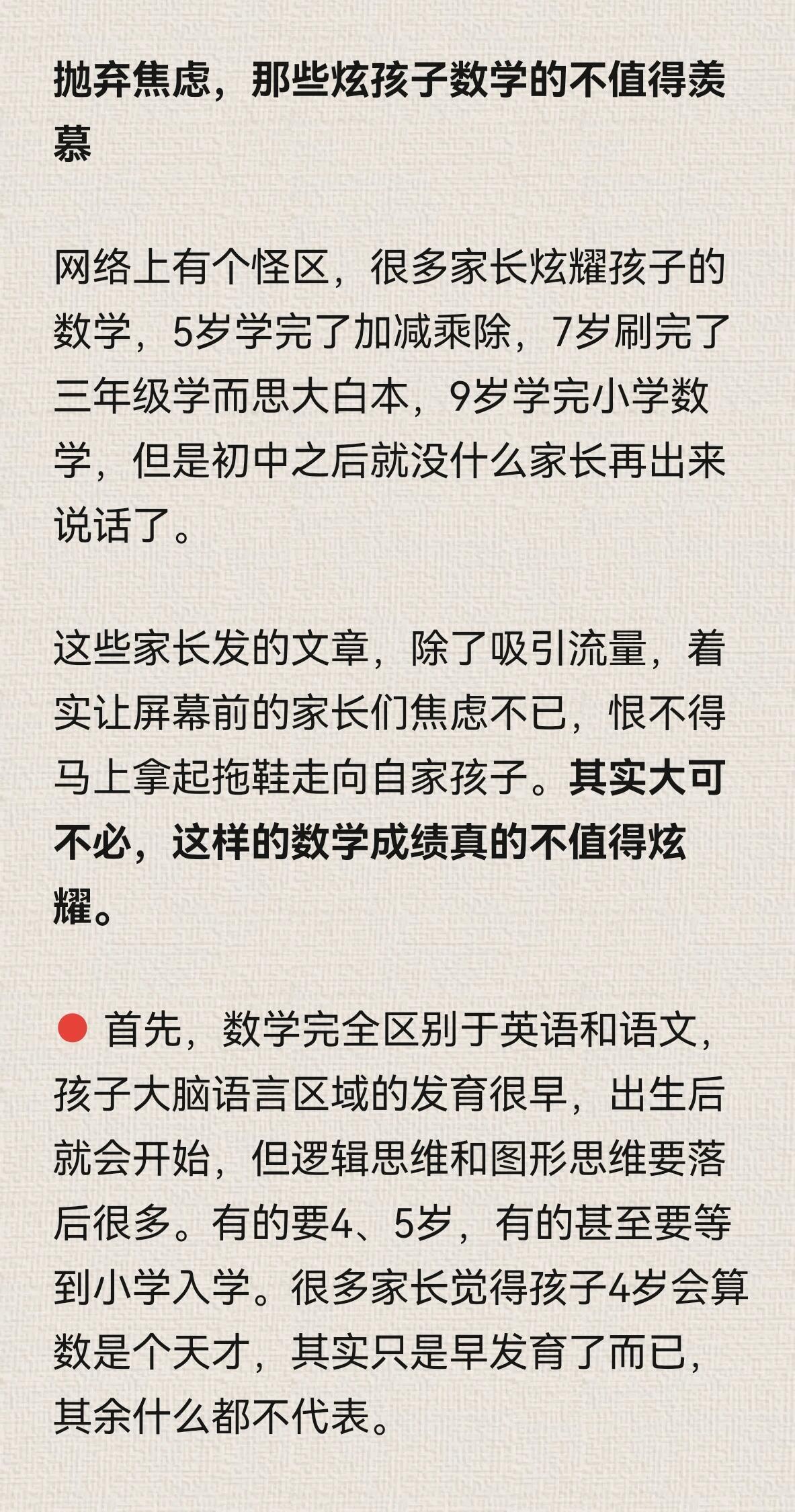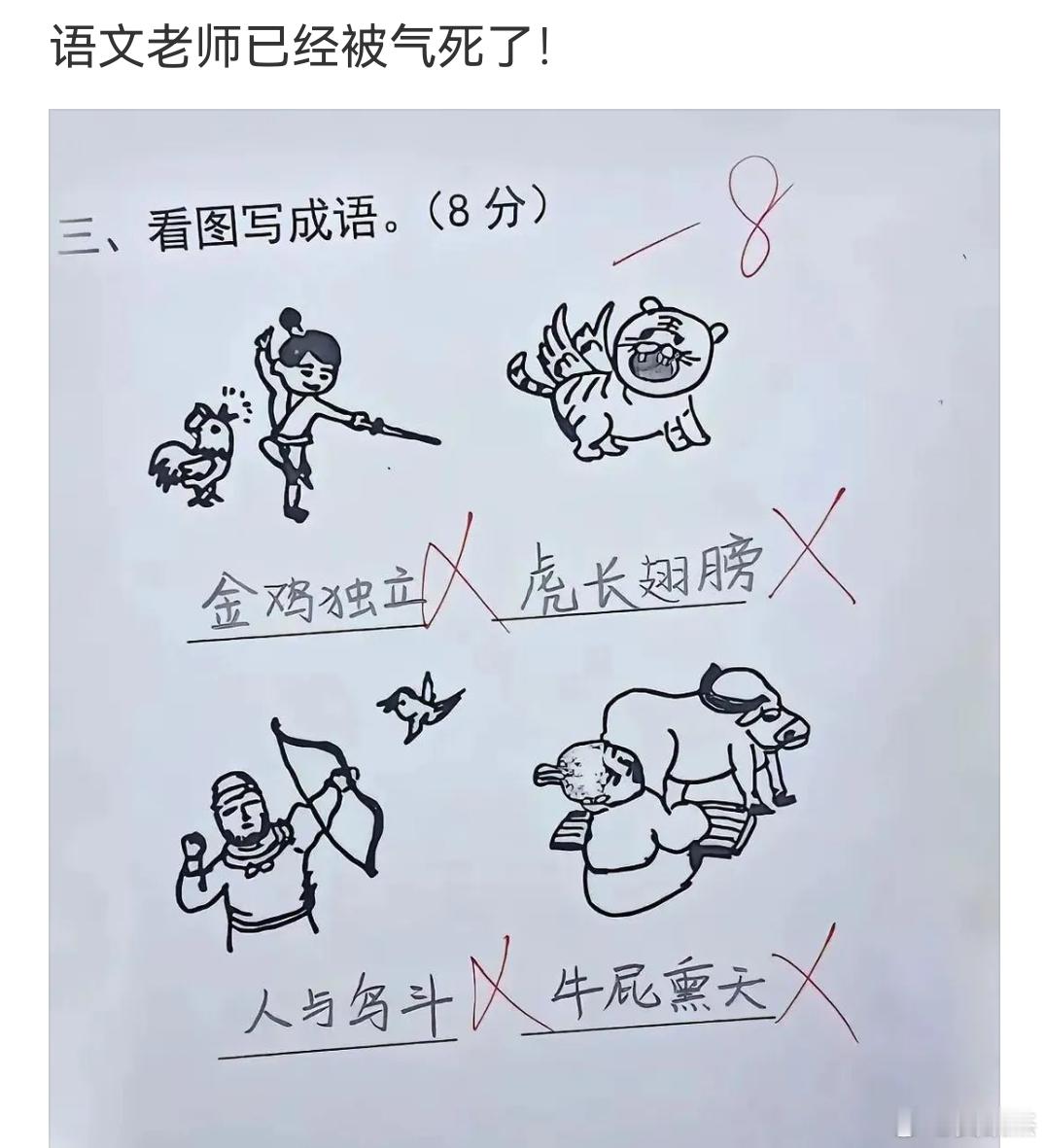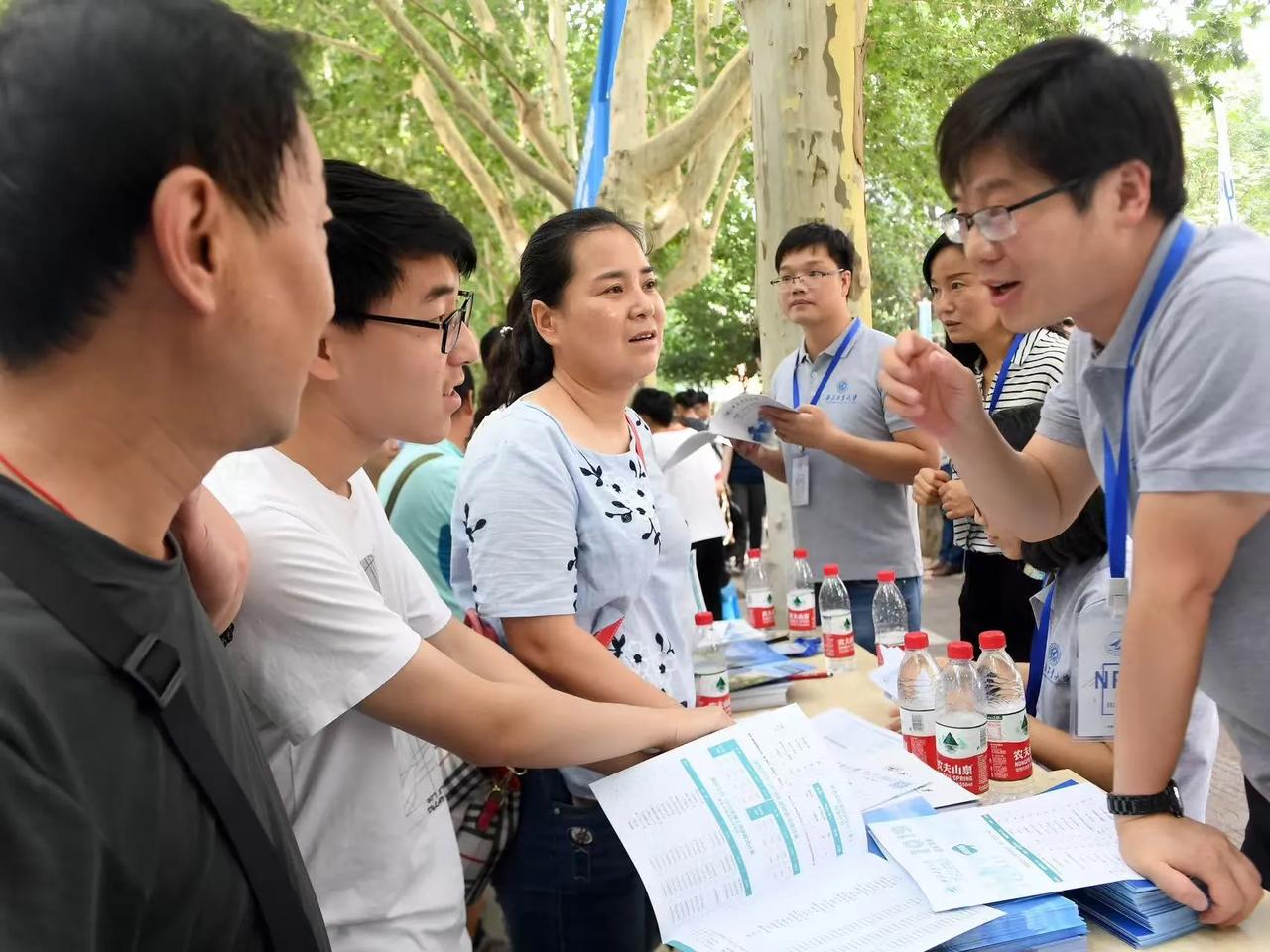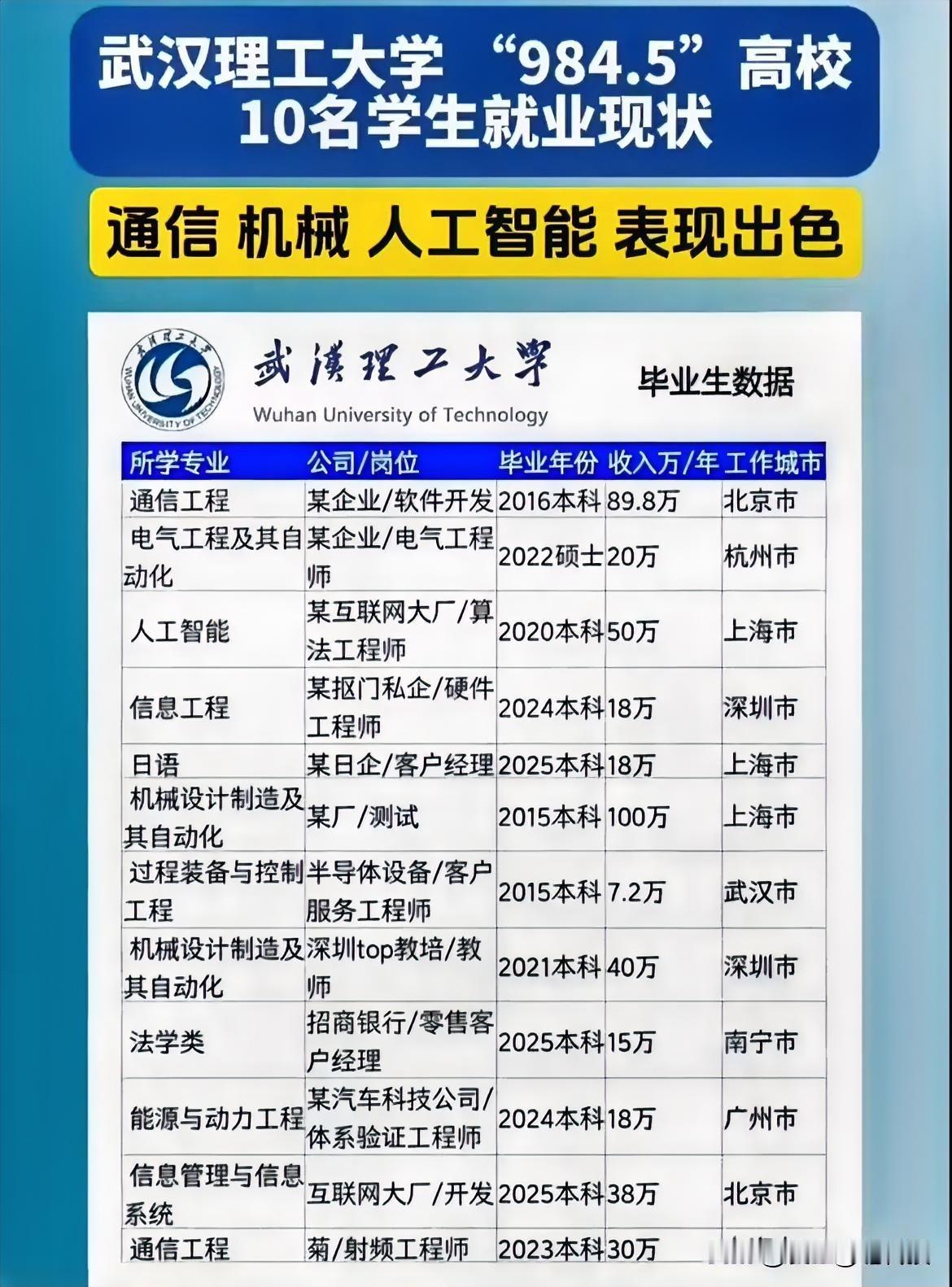今年我家儿子考了一所省内不错的211学校,儿子升学宴,姑姑包了两百块,准备退回去!真不是我嫌这钱少,说实在的,现在谁家办升学宴,随礼不兴三五百的?但这两百块攥我手里,比揣着块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烙铁还烫得慌。 八月末的升学宴,酒店包间里空调吹得人发冷,桌上的果盘里西瓜瓤都泛了白。 儿子穿着新衬衫给亲戚敬酒,到姑姑那桌时,她从蓝布包里掏出个红包,塞我手里——“给大侄子的,买点笔本。” 红包薄薄的,捏在指尖能摸到纸币折叠的硬边。旁边表妹悄悄碰我胳膊:“我妈非说两百够了,我说拿五百,她瞪我半天。” 我没接话,把红包塞进裤兜。那布料贴着大腿,凉丝丝的,心里却像揣了团火,烧得人坐立不安。 真不是嫌少。去年表妹出嫁,我包了八千;前年姑姑家盖房,我偷偷塞了两万。现在谁家升学宴随礼不兴三五百?可这两百块,怎么就比灶膛里的烙铁还烫? 散席时姑姑拉着儿子的手,絮絮叨叨嘱咐“大学里别熬夜”“食堂饭不好就回家吃”,眼角的皱纹里卡着点没擦干净的粉底。她转身要走,我摸出红包想塞回去,她手一挡,蓝布包带子在手腕上勒出道红印:“干啥?嫌少啊?” 我慌忙摆手,话卡在喉咙里——哪是嫌少?是二十年前那个雪天,她把我拉进供销社,掏出皱巴巴的五块钱买了双红棉鞋,自己脚上还穿着露脚趾的单鞋;是我高考失利躲在房里哭,她揣着热乎的糖糕来劝我,临走时往我枕头下塞了张百元钞,边角还沾着面粉。 那天晚上我翻旧相册,找到张泛黄的照片:十岁的我骑在姑姑肩上,她穿件洗褪色的蓝工装,手里攥着个冰棍,正往我嘴里送。照片背面有她歪歪扭扭的字:“妮儿要考大学,姑姑供你。” 第二天我没去退红包,提着水果篮去了姑姑家。门没关严,听见她在屋里跟姑父打电话:“……两百咋了?我这月药钱刚凑够,等发了退休金再给大侄子补个大的……”我推开门,看见桌上摆着个搪瓷缸,里面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缸沿豁了个口。 她看见我,手忙脚乱把手机藏起来,脸上堆起笑:“来啦?快坐。”我把水果篮放桌上,从包里掏出个信封塞她手里——不是退红包,是我该给她的。她死活不要,两人推搡间,我摸到她手腕上突出的骨头,像两段干柴。 最后我没再坚持退红包,只是把那两百块钱换成了崭新的票子,夹在她常看的《健康时报》里。她后来打电话骂我“瞎花钱”,声音却软乎乎的,像小时候给我讲故事时的语气。 现在那两百块还在我抽屉里,夹在儿子的录取通知书里。有时翻开看,纸币边角磨得起了毛,沾着点蓝布包上的线头——原来亲情从不是天平两端的数字,是她藏在皱纹里的牵挂,是我攥在手心的愧疚,是二十年前那个雪天,红棉鞋里暖烘烘的温度。 下次去看姑姑,得记得给她买双软和的鞋。
抛弃焦虑,那些炫孩子数学的不值得羡慕
【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