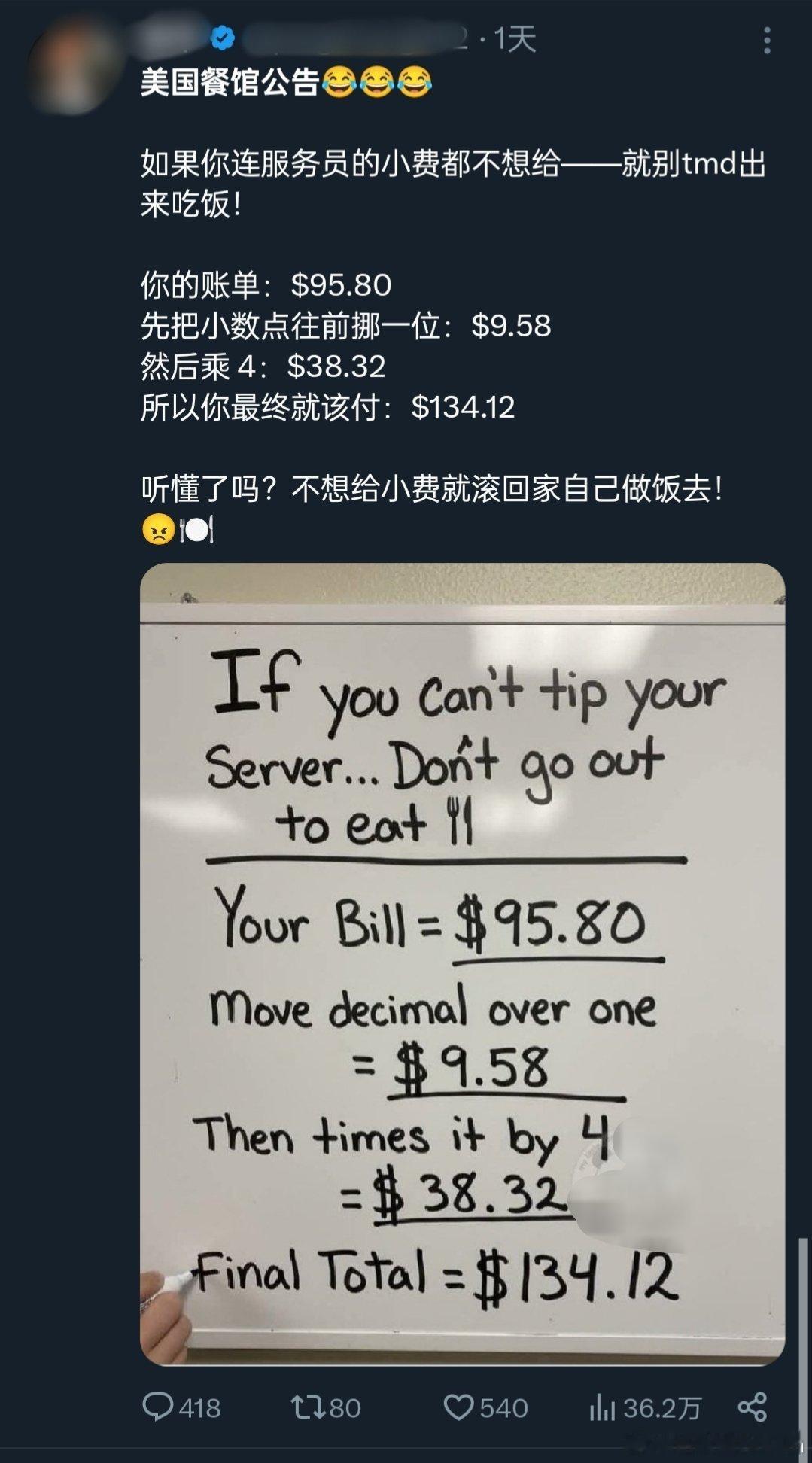年初的时候,我跟老婆商量,准备清明祭祖那天,请族里的男女老幼去镇上的餐馆吃一顿。老婆听了没反对,只说这事得提前跟族长说一声,再把各家的人数统计好,不然餐馆那边不好留位置。我觉得她说得对,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族长家。 年初天还冷着,堂屋的煤炉烧得正旺,我蹲在炉边烤手,跟老婆琢磨着清明祭祖的事。 “要不今年别各家自己弄了,”我搓着手说,“请族里老老少少去镇上馆子吃一顿,热闹。” 老婆没搭腔,手里正剥着年前晒的南瓜子,壳子在竹篮里堆成小山。 过了好一会儿,她把最后一瓣瓜子仁扔进碗里,“这事得跟族长说一声,”声音闷闷的,“还得挨家挨户问清楚人头数,馆子要提前订,不然清明那天挤不下。” 我觉得在理,第二天鸡刚叫头遍,揣了包年前留的好茶叶就往族长家走。 田埂上还有残雪没化,踩上去咯吱响,远处祖坟山的松柏影影绰绰,像蹲在那儿的老祖宗们。 族长家的木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里头传来他咳嗽的声音——这老爷子开春就犯了支气管炎,说话总带着痰音。 “进来吧,门没锁。” 我推门进去,灶房飘来柴火味,族长正蹲在灶台前添柴,锅里咕嘟咕嘟煮着啥,热气在窗玻璃上凝成水珠。 “叔,起得早啊。”我把茶叶放在八仙桌上,桌角的搪瓷缸子缺了个口,里头的茶渍积得发黑。 族长直起腰,拿围裙擦着手,“啥事?”他没看我,眼睛盯着锅里翻腾的萝卜,“清明的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您咋知道?” 他咧嘴笑,露出半颗镶的金牙,“你爹活着时就好张罗,你随他。”说着掀开锅盖,白气扑了满脸,“萝卜炖骨头,你婶子说给你留了碗。” 我没接话,把请吃饭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说完心里有点打鼓——族里老人多,会不会嫌下馆子破了规矩? 族长没立刻应声,从碗柜里摸出两个粗瓷碗,盛了萝卜汤,又从樟木箱底翻出个蓝布皮本子,边角都磨卷了。 “你看,”他翻到去年清明那页,“老三家两口,老四家带俩娃,加上你婶子娘家来的亲戚,一共三十二口。”字是用毛笔写的,歪歪扭扭却清楚。 “馆子定哪家?”他忽然问,舀了勺汤吹着,“东街那家‘聚福楼’?去年你堂哥嫁闺女,在那儿摆的酒,菜量足。” 我愣了,原以为他会说“老规矩得守”,没想到连馆子都替我想了。 “我这就去统计人数?” “不用,”族长摆摆手,“本子上记着呢,每年就添几个新出生的娃,走了的老人我也划掉了。”他指着本子上一个红圈,“你二伯去年冬天没了,今年就别算他了。” 我看着那红圈,心里有点发酸,去年祭祖时二伯还拉着我手说“明年多带瓶好酒”。 “钱咋算?”族长忽然问,眼睛亮了亮,“各家摊?还是你全出?” “我出,”我没多想,“一年就这一回,花不了多少。” 族长放下碗,筷子在桌上顿了顿,“别,”他声音沉下来,“各家男丁凑份子,女眷带点自家做的清明粿,孩子们跟大人走——老规矩,祭祖是全族的事,哪能让一家扛着?” 我忽然想起老婆昨天说的“提前跟族长说”,原来她早料到族长会这么安排。 从族长家出来时,太阳已经爬到竹竿顶上,田埂上的雪开始化了,湿了鞋尖。 回家跟老婆说这事,她正弯腰给煤炉换煤,火钳碰着炉壁当啷响。 “我就说族长会有章程,”她直起身,脸上沾了点黑灰,“你以为请吃饭是简单事?人多了坐不下,钱少了不够花,老的小的口味还不一样——得亏你去问了。” 我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族长给的蓝布本子,翻到第一页,是二十年前的字迹,写着“清明祭祖,到会男丁十七人,女眷九人,孩童五人”。 本子的最后一页空着,族长说等今年吃完了,让我把新人数写上。 现在离清明还有一个月,我每天晚上都翻这本子,数着上面的名字,好像那些没见过的祖宗,都在纸页上看着我笑。 不知道到时候聚福楼的包厢够不够大,也不知道各家的清明粿会不会带多了——不过族长说了,人齐了,比啥都强。
年初的时候,我跟老婆商量,准备清明祭祖那天,请族里的男女老幼去镇上的餐馆吃一顿。
正能量松鼠
2025-12-03 12:39:12
0
阅读: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