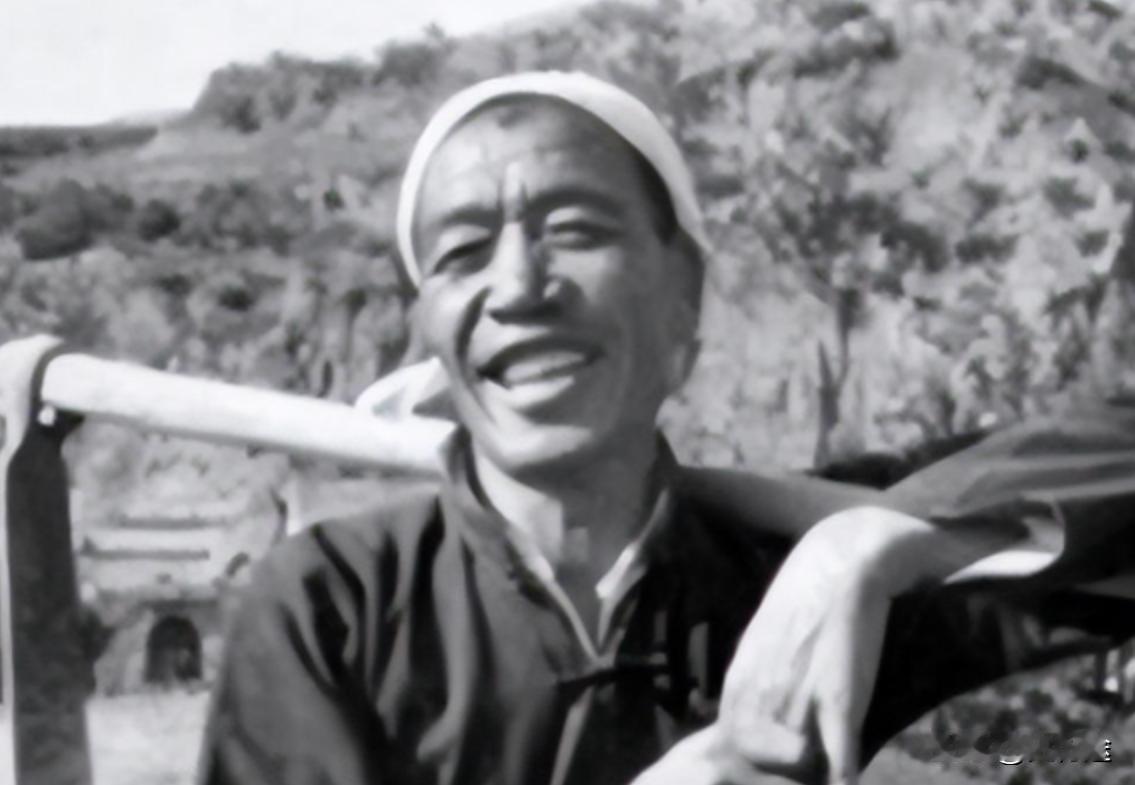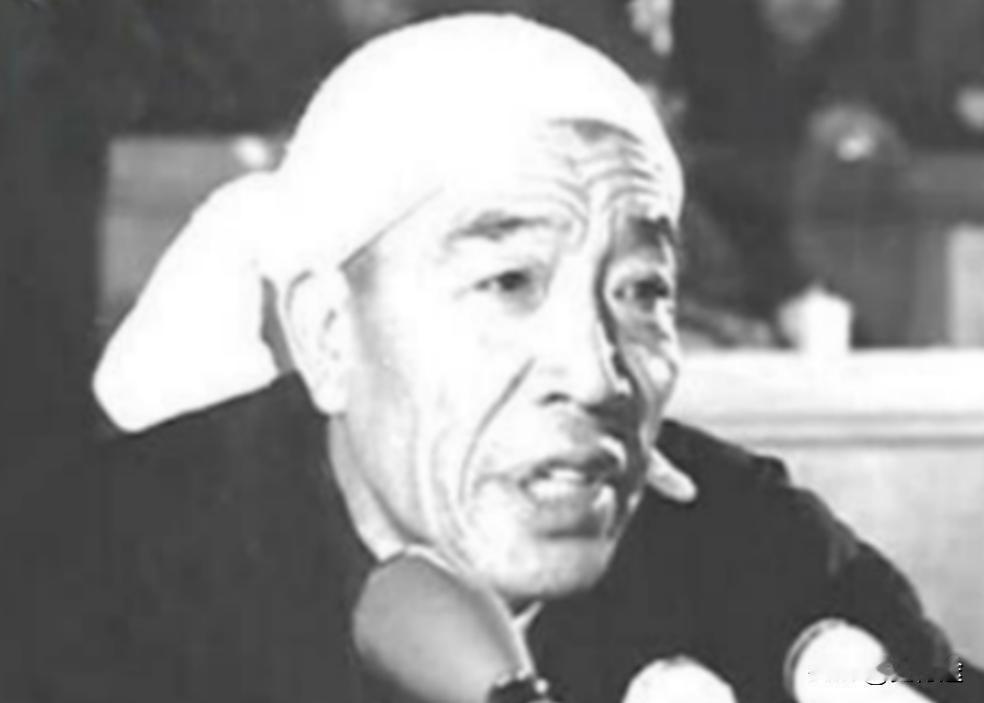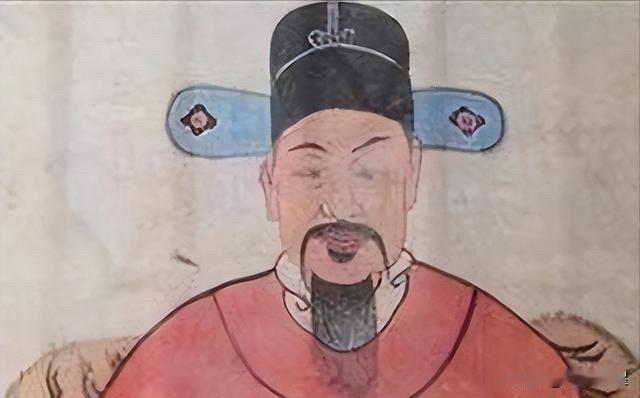一九七九年,陈永贵回到昔阳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说:“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 一九七九年,昔阳县的会场里人坐得满满。 陈永贵在台上,说出那句后来被记住的话:“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语气不重,意思不轻,听得懂的人都明白,他是在替那段岁月讲句公道话,也在给大寨和自己找个站得住的说法:这面旗还得扛,只是往后怎么扛,要看脚下的路。 解放前的大寨,是昔阳县角落里的穷山村,七沟八梁一面坡,风一刮,土顺沟往下跑。 村里老人一提旧日子,总爱先叹一口气,再念“三穷五多”:人穷,地穷,村子穷;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咬牙卖儿卖女的多,想不开寻死上吊的也多。 几句顺口溜,把那时的窘相捏得真切。 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党支部把眼睛先盯在地上。 家伙什不多,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撅头、两个箩筐,人往坡上一站,就是一台“土机器”。 陈永贵领着全村,白日黑夜往山上跑,把河沟一点点垫高,把陡坡一层层削平,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成一块块梯田。 十多年下来,大寨有了稳产高产田,亩产能上千斤,口粮不愁,每年还能往国家交二十万斤粮食,在周边村子眼里,这就是硬本事。 一九六三年,暴雨连着几天砸下。 山流冲下来,地冲塌,房倒,窑洞塌,十年心血眼看要被水卷干净。上级很快派人带着钱、粮、物进村安慰。 大寨人连着几晚开会,最后咬牙做了个外人听着有点“轴”的决定:不收。 党支部一班人领着大家再上山,重新量坡、打埂、垒墙、修地,用了一年时间,一个新大寨又立在梁上,“战天斗地”四个字从此扣在村名上。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一下从县里蹿到全国。 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一百二十多位老一辈领导人前后到村里看,通往大寨的公路两侧竖满标语牌,毛主席语录写得红火。 后来四五十岁那拨人,只要车一开上那条路,瞟一眼这些字,就能把六七十年代的场景翻出来。 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走到国务院副总理,可有空还往村里跑,跟社员一块下地干。一九八六年去世前,他早早开口:人走了也得葬在大寨,守着这片地。 时间拨到九十年代,大寨碰到的新难题,叫“发展”。 传统种地那一套,已经托不起全村人的日子,自然条件摆在那儿,坡还是那几个坡,水也就那点水,光盯着粮食产量,钱袋子鼓不起来。 村里做了学习和调研,慢慢认定:得调产业、改体制。 新一届班子里,郭凤莲顶在前面,一九九二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挂牌,村里开始引项目、引人才、引资金,不再只守着几亩田看天色。 厂子一间接一间建起来:水泥公司、酒业公司、制衣公司、食品厂、煤矿企业,名字普通,大寨人的身份变了,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股民。大寨核桃露就在这阵折腾里冒出来,瓶子上印着“大寨”两个字,从地方小饮料做成全国认得的牌子。再听人提“农业学大寨”,已经很难只当作一句政治口号。 山上也被重新打量,大寨人认准一条: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山上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把不少坡地从粮田退成树林。顺着山势建起森林公园,游步道贴着当年的梯田线盘上去。知青林、军民池、周恩来休息厅、郭沫若诗碑、孙谦纪念地,被一条条小路串在一起,成了“边走边讲”的路线。借着“大寨”这个老牌子,村里把旅游业做起来,国内外游客一拨一拨往山里钻。 展览馆里,两面墙对着看,一面写着过去的“三穷五多”,一面写着今天的“三有三不”。小有教,娃上学不为学费发愁;老有靠,养老保险托住晚年;考有奖,谁家孩子考上大学、大专、中专,村集体拿出真金白银发奖学金。 吃水不用吊,自来水早进了院;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常在村口叫着响;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主动上门。 把这些和当年的“当长工、打短工、卖儿、上吊”放在一起,对比已经很明显。 村里的样子,也和老照片里的印象差出一大截。窑洞还在,不过排得顺溜,旁边多出一排排错落的别墅楼,街道整洁,学校楼层高,教室里电器设备齐全,不少院子里停着小汽车。村外望出去,庄稼是一片规整的绿,山上林子郁郁葱葱,池水闪着光,村办企业的院子里机器声一阵接一阵。沿着林间山路往虎头山走,人造山林把山包得严严实实,很难再从肉眼里寻出当年梯田的折痕。 外地来的基层党员,常挑着“七一”前后来大寨学习,从山路走到展览馆,再走到知青林、军民池,最后在陈永贵墓前站一会。 眼前是一座已经实现“三有三不”的新大寨,耳边听到的,是过去“三穷五多”的旧故事。 很多人心里都会琢磨:这么一个当年穷到卖儿的山村,怎么一步步走到全国皆知,又怎么在九十年代之后,从政治样板拐到了经济发展这条路上,还把生态这张牌打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