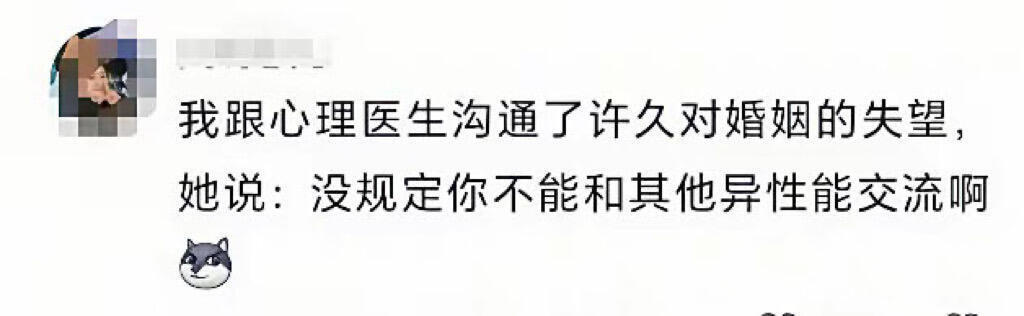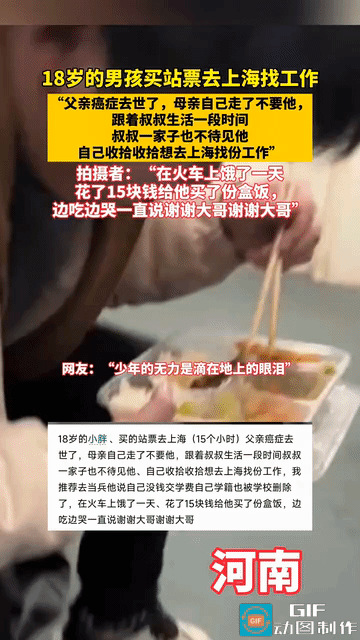航天专家罗健夫,从发现癌症到去世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去世后,医生根据他的遗愿解剖他的遗体时才发现,他的体内竟布满了肿瘤! 1982年6月16日,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解剖室空气沉闷。医护人员打开遗体的一瞬间,沉默在房间里蔓延开来。负责病理的医生看着肝脏、脊柱和骨髓上密密麻麻的病灶,神情复杂,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罗健夫把生命的最后4个月交给了实验室,把最后的愿望交给了医学研究,没有留下半句抱怨。 事情的真正起点要更早一些。1965年,罗健夫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主动要求进入航天工业部第十一研究院,也就是承担航天飞行器信息与绘图系统研发的科研单位。 那年十一院刚成立不久,许多设备还没有装好。他被安排进入704所的技术室,接触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图形发生器”系统。 那时中国连参照资料都没有,只能靠自己从零设计。604宿舍里到处堆着废旧电线、残损齿轮,还有从废品站捡回来的电机骨架。 罗健夫和同事李绍钧、郭庆三围着旧机床测试伺服装置,经常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夏天图纸被汗水浸得卷边,冬天大伙穿着棉军装一样画图。 1972年样机终于跑起来了,步进系统稳定输出,误差控制在毫米内,十一院的老专家当时激动得敲桌子。 研制成功后,有评委提出把成果一等奖给他,罗健夫推了回去。他说年轻同事更需要认可,奖金也都换成了专业书籍放在公共书架。 时间越往后,项目越多,他的角色从技术员变成了核心工程师。 1978年,新型号任务下达,他接手第二代图形发生器,总装形式改成多轴联动,还要兼容新的数字输入模块,难度比第一代高出很多。 十一院当时正处在科研体系重建期,预算紧、任务重,许多关键芯片被封锁。罗健夫提出采取分布式模块体系,用分级逻辑绕过进口芯片。这是个冒风险的决定,但他铁了心要把核心系统做成自主结构。 技术室的行军床成了他的常驻位置,项目笔记摞在枕头边,几本旧资料翻得卷了角。 1979年末他就开始觉得腰疼,以为是常年的伏案落下的毛病。1980年疼得厉害,他还是只用热水袋敷敷继续干活。 等到1982年2月在实验室晕倒,被送往医院时,晚期癌症已经扩散。主治医生给出“一个月”的判断,他却只问能不能再争取三个月,因为第二代图形发生器只差最后调试。医生当时没有说穿,只点了点头。 诊断书被他锁在实验室边上的铁柜里。那段时间,他靠止痛片扛着身体,不再能长时间站立,就扶着桌沿指挥调参。他常常半夜还在画结构图,痛得全身发抖也没松手。704所的年轻人看见他额头滚下的汗,心里发酸,想劝他休息,他却一句“科研不能停”。 第二代图形发生器最终顺利通过鉴定。那天罗健夫在操作台旁坐了很久,像在等一件事落地一样。项目结束后不到一周,他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去世前,他把妻子叫到床边,交代把自己的科研笔记交回单位。那是他从1965年工作到1982年积累下来的全部技术心得。 他想把晚期癌症的身体状况留给医学研究,也想把几十年的工程经验留给后辈。他没提过自己的辛苦,只说“别浪费了这些资料”。 整理遗物的人发现,他的衣柜里只有几件打了补丁的旧衬衣。工资条薄得吓人,新房的分配表上,他在备注栏写着“让给新来的大学生”。 抽屉里堆着几摞泛黄的计算纸,全是图形机的算法草稿。 罗健夫留下的图形发生器系统后来被推广到导弹、卫星和飞行器的设计制造中,节省了上亿元经费,也让中国在精密制造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1983年,罗健夫被追授“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而他留下的那些笔记,被十一院人称为“704宝册”,至今仍被翻阅。 罗健夫他把一生的光都放进图纸里,把最痛的日子留给工作,把最重要的遗愿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