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听说妻子彭德华要来北京,连夜把家里的大床换成了单人床,当着邻居的面撂下狠话:“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 谁也没想到,这张单人床后来摆了三十年,直到彭德华走了都没再合起来。 1964年的北京,胡同里的槐花都落尽了,空气里还飘着点甜丝丝的味儿。季羡林从学校回来,刚进院门就被邻居张大妈拽住:“季教授,听说彭大姐要从山东老家来了?这下好了,家里总算有个拾掇的人了。” 季羡林“嗯”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脚步没停就进了屋。屋里那张红木大床还是当年单位分房时配的,占了小半间卧室。他瞅着那床,眉头拧成个疙瘩,转身就往胡同口的木器店跑。 “给我来张单人床,越窄越好,今晚就得送货。”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语气急得很。店主认识他,知道是北大的大教授,笑着打趣:“您这是要给客人加床?”季羡林没接话,掏出钱拍在柜台上:“别问了,赶紧送。” 傍晚的时候,两个师傅扛着张铁架单人床进了院,叮叮当当拆了大床,把单人床安在了原来的位置。邻居们都扒着门缝看,不知道这大教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赶上彭德华带着一篮子山东大枣进门,脚刚迈过门槛,就看见那张小得只能蜷着腿睡的单人床,手里的篮子“哐当”掉在地上,枣滚了一地。她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裹着小脚,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旅途的尘土,瞅着那床,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这床就够我一个人睡。”季羡林背对着她,声音硬邦邦的,“你来了就睡外屋的沙发,反正你也住不了几天。” 邻居王大爷刚好路过,听见这话,忍不住插嘴:“季先生,哪有这么待自家媳妇的?” 季羡林猛地转过身,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对着院里的人就喊:“我就是死也不和她睡!” 这话像块石头扔进水塘,炸得街坊四邻都没了声。彭德华蹲在地上捡枣,手哆哆嗦嗦的,捡着捡着,眼泪就掉在枣上,把土都洇湿了。 谁都知道这两口子过得拧巴。季羡林是留过洋的大教授,读的是梵文,写的是洋文章;彭德华是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围着灶台转。当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拜堂那天他都没掀开盖头,第二天就躲回了学校。这几十年,一个在北平念书、留洋、教书,一个在山东老家伺候公婆、拉扯孩子,聚少离多,像两条平行线,好不容易有了交集,却碰出这么个火花。 彭德华在沙发上蜷了三个多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季羡林的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砚台里的墨总是磨得稠稠的,桌上的热茶从没凉过。季羡林呢,除了吃饭,基本不跟她说话,晚上关了书房门,就听着外屋沙发“吱呀”响,他知道她没睡好,却硬是没挪过一步。 有回彭德华得了风寒,咳得直不起腰,季羡林半夜被咳醒,在屋里转了三圈,最后还是拉开门,往她身上盖了件棉袄。彭德华迷迷糊糊抓住他的手,他像被烫着似的缩回手,摔上门就再也没出来。 后来孩子们来北京,看见那单人床都直皱眉:“爸,换张大的吧,妈睡沙发太遭罪。”季羡林把眼一瞪:“她愿意!”其实他夜里看书,总听见外屋有动静,彭德华总在偷偷捶腰,沙发太硬,她那把老骨头哪扛得住。 就这么着,那张单人床在卧室里待了一年又一年。季羡林的书越堆越多,把床尾都占了一半,他就侧着身睡;冬天冷,他就在床边堆上棉被,像堵墙似的。彭德华呢,从不说啥,只是每年来的时候,都会把单人床的铁架子擦得锃亮,床板缝里的灰都抠得干干净净。 1994年秋天,彭德华走了。那天季羡林没哭,就是坐在书房里,对着那张小床发呆。孩子们要把床扔了,他不让:“放着吧。” 后来有人问他,这辈子最悔的事是啥。他想了想说:“年轻时总觉得日子长,等明白过来,人没了。” 那床就那么摆着,摆了三十年,从青丝摆到白头。床板上的漆掉了又补,铁架上的锈生了又擦,像个沉默的见证者,看着一个倔老头和一个老妇人,用最拧巴的方式,过了一辈子。胡同里的槐花开了又落,季羡林还是每天在那单人床上睡觉,只是夜里翻身时,总觉得床底下,好像还藏着当年没捡完的山东大枣,甜丝丝的,带着点土腥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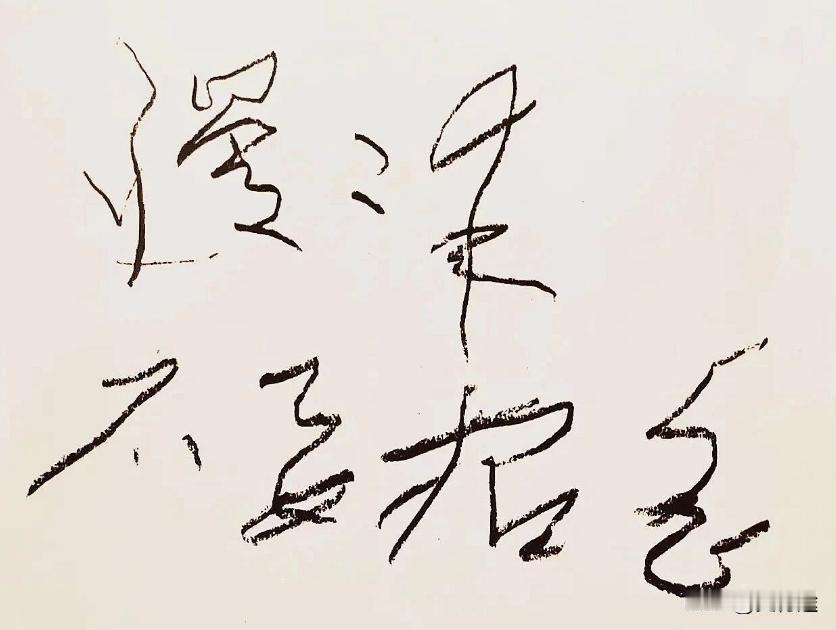




水利水利水利
胡编!新娘盖头都没接,夫妻没有接触,孩子们是哪来的?
云彩 回复 11-22 22:31
天上掉下来的
用户17xxx64 回复 11-28 12:59
他是请别人代劳的吧
用户10xxx70
瞎编造谣也要负责任的![点踩]
唾面自干 回复 11-23 06:34
大概率是真事,不然他儿子怎么会这样狠他爸一辈子的呢
用户43xxx40 回复 11-28 09:30
大概率是真的,还有鲁迅徐志摩……。那个时代的人,都差不多的,父母包办婚姻,女的大多都很本分,男的反而向往自由婚姻,对抗父母包办,迁怒于原配……;和现在相反,婚姻自由,男的背负养家重任,女的不本分的多……。
用户11xxx31
两个人怎么会有孩子的?
九斤老太
这么大的仇,能写写为什么吗?
清然
那就没必要看他写的文章了
立刻
孩子们哪来的?
芭蕉夜雨
负心多是读书人
兔兔 回复 11-28 06:46
这句话不是这么用的。没有读书人参与,新中国能成立吗
用户16xxx21
我是 70 后, 曾经是我们认为的大师,在 90-00 后眼里没有光了…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不用着急让所有人认识你,可能你认识的在后来人的认为里是…什么呢…渣!!!
有所谓 回复 大帝 11-28 08:50
听说鲁也是包办,但是人家要离婚,只是原配不同意。和这个故意折磨还是不同的。
大帝 回复 11-28 01:30
和鲁迅对待原配一样
拔总
好像他那老爹也是一路货色
玉哥
隔壁老王的
玉茶壶551014
一个老公知和胡适有的一拼!
用户10xxx10
自己无能反抗不了父母就迁怒到无辜人身上,要是婚前就不同意这女人嫁给别人至少比跟你过强,什么玩意儿
用户13xxx98
公知鼻祖
枫叶 回复 11-23 08:51
呼死他,欺负我们山东人
用户10xxx13 回复 枫叶 11-28 09:31
季也是你们山东人。
用户10xxx88
盖头都没掀能有孩子吗
用户10xxx86
哎,那个年代的文人雅士,背后的那点私事,还真不少,就这两年去读一些个人传记,发现冷脸相对原配的不是少数,徐志摩,老舍~都打破了我对他们的想象,如果不是夫妻,可能还会认为对方是个好人,这样,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等活明白了,一切都晚了
芭蕉夜雨
负心多是读书少
红鲱鱼
老爷子学问做得好,对家人有点太冷了。
秀秀
孩子哪来的[哭笑不得][哭笑不得]
烔炀
呸
用户14xxx56
孩子应该是隔壁的吧
淡定
狗屁不通。怎么能上去的,主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