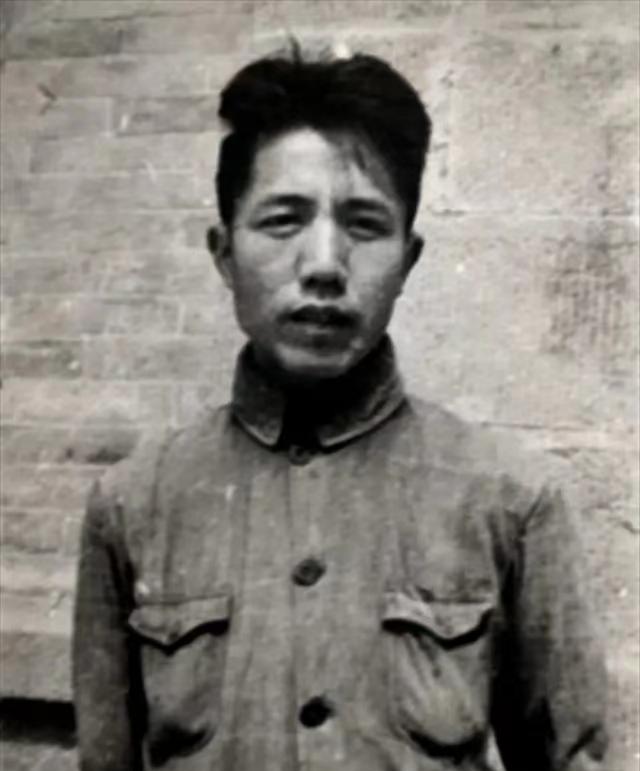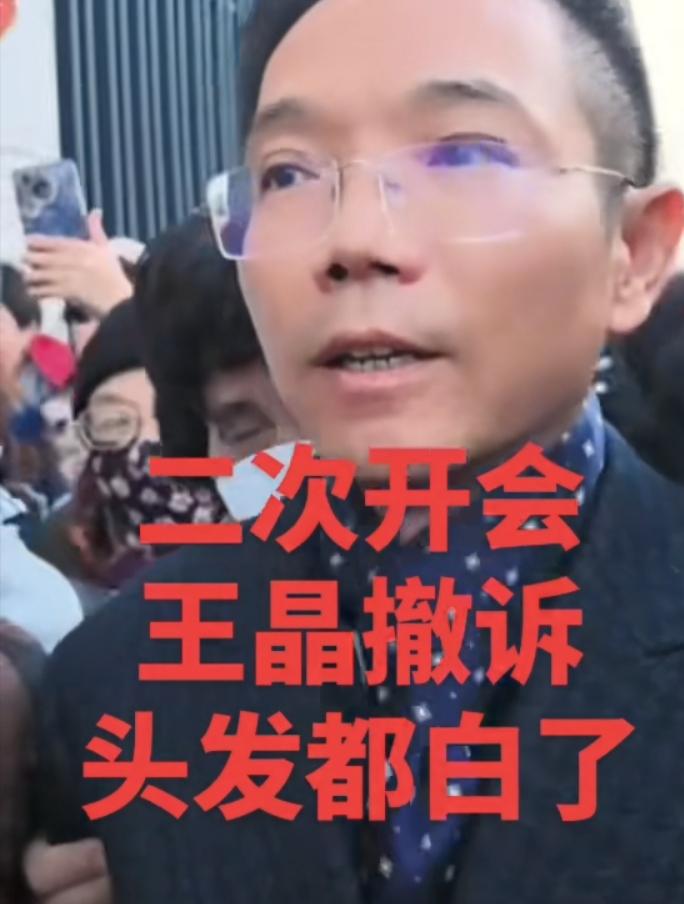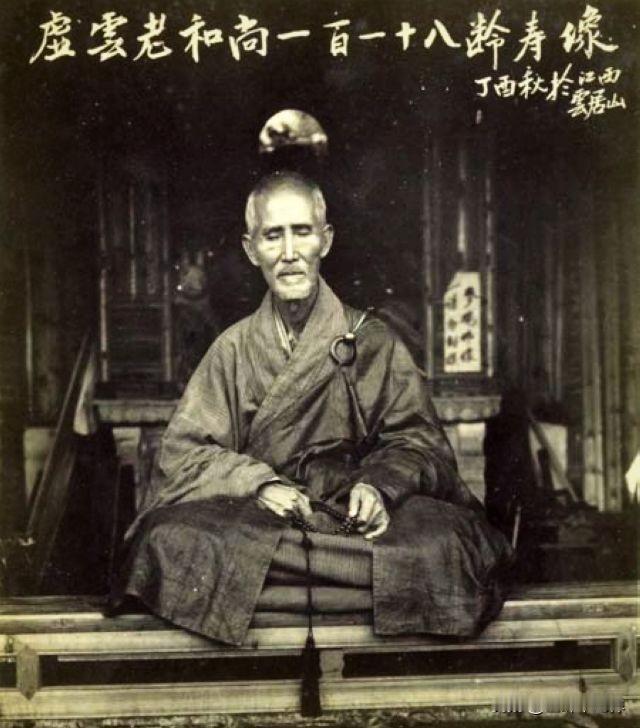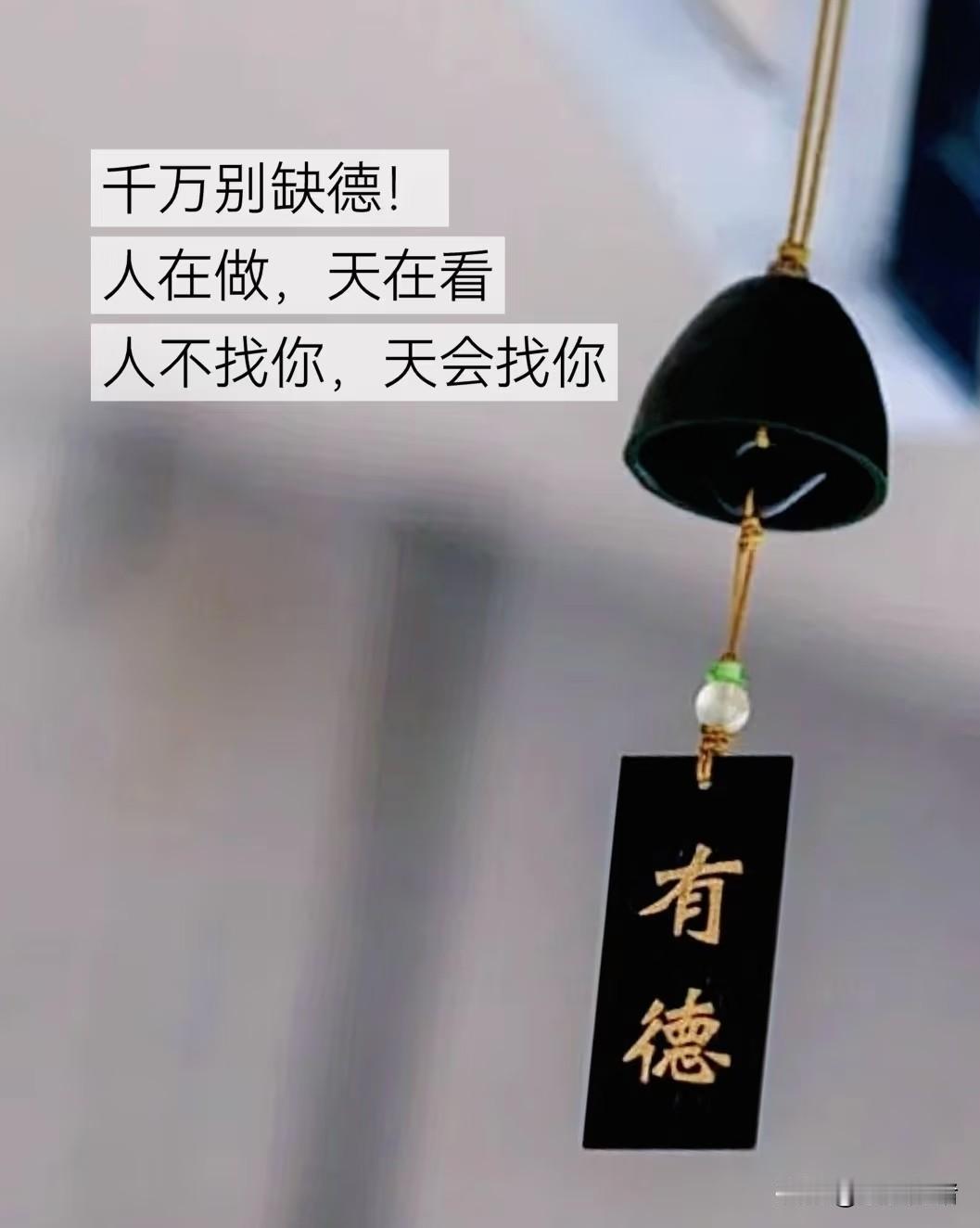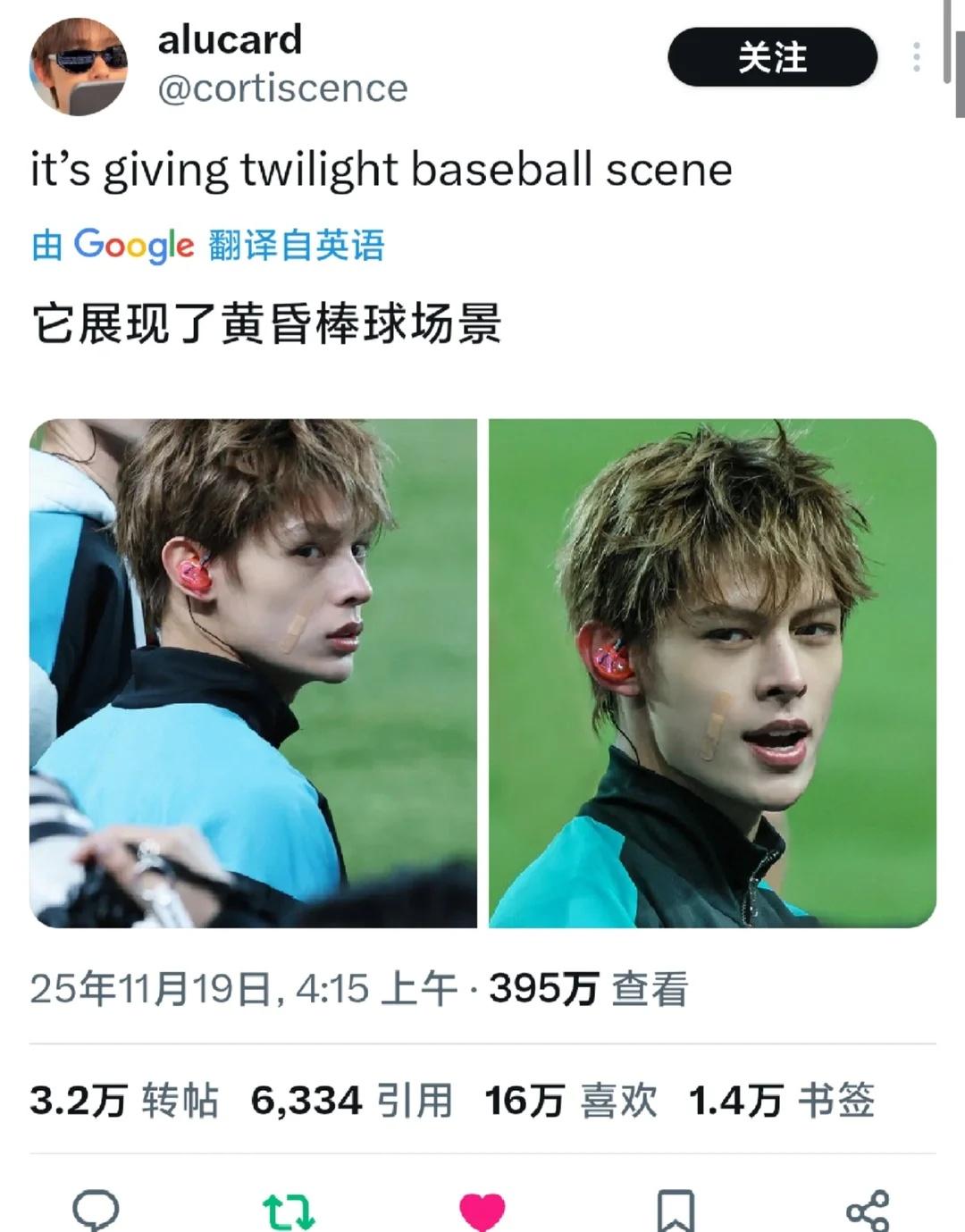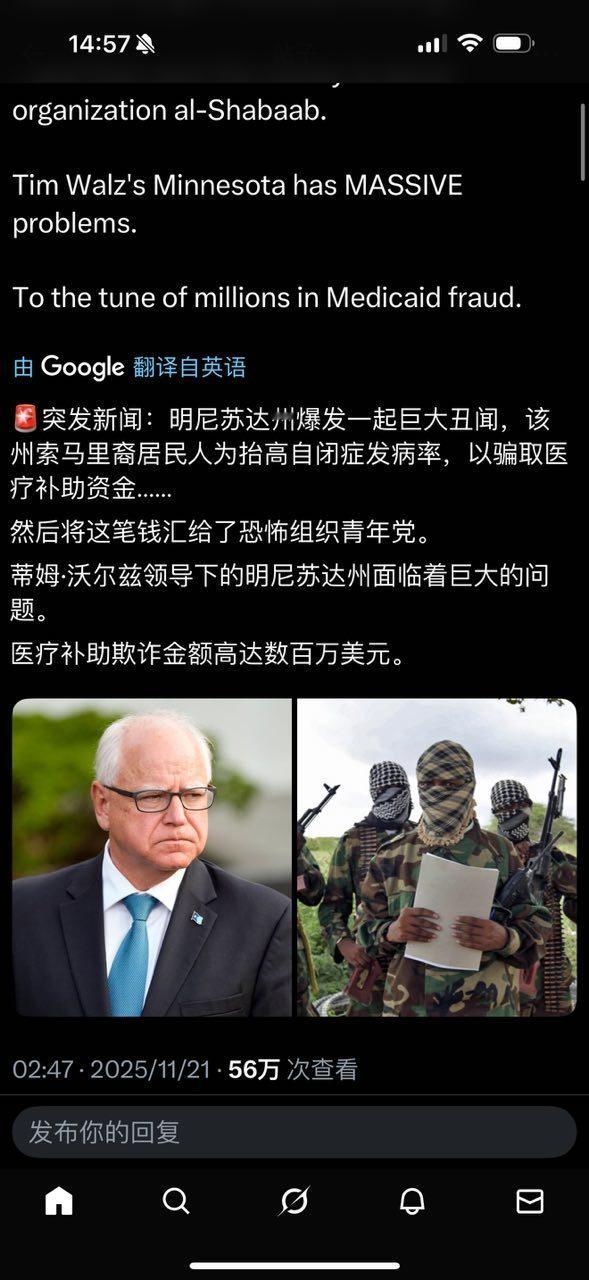1980年春末周扬回到湖南益阳,这是他许久未归的故乡,青砖灰瓦、老街旧巷依旧如梦初醒般存在着,但人事已非。 彼时他身为全国知名作家,政坛文坛皆有一席之地,回乡探亲本是寻常之举,同行者也不过是几位老朋友,行程紧凑,没想到途中插入了一桩“旧事”——他执意要顺道去看一座早年故人的墓,那人叫吴淑媛。 这名字在当地人耳中早已淡去,甚至不少年轻人根本没听过,但在周扬心里,却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 据说周扬那天情绪反常,在车上沉默许久,抵达墓地附近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闷雷滚滚,随后暴雨倾盆,他撑着伞站在墓地入口不到两分钟,脸色发白,突然转身就走,不顾同行人的呼唤,也不再回头。 没人知道那一刻他想起了什么,但回忆起他与吴淑媛的往事,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周扬与吴淑媛的关系,外界所知甚少,吴淑媛早逝,文献记录也极为稀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详细资料,但在老一辈人中,却流传着一些只言片语——他们年轻时曾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两人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周扬初入文坛,意气风发,而吴淑媛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女青年,长相秀丽,性格温婉,曾在省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获得不少好评。 两人因一次文学沙龙结识,随后频繁通信,交往甚密,有人回忆说,吴淑媛曾在信里写道:“扬兄之文,犹如春水东流,温润我心。” 那几年周扬频繁回益阳,每次都住得很久,街坊邻里都看在眼里,有人见过他与吴淑媛在傍晚的河堤边散步,也有人说他常在她家中小坐至深夜,可惜天不遂人愿,这段关系最终无疾而终。 有人说是因为政治风向突变,周扬北上发展;也有人说是吴淑媛家中出了事,被迫与他断了联系,更有甚者传言,吴淑媛曾为周扬生下一个孩子,但胎儿难产夭折,之后她身体每况愈下,不久便病逝,无论哪种说法,周扬从未公开回应。 那次回乡周扬的确有探亲之名,但主动提出“顺道去看吴淑媛的墓”,却让同行人都有些意外,毕竟这事他从未提起过,甚至没人知道他记得她。 据一位老友回忆,当时车子驶入益阳郊区已是午后,他们绕过一片老树林,走入一条小路,尽头是一块荒僻的小山坡,吴淑媛的墓就在那里,碑上字迹已模糊,但依稀可见“民国三十八年卒”几个字。 刚到墓前,天忽然变阴,风一阵紧似一阵,雷声在山间回荡,周扬站在墓前不到一分钟,突然仰头看天,神情变得极其复杂,他没说一句话,突然转身就走,甚至连头也不回。 同行者也被这突变的天气吓到,赶紧跟上,有人试图问他为什么不祭拜,但他只是摆手,声音低得几不可闻:“不能拜,不敢拜。” 他为什么不敢靠近她的墓?这一点至今仍无人能够解释清楚,但如果把两人的过往拼凑起来,答案也许就在其中。 吴淑媛的死因至今成谜,有人说她是病亡,但也有传闻称她晚年精神恍惚,常在街头低声自语,像是在念着某个人的名字,她死后无人照料,连下葬都是邻居凑钱安葬的,周扬那年已经是风云人物,却没有出面。 而那块墓碑,可能正是当年他亲手请人刻的,墓地的选址也颇为特别,远离人群,隐蔽安静,据说刻碑的师傅至今还记得那年一个穿中山装的男子,亲自挑选石料,要求只写名字,不留任何身份信息。 多年之后,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想要面对,却在雷雨交加中临阵退缩,有人相信,那场大雨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天意”的警告。 周扬此后再未提起吴淑媛,那次墓地之行,也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被刻意蒙尘的记忆点,但益阳当地的老人们却始终记得,那个曾经风度翩翩的年轻作家,曾无数次出现在那位姑娘的家门前。 而吴淑媛的墓,如今已被杂草覆盖,只有真正知道她故事的人,才会在清明时节去烧一炷香。 人们常说,名人的私生活总是扑朔迷离,但在这些被尘封的情感背后,其实也不过是普通人最原始的情感:爱而不得、悔而不及。 而那场1980年的雷雨,或许不是突然降临的天象,而是几十年未曾释怀的心结,终于在那个下午,重重地落在了他心上。 周扬去世多年后,关于他与吴淑媛的事情依旧只有零碎片段,有人试图写进传记,但都被删去,有人说他晚年常在夜里独坐,看窗外发呆,桌上摆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女子穿着旗袍,笑容温柔。 是不是吴淑媛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旧情从未真正结束过,或许在周扬心里,真正的忏悔不是跪在坟前烧香,而是那场雨中的转身,他明知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却还是没能走到她面前,这才是他一生中最无法释怀的事。 参考资料: 李洁非《不同的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