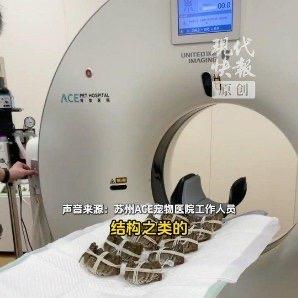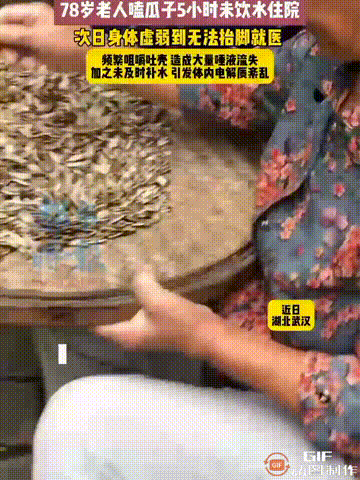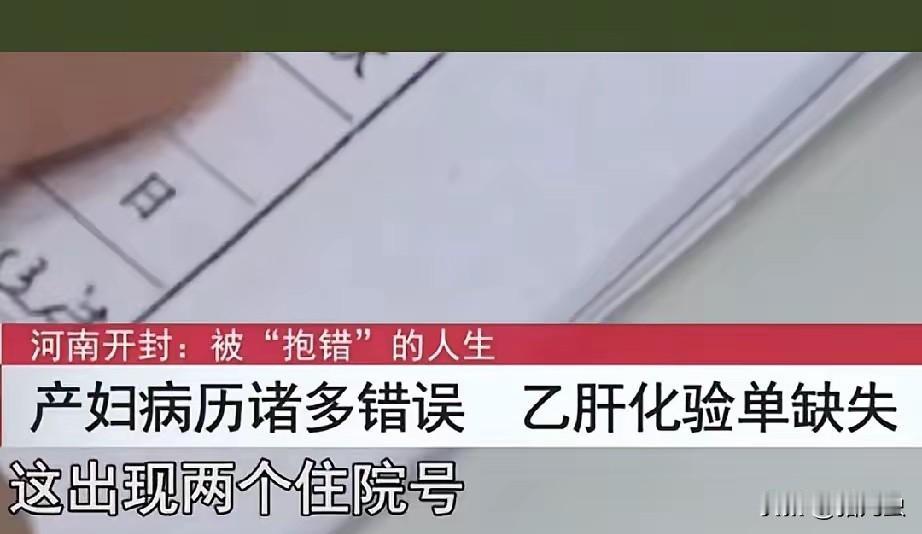2020年,当年提出武汉“封城”举措的李兰娟院士,为国家立下了卓越功勋。不为人知的是,这位在医学界威望极高的专家,竟是靠着自学中医,才有了后来声名远扬的院士之名! 李兰娟早年是纯粹的西医背景,1970年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时,她满脑子都是解剖学、药理学这些西医理论,毕业后走进医院感染科,手里攥着的是听诊器,开的是标准化西药处方,那时候的她大概不会想到,日后让她在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突破,会和老祖宗的医术紧密相连。 真正让她对中医改观的,是基层卫生院里一次惊心动魄的急诊。刚工作没多久,一位产妇产后大出血,血压直线下降,呼吸都快停了,偏偏院里唯一的老中医外出出诊。 看着产妇家属哭天抢地,李兰娟脑子里突然闪过之前帮老中医配药时听过的“独参汤”。死马当活马医,她立刻生火煎药,同时配合西医输液抢救,几碗温热的参汤灌下去,产妇的脉搏竟然慢慢稳了下来。 这场和死神的赛跑,让学西医的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那些看似“土气”的草药和偏方,藏着救人的真功夫。 从那天起,李兰娟成了老中医的“小尾巴”,白天跟着抄方抓药,晚上在煤油灯下啃《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密密麻麻的批注写满了书页边缘。 为了认全草药,她趁着休息天扎进山林,带着医书对照着采集标本,有时候为了确认药性,还敢亲口尝一尝。 有次误吃了有毒的植物,上吐下泻差点晕过去,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在医书上标注“此草有毒,味涩麻,忌与甘草同用”。 这种带着点“拼命”的劲头,让她在短短几年里就把常用中草药的性味归经记得滚瓜烂熟,针灸手法也练得有模有样。 1972年浙江当地爆发甲肝,患者上吐下泻,黄疸严重,单纯用西医补液治疗,很多人好转后还会复发。李兰娟试着在治疗方案里加了茵陈、栀子这些中医里常用的退黄药材,没想到患者的复发率一下子降了下来。 她把治疗过程详细记录,整理成临床报告投给《浙江医学》,这篇融合中西医思路的文章,成了当地甲肝治疗的重要参考。 那时候医院里不少老西医都觉得她“不务正业”,但她认准了“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术”,依旧坚持在临床中摸索两者结合的门道。 真正让她的中西医结合理念大放异彩的,是重症肝炎的治疗。上世纪八十年代,重症肝炎的治愈率只有11%,很多患者送到医院没几天就因为肝衰竭离世。 李兰娟看着心急如焚,她想起中医“扶正祛邪”的说法,觉得不能只靠西医的抗病毒药物,还得帮患者提升自身免疫力。 她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把西医的血液净化技术和中药调理结合起来,用西医设备清除患者体内的毒素,同时用黄芪、党参等中药帮患者稳住气血。 这套后来被称为“李氏人工肝系统”的疗法,硬是把重症肝炎的治愈率从11%拉到了78%,国际肝病权威杂志都专门发文,称这是“肝衰竭救治的新视野”。 这套融合了中医智慧的疗法,在后来的传染病防治中一次次发挥威力。 2013年H7N9禽流感爆发,很多重症患者死于“细胞因子风暴”,李兰娟把人工肝技术用上,用西医手段清除体内的炎性介质,再用中药辅助调理,显著降低了病死率,这个成果后来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20年新冠疫情,她带着改良后的“新冠清肺汤”驰援武汉,临床数据显示,用了这套方案的患者,症状缓解时间缩短2.3天,重症转化率下降40%。 那些曾质疑她“西医不纯粹”的人终于明白,她从来不是要偏向哪一方,而是要把两者的优势捏合在一起。 如今李兰娟的诊室里,西医的化验单和中医的脉诊垫总是放在一起。她每周坐诊时,既看血常规报告,也会搭着患者的手腕号脉,开方时既有西药的精准,也有中药的调理。 有人问她一个西医为什么偏偏对中医这么执着,她总说当年学中医是为了救急,后来坚持用中医是因为管用。 从浙江农村的“赤脚医生”到工程院院士,她的成长路上,西医给了她严谨的诊疗框架,而自学的中医则给了她灵活的治疗思路。 那些深夜啃过的医书,山间采过的草药,最终都变成了救死扶伤的底气,让她在一次次疫情考验中,成为守护国人健康的硬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