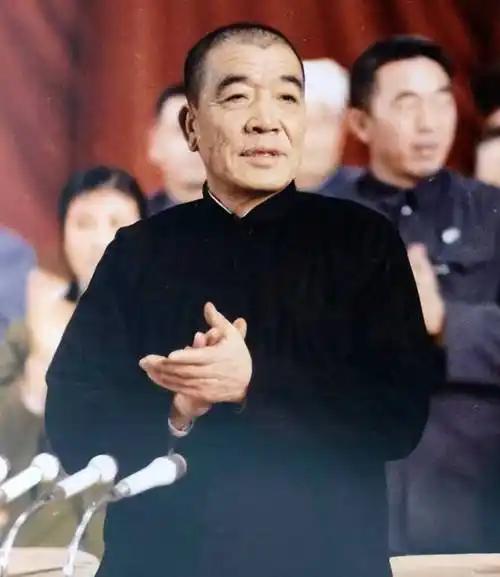1959年,“观音”左大玢告诉毛主席:“大伯是个逃亡地主。”毛主席却说:“逃了也好。” 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1986版《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堪称经典,眉眼间的慈悲庄严仿佛跨越虚实,成为不可复制的银幕符号。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正是湘剧表演艺术家左大玢。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将“观音”演活的艺术家,人生中曾有一段跨越年龄与身份的特殊缘分——与毛主席结下忘年之交。 1959年的湘剧界,二十出头的左大玢已小有名气。 一天,她接到通知前往湖南省交际处(今长沙市湘江宾馆)主演《生死牌》,饰演王玉环。 登台瞬间,她瞥见台下的毛主席,惊得险些忘词,强压心神才完整完成演出,散戏卸妆时,一位女同志走来告知,毛主席很喜欢她的表演,想邀她跳舞。 左大玢涨红了脸:“可我不会跳舞啊。”对方笑着说:“不会没关系,我找人教你跳舞,很容易的。”这位女同志便是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侯波。 在警卫员封耀松的临时指导下,她匆匆学会四步基本舞步,便被领到毛主席面前。 面对领袖,她紧张得手足无措,毛主席笑着解围:“娃娃,跳舞要动哕,不能老站着。” 这句亲切调侃让她放松下来,伴舞时却始终低头不敢对视,一曲结束后背已浸满汗水,这份腼腆直率反倒让毛主席对这个小老乡印象深刻。 往后毛主席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会被派去唱戏、陪舞或聊天,熟悉后两人的互动满是家常趣味。 毛主席曾半开玩笑问她:“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呀?”她实诚回答随父亲姓。 当毛主席把“玢(bīn)”念成“芬(fēn)”,她直言纠正:“主席,您念了白眼字。” 毛主席非但不恼,反倒大笑,打趣让她回家问父亲这是不是多音字。 聊起家族时,毛主席问及她与左宗棠的关系,提到她大伯左霖苍是“有名的举人”,左大玢却说:“什么举人哪,是一个逃亡地主。” 毛主席沉默片刻喃喃道:“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啊。”简单话语里藏着对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体谅。 舞会上的细节更显信任特殊,毛主席通常先邀省委书记夫人,再是两位资深湘剧艺术家,第四个便是她。 警卫员和公安厅厅长担心主席劳累,特意嘱托她陪主席休息,这份安排在戒备森严的环境里,是旁人难有的殊荣。 毛主席也常关心她的成长,叮嘱“搞文艺要多学文化”,连她下乡演出是否方便、嗓子是否沙哑都挂在心上。 这份知遇之恩,在1966年后成了左大玢的“保护伞”,因父亲曾是程潜帐下少将高参,她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下放农村两年。 1973年,她主演的《园丁之歌》被江青批为“毒草”,艺术生涯陷入危机,关键时刻,毛主席观看后当场鼓掌,这一表态让她免遭进一步迫害。 这段缘分还为她铺就了通往经典的道路,毛主席晚年卧病,想看家乡湘剧,相关部门便组织演员排演传统剧目拍录像送北京。 1976年,央视导演杨洁赴湘录制《追鱼记》,见左大玢饰演的观世音形神兼备,当即许诺:“以后拍观音戏必请你。” 六年后,央视筹备《西游记》,杨洁兑现承诺邀她试妆,著名化妆师王希钟一见便惊叹:“像!像!像!根本不用试妆!” 为贴合角色,她改掉湘剧青衣“眼神过活”的习惯,学着控制目光;每到取景地必进庙揣摩观音塑像的神态手势,把慈悲庄严刻进骨子里,最终成就了家喻户晓的“活观音”。 这段忘年交,早已超越普通交往,成了领袖与文艺工作者关系的生动写照。 毛主席对左大玢的赏识,从不是特权加持,而是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才的珍视。 他看见她表演里的灵气执着,用鼓励给她信心,用庇护守她艺术生命,用“多学文化”的叮嘱引她走得更远。 这种伯乐之责,藏着领袖对传统文艺的远见:文艺要繁荣,就得理解支持创作者,给人才成长留足空间。 左大玢的成功也没辜负这份知遇,她没沉溺特殊缘分的关注,而是以匠人之心打磨技艺。 从湘剧舞台到影视银幕,她用纠正读音的直率守事实,用揣摩观音的虔诚践“戏比天大”,把机遇变动力,用努力回应信任。 领袖的远见照亮艺术之路,匠人的坚守成就经典传奇。 左大玢与毛主席的忘年交,是段往事更是份启示——文艺因人才而兴,人才因尊重而盛。 这份跨越岁月的情谊,像陈年佳酿越品越浓,也为后世留下关于艺术、人才与传承的永恒思考。 【评论区聊聊】你心中最难忘的经典银幕角色背后,是否也藏着这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信源:艺苑风采丨“观世音”与毛泽东的忘年交——新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