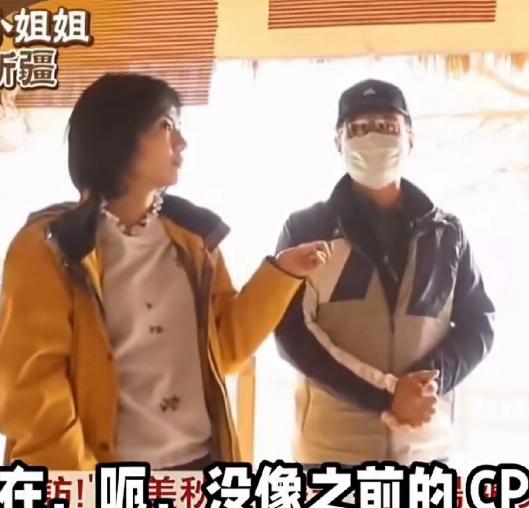聂晓岚,即是烈士聂曦在台湾的侄孙女。目前聂晓岚是台北一所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拍摄《沉默的荣耀》时,她专程从对岸飞过来,客串了这个庭审的最后时刻,一位庭审员。聂晓岚不是在演戏,她是真实聂家在新时代里生命的延续。 她攥着口袋里那张磨得边角发毛的黑白照片站在庭审现场,指尖反复蹭过照片上年轻的面孔——那是叔公聂曦,1948年潜伏在台湾时留下的影像,背后还歪歪扭扭写着“待归乡,敬候家人”。那天片场的灯光打在她脸上,没有演员的紧张,只有一种沉在骨子里的郑重,仿佛不是来客串一个角色,而是替整个聂家,赴一场跨越七十多年的“重逢之约”。 没人比聂晓岚更清楚,“聂曦”这两个字在家族里的分量。她从小听奶奶(聂曦的亲侄女)讲叔公的故事,讲他19岁瞒着家人投身革命,讲他在台湾街头装作布店伙计,偷偷传递情报时总把袖口挽到小臂,方便随时藏起密信;更讲1950年那个雨夜,军警闯进布店时,聂曦为了烧毁情报,手指被火苗烫得全是疤,最终还是被押走,再也没回来。奶奶说这些时,总拿着一块聂曦留下的蓝布手帕擦眼泪,那手帕上的针脚,是聂曦出发去台湾前,母亲连夜缝的。 可这些故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藏在台湾的聂家老宅里。聂晓岚上中学时,历史课本里关于那段隐蔽战线的记载少得可怜,提起“聂曦”这个名字,连专门教台湾史的老师都摇头说“没印象”。她那时候就憋着一股劲:叔公不是“无名者”,他的牺牲不该被埋在时光里。后来考上师范大学,她毫不犹豫选了历史专业,就想把这些“沉默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在台北的中学课堂上,她讲两岸近代史时,总会多留十分钟。拿出那张老照片,跟学生说“这是我的叔公聂曦,他当年在台湾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家园,把生命留在了这里”;讲情报传递的危险时,会提起奶奶说的“袖口藏信”的细节,告诉学生“英雄不是课本上的黑体字,是会疼、会想家的普通人”。有学生问她“两岸隔着海,这些故事还有意义吗”,她指着教室窗外的樟树说“就像这树,根在土里连着,不管枝叶往哪边长,本源从来没变过”。 这次来客串《沉默的荣耀》,是她主动联系的剧组。看到剧本里写的“庭审最后时刻,众人向烈士默哀”,她立刻订了机票——她想站在那里,不是演“庭审员”,是作为聂家的后人,替那些没等到聂曦归乡的长辈,说一句“我们记得”。片场里,当导演喊“默哀开始”,她低下头的瞬间,脑子里闪过的是奶奶临终前抓着她的手说的话:“要是能让你叔公知道,家里有人还记得他,他就不孤单了。” 她从来没把自己当“客串演员”。拍戏间隙,她拿着聂曦的事迹资料,给剧组的年轻演员看:“叔公当年潜伏时,每天都要记好几本假账,怕暴露身份;他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糯米糕,到台湾后再也没吃过。”那些细碎的生活细节,让剧本里的“烈士”形象,一下子变得有血有肉——原来所谓“荣耀”,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光环,是普通人在绝境里守着信念的执着,是后人隔着岁月不肯遗忘的牵挂。 聂晓岚回到台北后,把拍戏时穿的那件庭审员制服叠得整整齐齐,和那张老照片放在一起。课堂上,她又多了一段新故事,讲她在片场看到的、听到的,讲“沉默的荣耀”不是一句口号,是像叔公这样的人用生命写就,再由一代又一代人,用记忆和传承续下去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