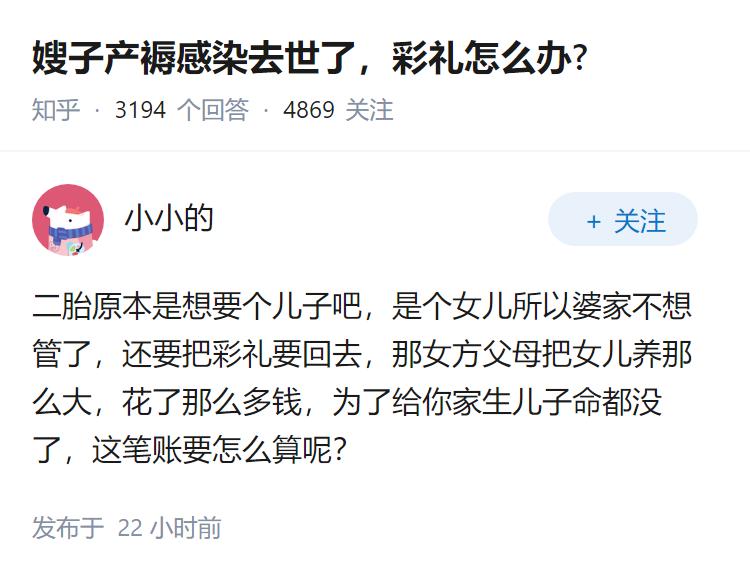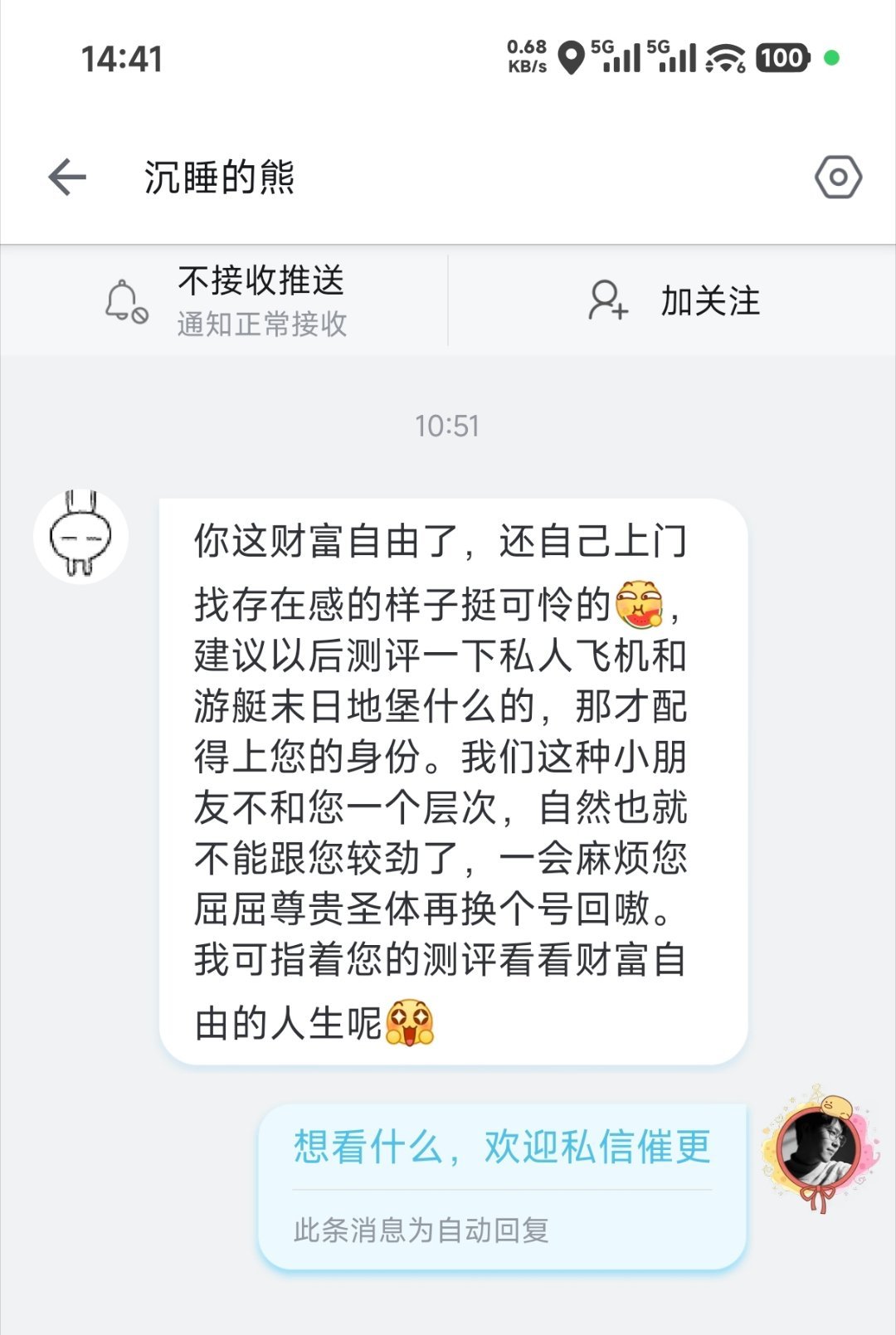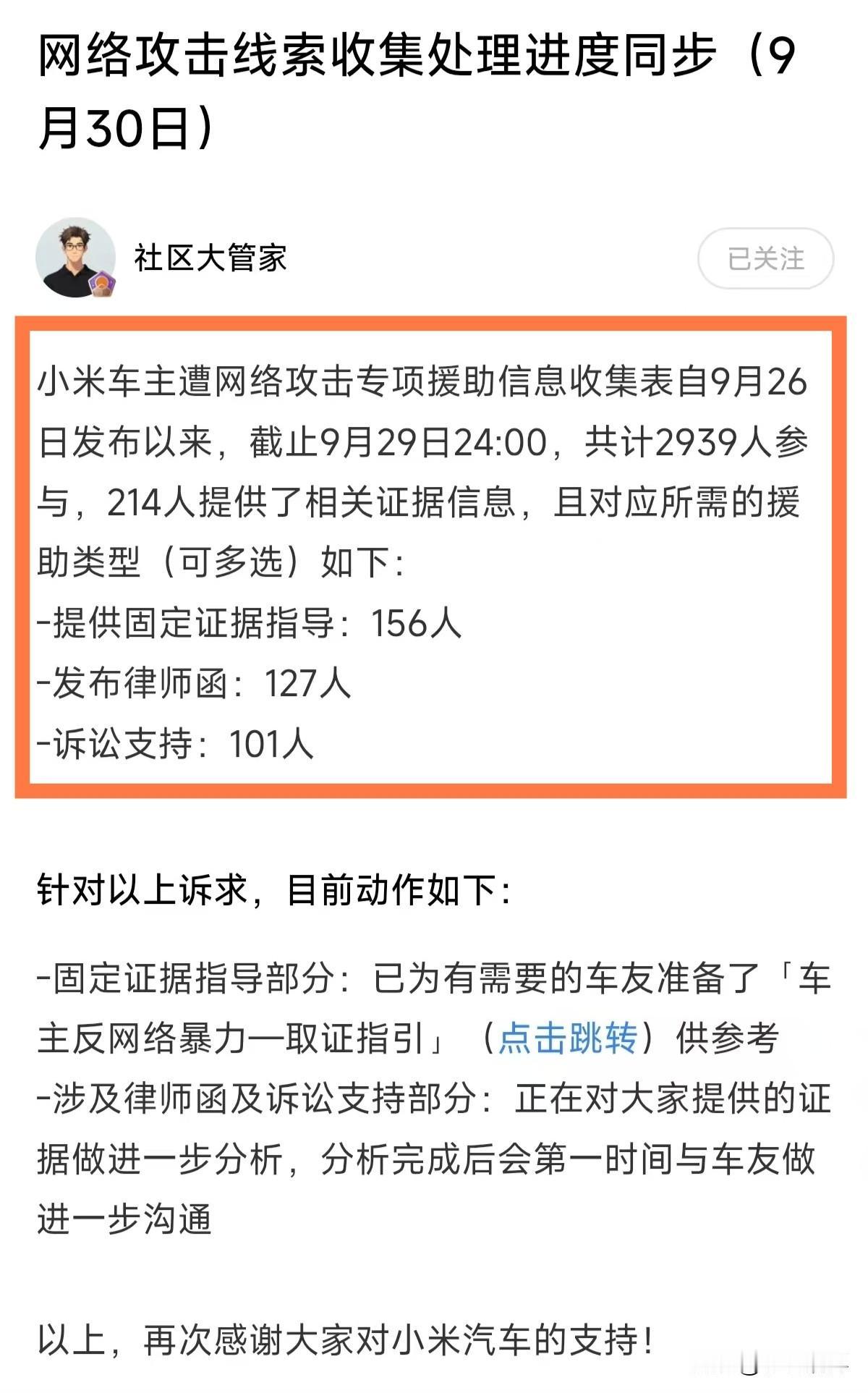1996年底,褚时健崩溃的对调查人员说,你们别搞我的家人,有什么事冲着我来。1个月前,褚时健刚刚得知,自己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看守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3年冬,哀牢山的橙子刚摘完最后一筐,85岁的褚时健坐在果园的竹椅上,手里摩挲着个表皮皱巴巴的橙子。 孙子递来手机,屏幕上是“褚橙上线电商”的新闻,他笑了笑,指节敲了敲竹椅扶手:“当年映群说要学会计,要是现在,该帮我管这些账了。” 竹椅旁的土坡上,插着块小木牌,上面刻着“褚映群”三个字,周围种着几株她生前喜欢的山茶。 1979年夏,玉溪烟厂的旧车间里,褚时健光着膀子检修机器,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 18岁的褚映群背着帆布书包跑进来,手里攥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爸,我考上云南财贸学院了!” 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汗,接过通知书看了又看,把女儿拉到身边:“好,以后爸的账,就交给你算。” 那天晚上,马静芬做了锅红烧肉,褚时健喝了两盅酒,话比平时多了不少,说要把烟厂的旧机器都换成新的,让女儿毕业回来有个好工作。 1985年深秋,褚时健带着烟厂的技术员去德国考察,临走前,褚映群把个笔记本塞给他:“爸,每天记一笔开销,我回来帮你核对。” 他在德国的酒店里,真就每天对着发票记账,连买瓶矿泉水都写得清清楚楚。 回来时,他给女儿带了个计算器,褚映群抱着计算器笑:“爸,以后算账不用你动笔了。” 那时烟厂的效益越来越好,褚时健却更忙了,常住在厂里,褚映群就每周带着饭菜去看他,坐在车间的角落里,陪着他核对生产报表。 1994年雨季,褚时健收到第一封举报信,他没当回事,照样每天去车间。 褚映群却犯了愁,拉着他的胳膊说:“爸,咱们把账交出去,请审计来查,省得别人说闲话。”他拍了拍女儿的手:“爸没做亏心事,不怕查。” 可没过多久,调查人员就进了厂,褚映群帮着整理账本,熬了好几个通宵,眼睛红得像兔子。马静芬偷偷跟褚时健说:“让映群先躲躲,别受牵连。” 他摇了摇头:“身正不怕影子斜,躲什么。” 1995年冬,褚映群被带走的那天,褚时健正在开产销会。秘书在他耳边说了句,他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接着往下讲,声音却比平时低了些。 散会后,他回到办公室,看着女儿帮他整理的账本,一页页翻着,直到天亮。马静芬哭着要去找人,他按住妻子:“别去,相信映群,也相信法律。” 可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女儿在看守所的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只说“爸,别担心我”。 1996年底,褚时健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褚映群没了。他当时正在看烟厂的年度报表,手里的报表滑落在地。 马静芬赶来时,看见他坐在椅子上,盯着窗外的红塔山,半天没动。后来调查人员找他谈话,他红着眼眶说:“所有事都是我做的,别牵扯我的家人。” 1999年审判时,他穿着中山装,腰杆挺得笔直,听到无期徒刑的判决,也没哭,只是看向旁听席上的马静芬,轻轻点了点头。 2002年保外就医后,褚时健第一件事就是去哀牢山。他踩着没膝的草,看了一片又一片荒地,最后选了块向阳的山坡。 第一天挖坑种树,他不小心崴了脚,马静芬要扶他下山,他却坚持要把坑挖完:“这点疼算什么,当年烟厂那么难,不也过来了。” 橙子树刚结果时,遇到冻灾,很多树苗都死了,他蹲在地里,看着冻死的树苗,半天没说话,后来跟工人说:“重新种,选耐寒的品种。” 2012年,“褚橙”开始走红,有记者来采访,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创业。 他指着果园里的橙子树说:“这些树就像人,只要根还在,就能活。”晚年的他,每天都会去果园转一圈,看看橙子的长势,跟工人聊聊天。 马静芬陪着他住在山上,两人偶尔会坐在院子里,喝着茶,聊起褚映群小时候的事,说她小时候最喜欢吃橙子,每次都把汁弄得满脸都是。 2019年褚时健去世后,马静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果园里,旁边就是褚映群的小木牌。每年橙子成熟时,马静芬都会摘几个最好的橙子,放在两人的墓前。 现在,果园里的橙子树越来越多,“褚橙”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孙子接过了管理果园的担子,时常会跟马静芬说起电商上的销量,马静芬就会笑着说:“你爷爷和你姑姑要是知道,肯定高兴。” 哀牢山的风里,总是飘着橙子的甜香,像是在诉说着这个不服输的老人,和他从未放下的牵挂。 主要信源:(凤凰网卫视——褚时健谈女儿狱中自杀老泪纵横:是我害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