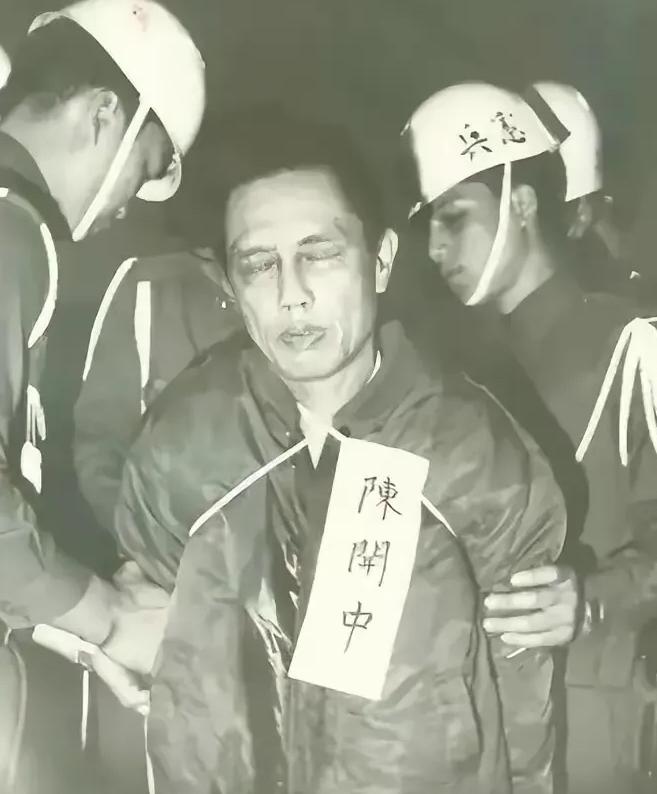1944年冬春之交的乌克兰,一队苏军士兵正在打扫战场。突然,一具德国军官的尸体引起了苏军士兵的注意:在一辆装甲指挥车的残骸旁边,德国军官怀中抱着一支步枪死去,看上去已经60多岁了,雪花落下后将他的两鬓染成了斑斑白色。 1944年初,乌克兰的地面冻得硬,天阴着,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 切尔卡瑟那块地方,苏军已经包了个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上年就盯着这口袋,一点点收着口。 德军在那里面,被围住了。将近六万人,跑不了,躲不掉。 施特默尔曼,是德军里少有的那种将军,不嚷不闹,不摆排场。他指挥着XI军团,在圈里。地图摊开好几张,他就拿笔点着看,不多话,谁也听不出他到底怎么想。 他岁数大了点,五十多,神色一直紧着,看人都不带笑。 那时候,物资紧,天又冷,吃的靠空投,给一车,丢一半。 士兵就那么蹲着,冻得直抖,咬着干粮啃。有的人饿出毛病,晚上能听见咕哝说梦话,喊着娘。 苏军压得紧,每天打炮。 有时候晚上轰一轮,炸出火来,雪地跟着亮,像哪儿着火了一样。 德国兵不动声色,该干嘛干嘛。撤退也没指望,外头那支来救的部队走不动了,天太冷,路不好走,人手也不够,曼施坦因发来电报,说救不了。 到了2月16号,施特默尔曼接到电令,说只能靠自己突围。 他没开会,直接下命令。让前锋准备,后卫断尾。 他说话不重,但谁都知道,这话说出来,就没人能回头了。 当天晚上,风吹得很猛,雪刮得脸生疼,队伍出发,走在路上的时候没声,只有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 两千多个重伤员留了下来。没办法,带不走,扛不动。留着只是拖累。医护给他们盖了毯子,留了干粮,有人写了信,交给战友带。就那点火,烧不热帐篷,只是让人心里不太凉。 突围队伍是往西走的,前头是维京师。精锐,都知道怎么打仗。 他们趁夜穿过树林,想避开苏军火力,可终究还是被发现了。枪声一响,像是划破布一样,嘶一下就劈开了。 炮弹落下来,炸得人倒地不见影。 队伍乱不了,还在走。有的人被火烧着了,也不叫,扑几下继续跑。 过了几公里,河到了。格尼洛伊季基奇河,不宽,但水急,冰厚,没有桥。 那一刻,谁都清楚,要活,就得跳水。装备早扔了,身上只剩步枪和几块干粮,鞋都湿透了。 三万多人咬牙过河。水冰得刺骨,河里浮着冰碴子,腿一踩下去就麻。有的人走一半脚抽筋,没起来。还有的人爬着上岸,手上全是血口子。 后面那两万人,没过来。 苏军堵了口,炮火继续轰。天边泛白的时候,骑兵压上来了。德军撑不了多久。 地上是雪,也是血,马蹄一阵阵踩,刀砍下来不分投不投降。举手的也中刀,喊没喊全就没了声。有些人想跑,可哪跑得动,全都冻僵了,根本迈不动腿。 施特默尔曼还在。 他没跑,也没换衣服,就是穿着那身旧军装,站在一处高地边。那地方是死守的最后阵地,后卫营都聚在那里,任务只有一个,把苏军拖住。 他跟士兵一样,蹲着、爬着、躲着炮火。步枪没放下过。有人见他还在发命令,也有人说他最后一句话是:“能出一个是一个。” 战斗结束了,没声音了。苏军打扫战场。装甲车是烧过的,冒着烟。 地上是尸体,枪压在身下,有的还热着。施特默尔曼的尸体靠在一块残骸旁,手里握着枪,脸是白的,鬓角有雪,胸前的勋章还挂着,已经被血染红。没人动他。 苏军那边的军官看了眼,说按军礼安葬。没有仪式,就是抬去埋了,算是敬个对手。 回到德国,他的名字上了公报,说他是“为帝国而死”。 照片印在小册子上,戴着帽子,站得直直的。家属拿到了勋章,说是橡叶骑士十字。也有人觉得他是替罪羊,死得正好,拿来做宣传。 后来有些历史书翻他,说他不该带兵死守,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 也有的人说,他就是干到最后的兵,没跑、不躲,死在阵地上,也算有样子。 不争这些。当时那些士兵活下来多少算个命,全靠前头有人挡着。断后的,就他一人是将军,其他全是下士、中士,还有几个副官。 他们没后退,也没多说。就在那里站着,等炮响,等冲锋,等最后一下。 切尔卡瑟口袋这个仗,翻来覆去讲,谁赢谁输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那段时间,有人冻死,有人饿死,有人走出冰河后不说一句话,有人一直喊着哥哥就再没睁眼。 雪是后来化的。 施特默尔曼倒下的地方,春天化水流过,泥泞了一大片。后来那块地没人种,长草,风一吹,草倒了,河还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