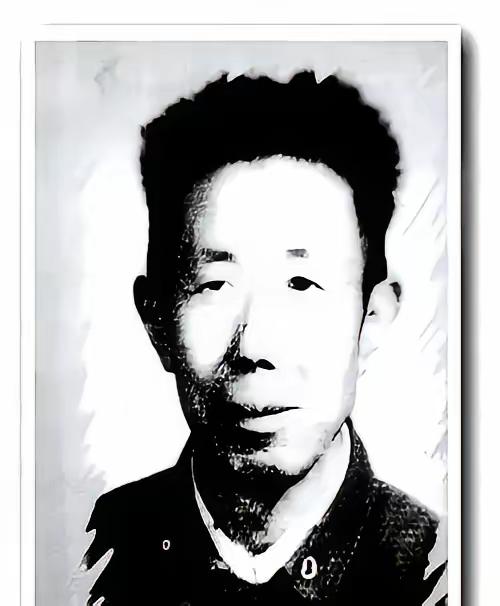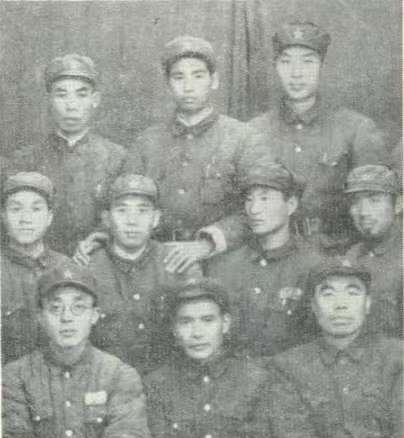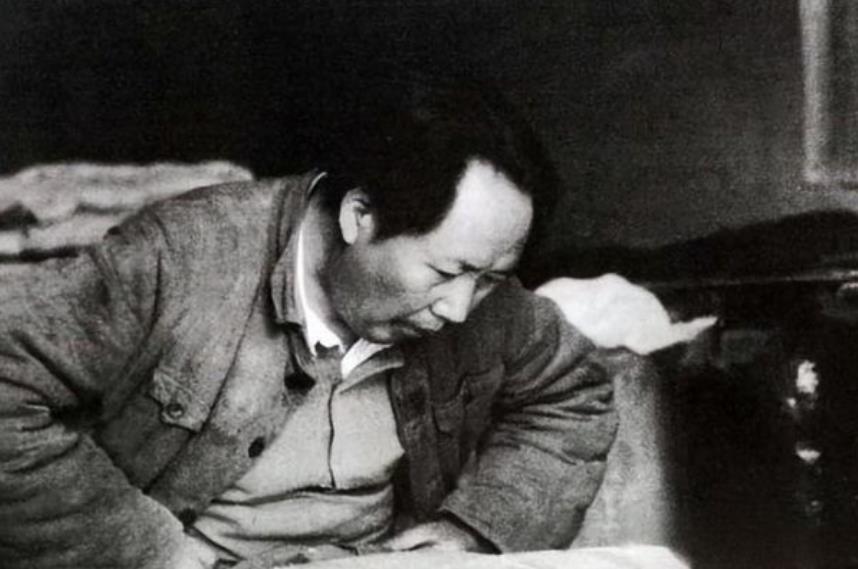1949年,杀了3000多名红军的韩起功率残部逃入祁连山,这时,一个农民走了100多里路找到了解放军:“我知道韩起功在哪里!” 张掖县供销处的办公室里,任廷栋正低头整理一份账本,窗台上摆着一盆村民送的仙人掌,翠绿的叶片上还沾着些许泥土。 这是 1952 年的春天,距离他协助抓获韩起功已过去三年,从农民到供销处主任,身份变了,但他手上的老茧、待人的热忱,仍带着祁连山脚下泥土的气息。 没人能想到,这位温和的干部,曾藏着一段跨越十二年的沉重记忆。 1940 年,任廷栋逃到祁连山脚下的岔河村已三年。这年冬天特别冷,他住的土坯房四处漏风,邻居马大娘揣着一碗热面片上门,看着他冻得发红的手叹道:“后生,别硬扛,有难处跟大娘说。” 任廷栋接过面片,热气模糊了双眼。在岔河村的这些年,他跟着马大爷学种青稞,帮村民修过漏水的屋顶,教孩子们认过字,村民们只知道他是 “从南边来的任娃”,却从没人追问他的过往。 只有在每年清明,任廷栋会独自去村后的山坡,对着空谷轻声念出几个名字,那是他再也没能见到的战友,他把这些名字刻在心里,像守护一份秘密的约定。 1949 年那个秋日的相遇,打破了这份平静。任廷栋在山上给青稞浇水时,看到几个身影从树林里窜出,为首那人的皮靴在碎石路上磕出声响,虽沾满尘土,却仍透着一股蛮横。 任廷栋的心跳骤然加速,他赶紧躲到岩石后,看着那人转身的瞬间,十二年前张掖城墙上的那双眼睛,突然与眼前的面孔重叠,是韩起功! 他攥紧了手里的锄头,指节泛白,直到那伙人走远,才发现手心已全是冷汗。 那天晚上,任廷栋翻出木箱底层的红军徽章,借着煤油灯的微光反复摩挲。徽章边缘已有些磨损,却依旧能看清上面的五角星。 他想起马大娘常说的 “做人要对得起良心”,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战友,一个念头逐渐清晰:他要去找 “解放军”,那个村民口中 “打马家军的队伍”。 第二天清晨,任廷栋跟马大娘说要去城里赶集,揣着几个干馍就上了路。 100 多里的山路,他走得比往常任何一次都急,路过山泉就掬水喝,饿了就啃口干馍,脚底磨出了血泡,就用布条裹紧继续走。 走到张掖城门口时,他看到挂着 “解放军军管会” 的牌子,门口的战士正笑着跟百姓打招呼,那股亲切劲儿,让他想起当年红军行军时的模样。 “同志,我知道韩起功在哪里。” 当任廷栋说出这句话时,军管会的同志先是惊讶,随后认真听他讲完过往。 几天后,劝降的任务落在他肩上,出发前,任廷栋特意去了趟岔河村,马大娘塞给他一袋炒青稞:“早去早回,大娘等你吃晚饭。” 他接过青稞,突然觉得心里踏实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还有岔河村的乡亲,还有那些等着一个交代的战友。 劝降那天,任廷栋站在火烧沟台的山洞前,没有丝毫犹豫。韩起功看到他时,眼中满是错愕,任廷栋却很平静:“你欠的债,该还了。” 山洞里的沉默,比山间的寒风更刺骨,当韩起功最终垂头走出山洞时,任廷栋望着远处的祁连山,突然觉得天空亮了许多。 后来,他花了半年时间,凭着记忆整理出一份战友名录,把能想起的名字、籍贯都写下来,交给了当地纪念馆,他想让这些名字,被更多人记住。 1955 年,任廷栋带着家人回了一趟岔河村。马大娘拉着他的手,指着村头的新学堂说:“这学堂,有你当年教娃认字的功劳。” 任廷栋看着孩子们在学堂里读书的身影,突然想起自己 14 岁参加红军时的模样。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他整理的战友名录,他把笔记本交给学堂的老师:“要是孩子们问起过去,就跟他们说,有一群人曾为了好日子,拼过命。” 晚年的任廷栋,最爱坐在院子里看祁连山。夕阳落在雪山之巅,把云彩染成温暖的橘色,他会给孙辈讲岔河村的故事,讲马大娘的热面片,讲种青稞的技巧,偶尔提到当年的事,也只说; “做人要守着良心,不管等多久,该做的事一定要做。” 他的书架上,始终放着那本战友名录,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坚守。” 如今,任廷栋的故事已成为张掖当地的一段佳话。他当年整理的战友名录,被珍藏在张掖市博物馆,成了传承红色记忆的重要载体; 平凡的人也能凭着坚守,活出不凡的意义。祁连山的风,年复一年吹过这片土地,带着任廷栋那代人的记忆,也带着这份坚守,继续向前。 信源:六安纪检监察网【红色记忆】深山遇顽匪 连夜报军情——流散红军任廷栋擒匪记 2021-01-25 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