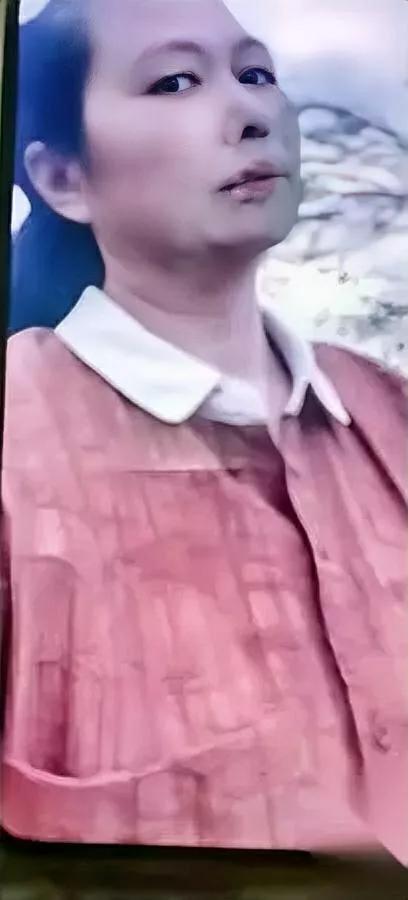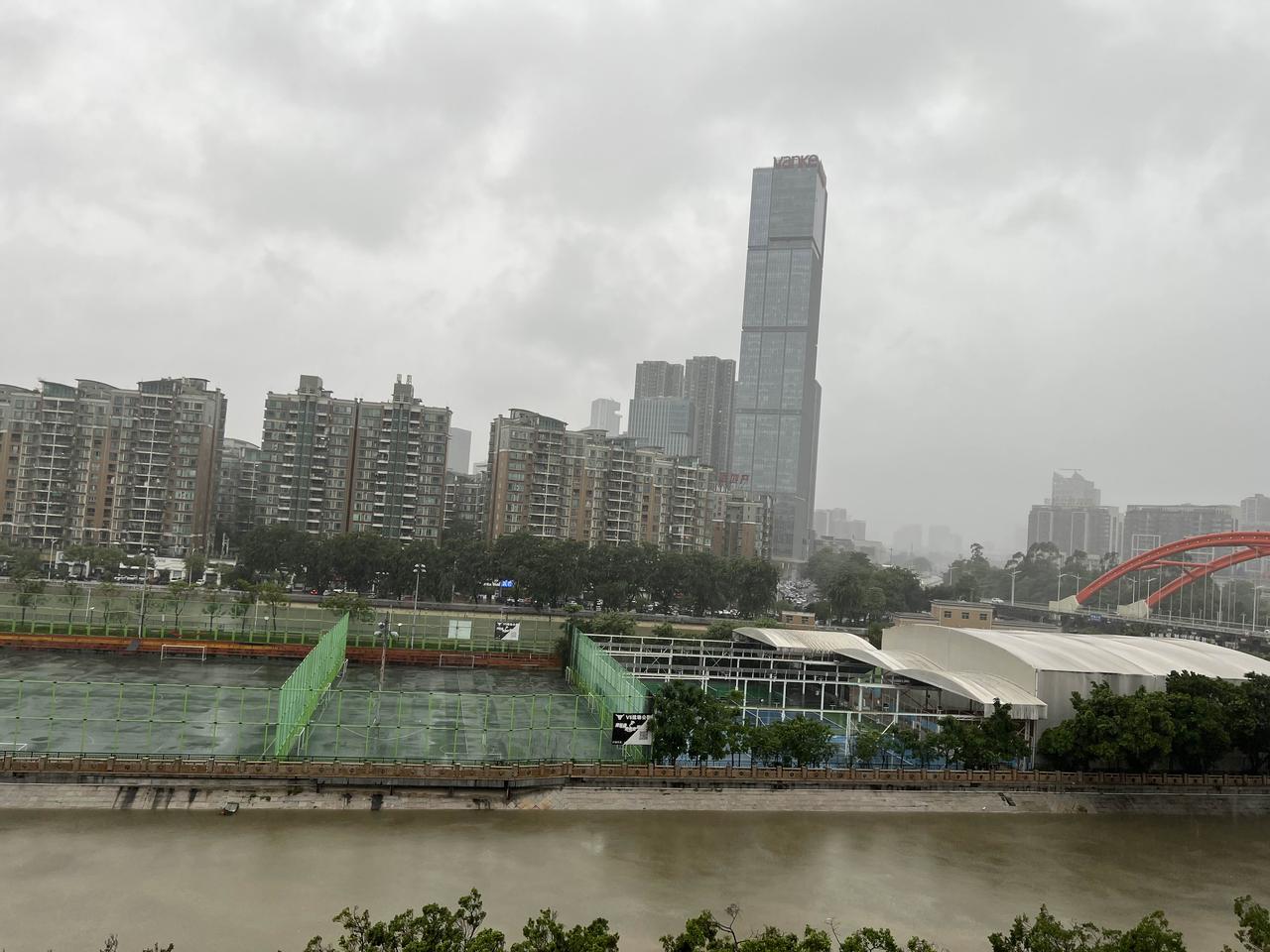元朝末年,雁门关外有家不起眼的小客栈,老板姓赵,是个退伍的老兵。他立下一条规矩,凡是进京赶考、盘缠不足的读书人,一律免收食宿,还赠送一双新草鞋。二十年间,他送走了上百位穷书生,账本上记下的欠账,他从未想过要去讨还。 1358年,在雁门关外,雪比往年早下了三个月。 雁门关脚下那家挂着“赵家栈”布幡的小客栈,檐角的冰棱子坠得比往年更长。 老板赵守义的跛腿裹在厚棉裤里,每走一步都蹭着地面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赵守义不是天生会开店。 二十年前他是大元军的步卒,跟着主帅打宋军时走散在雁门关的山坳里,饿了三天,最后是山脚下种红薯的老乡挖了半块烤红薯塞给他。 “娃子,活着才有指望。” 后来他腿上中了元军的流箭,伤好后没法再扛刀枪,就用退伍银钱盘下这间破客栈。 不为赚钱,就为续上当年那半块红薯的暖。 他立了个没写在招牌上的规矩。 凡进京赶考、盘缠断在路上的读书人,管吃管住,走时再送一双草鞋。 草鞋是他让栈里的帮工纳的,鞋底垫着晒干的艾草,厚得能隔雪寒。 他还会在账本上写上每个书生的名字:“至正五年,李生,欠食宿四百文,赠草鞋一双”“至正十年,王生,欠馒头四个,赠干粮半斤”。 每个名字旁,还会画上个小圈。 “这些圈是盼头。” 赵守义后来对来修客栈的陈默说,“前两年有个周生,考上了江南县令,托人送了两袋新米来,说当年没我的干粮,他走不到大都。” 陈默是第六十个被赵守义留在栈里的人。 那年冬天雪下的紧,陈默从陕西渭南出发,走了快一个月,过山口时被小偷摸了包袱,最后只剩一件破长衫裹着身子。 他敲开赵家栈的门时,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老伯,能给碗热水不?” 赵守义没说话,先把烤红薯塞进他手里,又端来小米粥。 等陈默暖过身子,赵守义从里屋抱出个木箱子,里面全是新纳的草鞋。 “这双厚,垫着艾草,夜里睡觉不冻脚。” 他掀开西厢房的棉帘,“明早走的时候,我给你装袋炒面,遇着风口就着雪吃,别饿坏。” 陈默接过草鞋时,差点流眼泪:“等我考中,一定回来报答您。” 陈默鞠躬时,眼泪砸在草鞋上。 赵守义摆手笑:“报答啥?我当年要不是那半块红薯,早埋在山里了。你们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将来能帮百姓办事,就是最好的报答。” 六年后,至正二十四年春,赵守义的头发更白了,左腿的旧伤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直抽抽。 栈里的生意淡了,元朝末年战乱多,赶路的人少了,有时候一整天只有几个卖货的商贩来歇脚。 那天上午,栈门口突然传来马蹄声。 一队人马停在门口,为首的青衫官员跳下马,快步走进来。 陈默穿着御史的官服,腰间挂着鱼符,身后跟着两个随从,拉着一车木料和粮食。 陈默紧紧握着赵守义的手:“老伯,我回来了。” 赵守义揉着老花眼,半天才认出眼前穿官服的人:“你、考上了?” “嗯,现在在大都当御史。” 陈默看见栈顶的茅草被雪压塌了一块,赶紧吩咐随从:“去镇上找工匠修屋顶,请大夫给老伯看腿伤。” 赵守义拦着:“别破费,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 陈默却执意:“当年您把最后一口热粥都留给我,现在我有能力了,该还了。” 后来,陈默联系了当年受过赵守义帮助的书生。 有在江南当县令的周生,送来了新木料。 有在京畿做教谕的王生,送来了《四书》刻本。 还有个做过知府的李生,提笔写了块“助学栈”的木牌。 黑底金字,挂在栈门上方,比原来的“赵家栈”更亮。 “助学栈”的名声慢慢传开。 不只是书生,路过的百姓、逃荒的难民,赵守义都乐意接济。 有人问他图啥,他乐呵呵的指着账本的墨圈:“不图啥,就图这圈里的名字,能多几个读上书、做好事的。” 至正二十八年冬天,赵守义在“助学栈”闭了眼。 临走前,他还攥着当年陈默送他的那支毛笔,笔杆上刻着“读书报国”四个小字。 后来,“助学栈”换了掌柜,是当年受赵守义帮助的周生。 他把栈里的规矩传了下去,穷书生免食宿,送草鞋,遇到逃荒的人,管顿热饭。 账本上的墨圈越画越多,像一串串挂在岁月里的灯,照亮每个路过的人的路。 元朝灭亡那年,“助学栈”还在。 新来的书生坐在西厢房的炕上,摸着账本上的墨圈,想起赵守义的话:“这世上,总有人愿意把温暖传下去。” 窗外的雪还在下,可栈里的炭火旺着,粥香飘着,像在说,有些善意,从来不会因为朝代更迭而消失。 雁门关外的风还在刮,可“助学栈”的布幡一直没倒。 它像个老人,守着一段关于善意的故事,等着下一个来取暖的人。 主要信源:(《元史·隐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