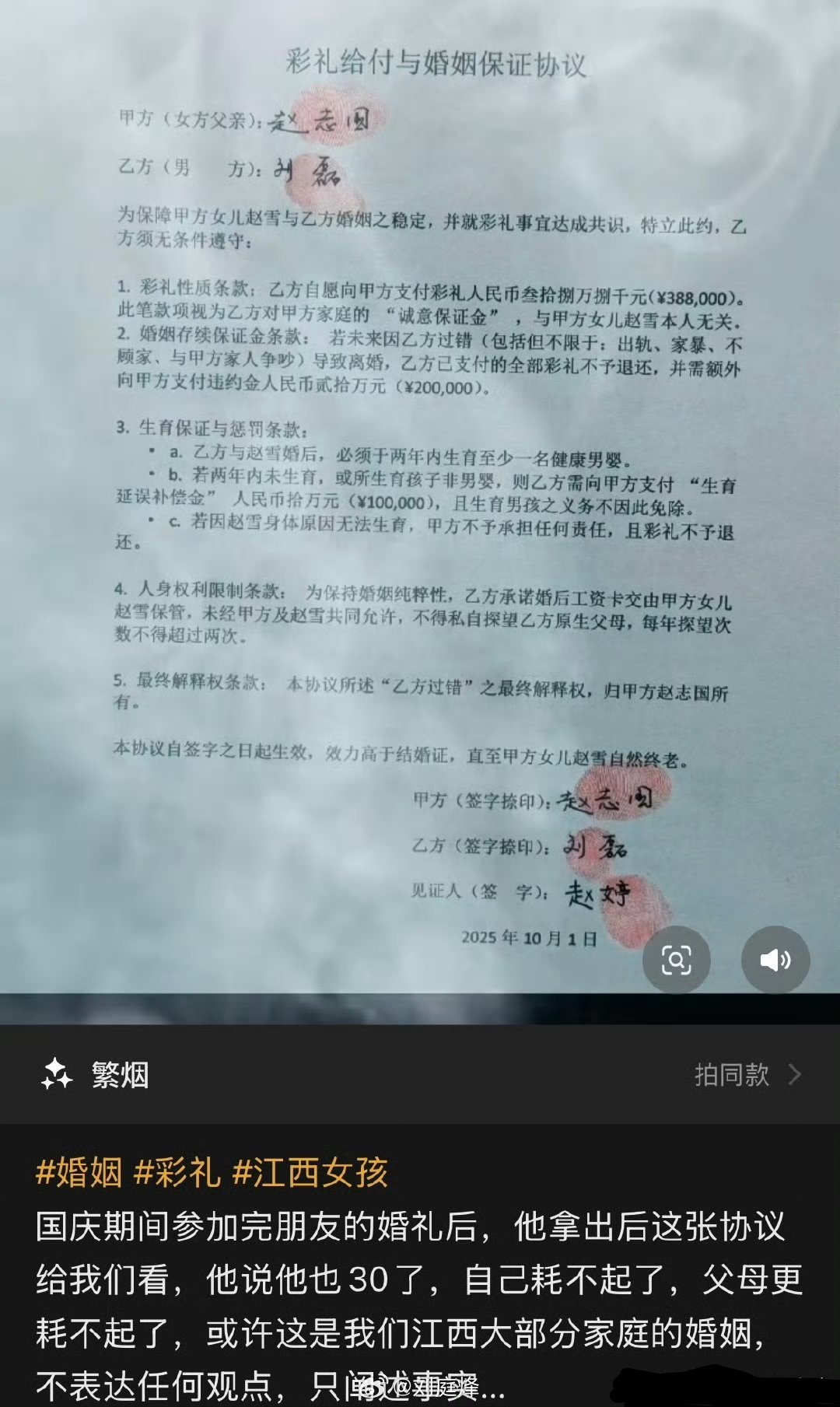清末民初,少林寺住持恒林和尚为了乱世生存,保护寺庙,做了一件看似明智其实极为凶险的事,他领头成立了少林寺民团,并亲自担任团总,购买了大量枪械,将少林寺武僧团体发展成了一支极具战斗力的地方武装。 嵩山少林,有些日子是黑暗的、混乱的。 清末民初,乡下盗匪、不稳的军阀、枪声、谣言——这些都从没离开这个地方。 山门里,寺庙里的和尚们曾经练拳、舞棍,也诵经、打坐,但那种能把祖师传下来的拳脚功夫用来挡子弹,没几个人相信。恒林和尚相信。 恒林住持那阵子,少林寺香火微弱,庙宇年久失修,财产时常被掠,民生被战火波及。山下村民说:“咱家的稻子被匪徒抢了,孩子饿着肚子跑到寺里来求一碗饭。”恒林看到了,不是念佛能管用的。拳法在木棍上比在实战里管用,到了真正枪来,拳脚就成摆设。 这也不是武侠小说的台词,是现场每天都打的仗,是火光里响起来的子弹壳贴着肚皮飞过来。 恒林组织“少林保卫团”,和尚们披僧衣也拿枪。 他带人练习开枪、练队列、练夜间埋伏,把禅堂、殿堂间的练武和战术融合起来。 第一次练机枪,和尚们搞不清机枪架怎么调,子弹蹦的声音像铁锤打钉子。恒林几次在旁边捶胸责备:“你们学拳十年,把枪都不敢举!”慢慢地,机器的冷笑变成了战斗的利器。 少林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是村民白天能听见的弦外之音。 土匪先吃亏。 他们夜里摸过来,恒林和尚带着保卫团在黑夜伏在石头后头,一点灯光也不给对方。 土匪以为是盗贼会破庙夜闯,没想到被机枪扫下来,狼狈撤退。 村头老李头说:“咱们几里地没盗匪,半夜能睡个踏实觉。”那几年,少林保卫团几乎场场有功,匪徒被击退、被缴械,村民收复土地,种稻挖田有个安妥。 恒林去世时,保卫团基础还算牢靠。 这比很多人想得复杂。保卫寺庙、保住僧人、保住庙产,这三样险而微妙。恒林没把寺庙变成军阀据点的野心,他只是想稳住寺庙。 可他死了,接棒的是妙兴。妙兴有年轻气盛,也不太计较那种“佛门传统”怎么对枪支这回事。 他看见直系势力伸手过来,觉得投靠也好——有钱修殿、有人帮着守庙,这比天天怕被火烧怕被抢强。 1922年,樊钟秀到少林,捐银修殿堂。殿堂虽旧,但有人出钱就能修。妙兴接受了。 接着吴佩孚手下张玉山在登封召集军队,听说少林有几百把枪,也听说保卫团人数不小,就想把这些和尚编入军中。 妙兴带头答应,和尚们不只是守庙护寺,更成了军队的一部分。 北伐军打到河南的那阵子,冯玉祥与直系翻脸。 妙兴带着僧兵上前线,战况惨烈。子弹多,炮声震得地动。他在舞阳一战中被打中,倒在乱军里。少林寺失去领军人物,和尚们不知道往哪儿站。保卫团的意义开始模糊,是护寺,还是帮军阀争地盘?战争像猛兽,把少林拉进它的网子里。 1928年春天,火来了。石友三部追樊钟秀,樊钟秀把少林寺当成临时司令部。 这对石友三来说,是不能忍的挑衅。于是火被点燃。 火烧殿堂,藏经阁,禅房里堆着经卷的木架子劈啪作响。火焰吞掉梁柱,房梁倒塌,佛像摔裂。 僧人们慌乱地逃跑,有的抱佛像冲出来,有的转身又被火烟呛到,脚下一滑摔倒。那夜山风吹得厉害,火光飘过山头,村庄被映红。经卷变灰,灰尘落在灰烬上,像是末世的仪式。那一刻,少林寺不仅失去了屋顶,也失去了几百年积攒的安全感。 寺里静下来之后,什么都淡了:烟味、焦木味、血迹,连经声都不容易听到。 僧人们走出废墟,庙产荒了,窑瓦崩塌,香火冷了。 中原局势还没平,日军入侵、饥荒又来,少林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去修。百姓饿肚子,和尚也得混口饭吃。守庙的人少了,留在寺里的人常在夜里听风,看着倒塌的殿瓦,肩膀被凉风拍得疼。 抗战那几年,少林的名字又被历史提起。 有人说战争来了,和尚们戒备,有的端茶递水但手里握着刀。有一本书里记载,《铁流千里》,说皮定均到少林,山门里有人屏息,外头有僧人在墙头持枪的影子。他说见了那情形,没说话就走了。另一部回忆录,《中岳风雷》,写得有点悲壮,说和尚们学着八路军的方式组织,有人教孩子,有人带武装,有人唱歌唱抗日。 登封解放后,小和尚在街头,到处宣讲,有人听得热血,有人觉得荒唐。两本书里对少林的记忆不一样,好像一个人两种脸孔。哪种更真的?史家也说,记住多种声音可能更接近真相。 少林寺从恒林举起枪,到妙兴带兵上阵,再到烈火把殿宇烧成废墟,这条路上是一步步往深坑里走的。保卫本意并没错,可碰到军阀,那条界限一旦跨过去,就被扯碎。 很多时候不是和尚们不想佛门清净,而是没有别的出路。这些选择里都有痛,也都有希望。 风吹过残壁,破殿门上有灰尘落下,苍灰色。 山道上没人走,只有野草在风里摇晃。夜里寺里灯光暗淡,僧人在废砖里叹息。石阶上那条裂缝会让脚滑,屋顶漏雨,风从瓦缝里钻进来。 柴火与焦木的味还在,灰尘还在,少林寺还在,只是人心比瓦片更破碎。





![把溥仪成功改造了,比杀强太多了[6]](http://image.uczzd.cn/31308438519770628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