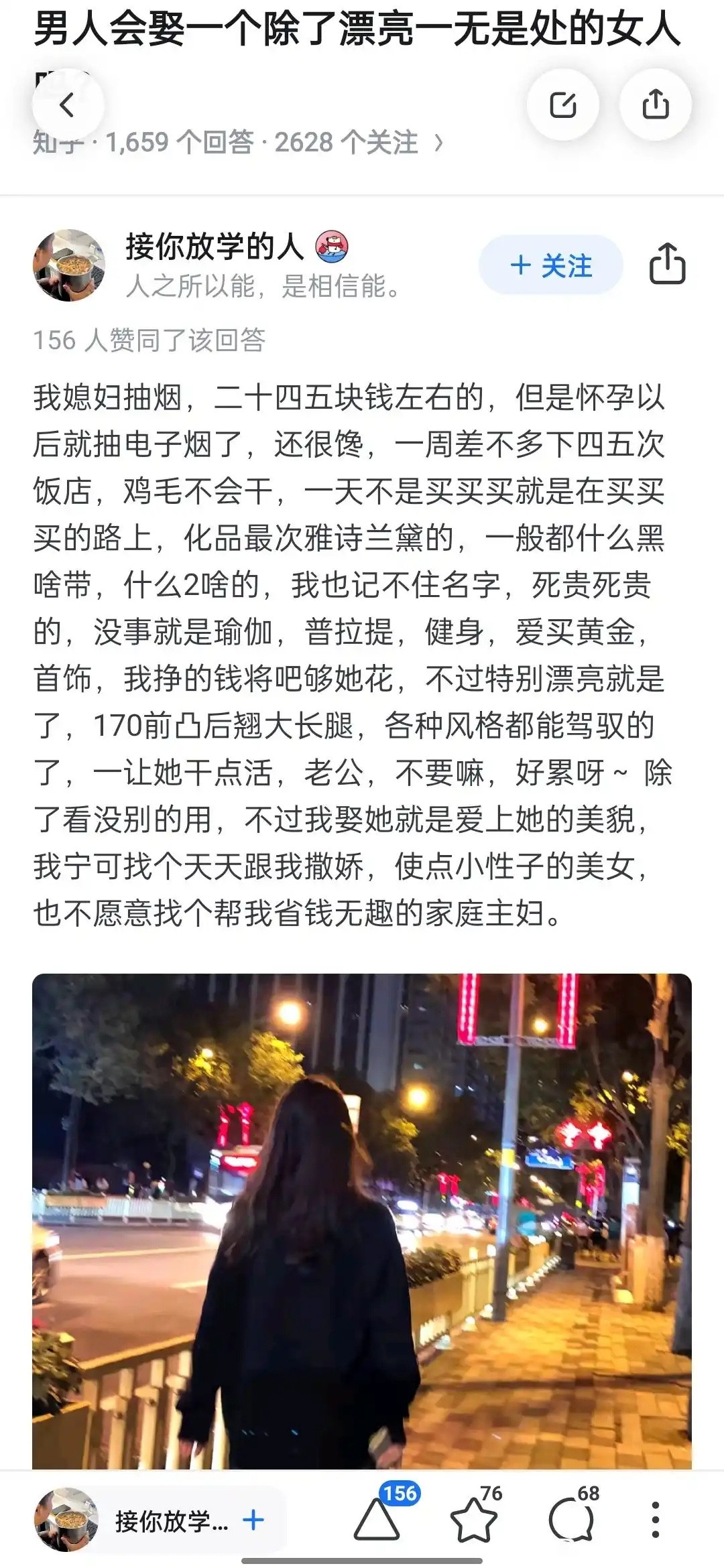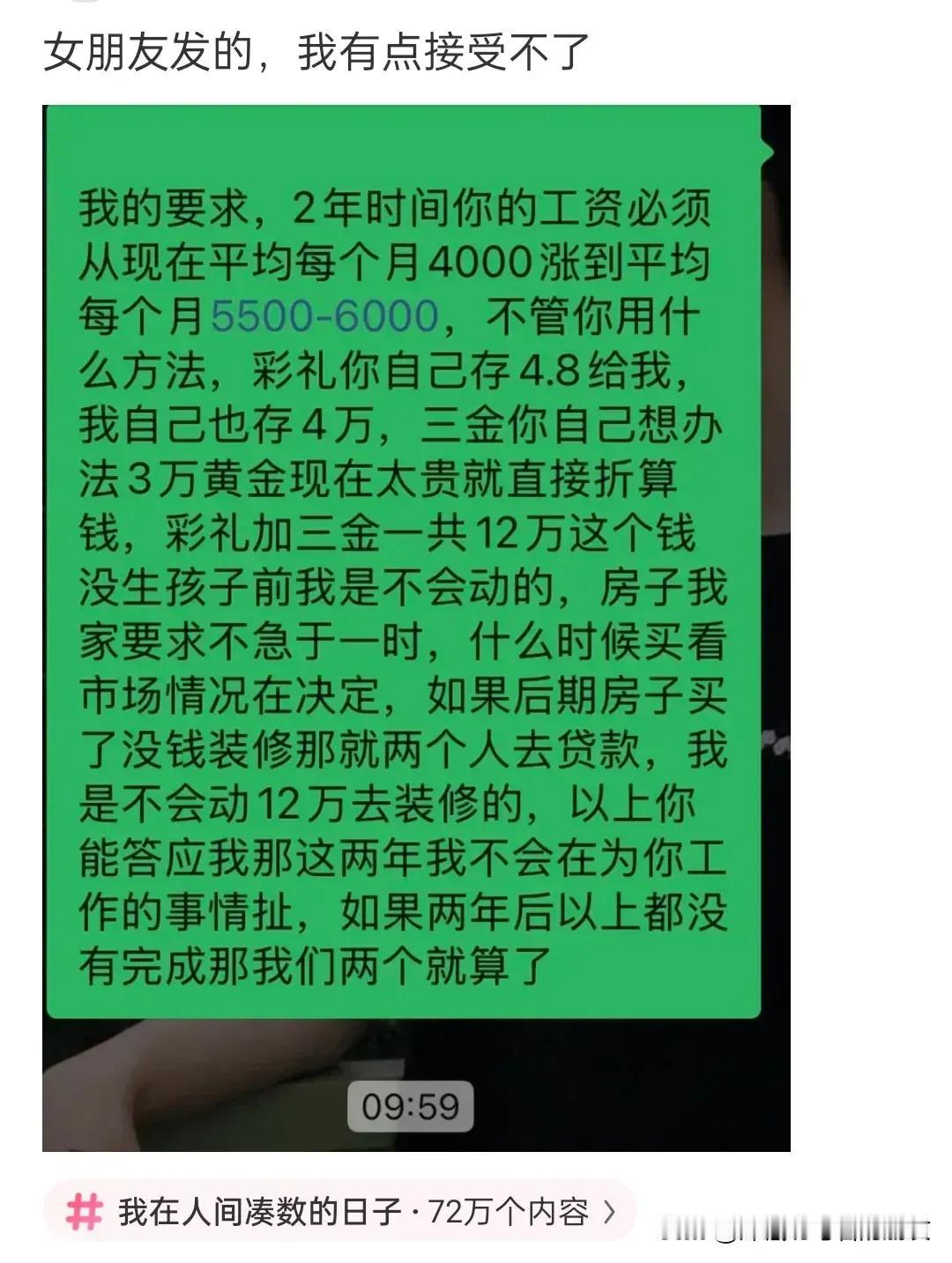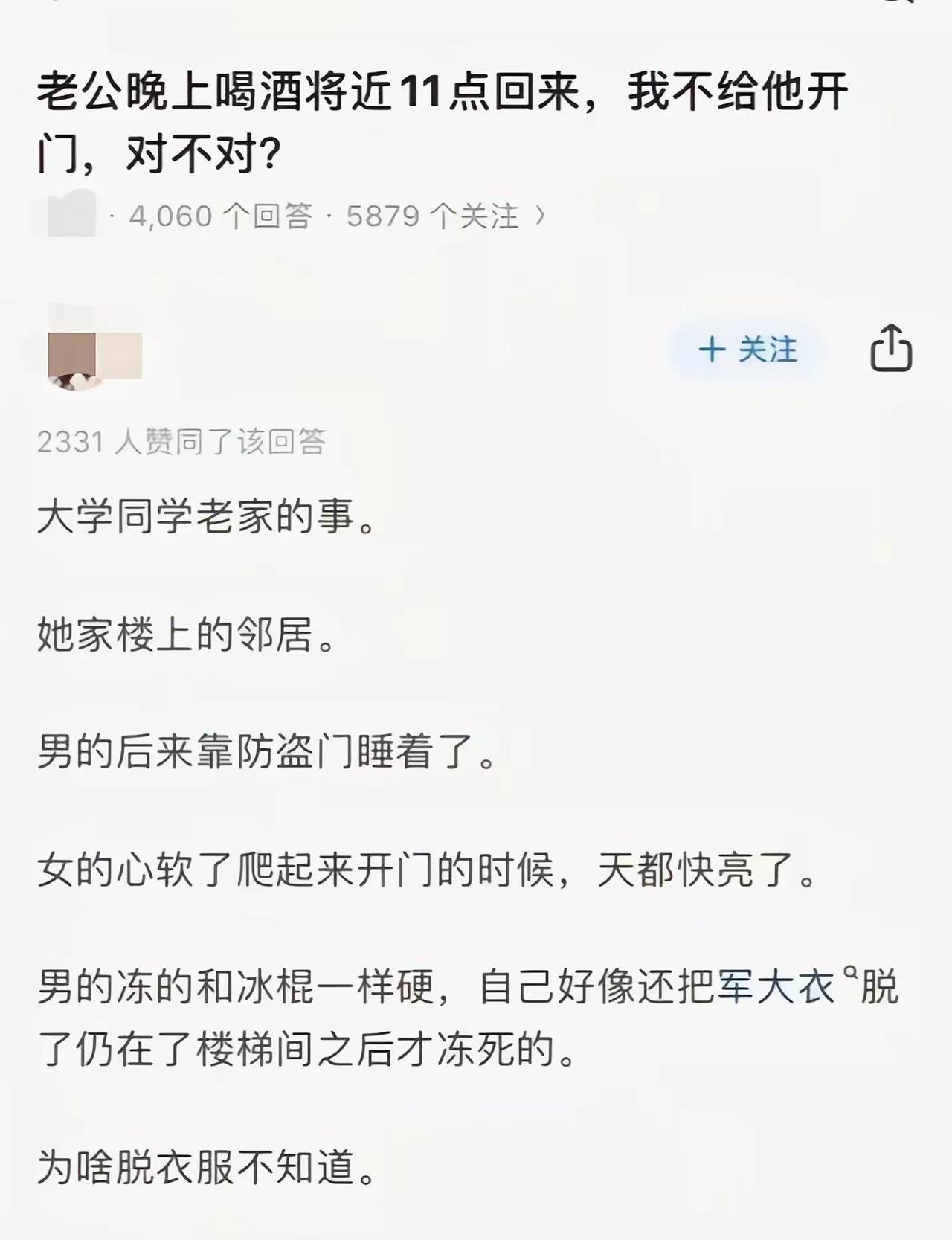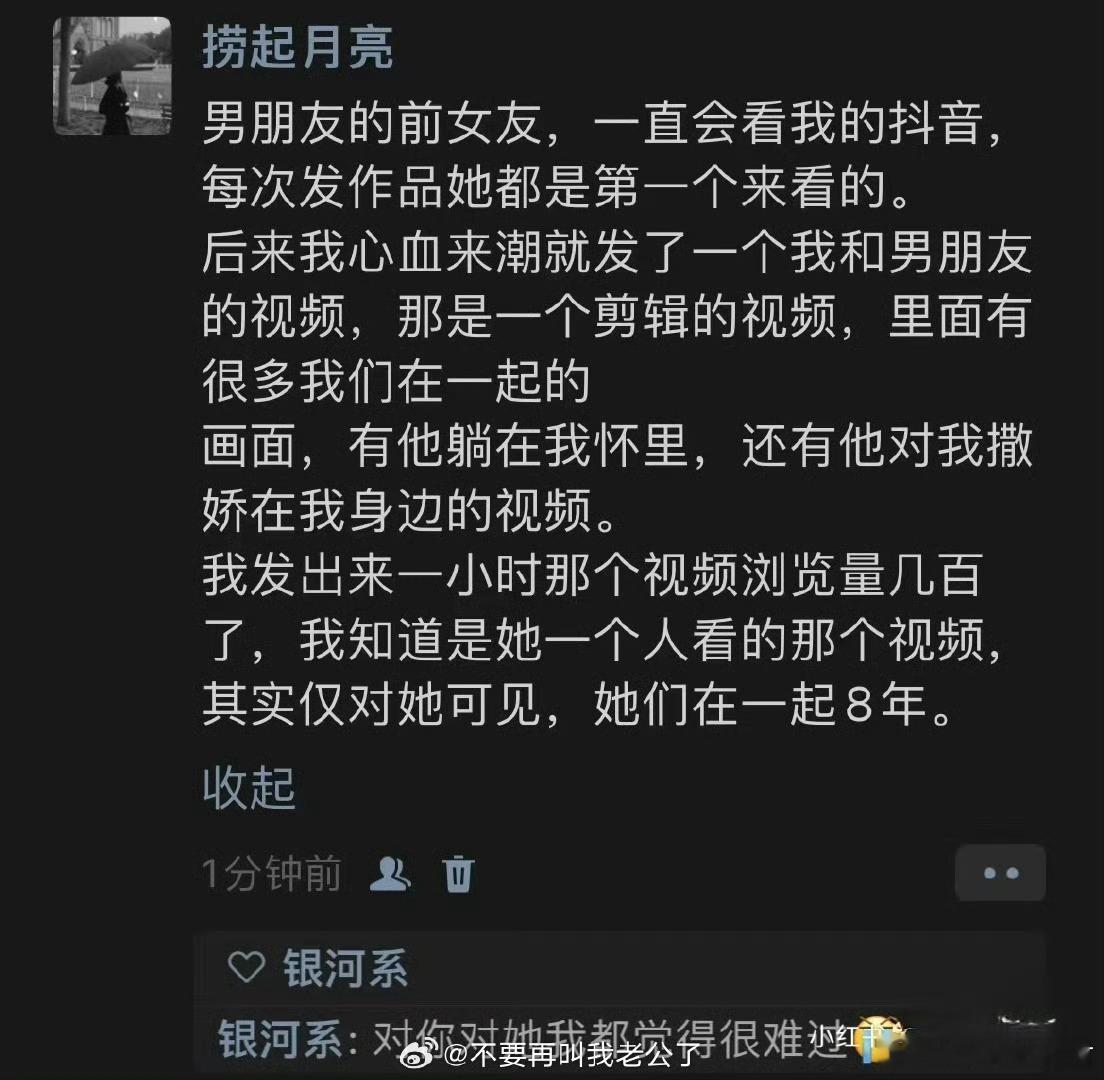元代大画家倪瓒因为洁癖,大半辈子不咋碰女人。有回心一横招当红歌姬赵买儿来陪宿。姑娘没进门先洗了回澡,刚在床榻躺平,倪瓒便从脖子到脚开始且扪且嗅,扪至阴,觉着不好闻,让她再去洗,来来回回一直搓澡到天亮,倪瓒啥也没干成,白白付了钱…… 1373年,72岁的倪瓒蜷在太湖的小船上,船板上摆着他的画案与砚台。 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让老仆人划着小船去湖心汲新水,回来后用细布蘸水反复擦拭画案,连砚台边缘的墨渍都要抠干净才肯研磨。 此时的他早已散尽无锡老家的田宅,元末战乱四起,他怕财富引来祸端,索性把家产分给族人,带着简单的画具漂泊湖上。 可即便居无定所,他的洁癖仍没半分收敛:睡觉时枕头要铺三层干净绢布,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绢布上有没有落灰; 吃饭时碗碟必须用开水烫三遍,仆人端饭时手不能碰到碗沿,否则这顿饭他便一口不碰。 这份对“洁净”的极致追求,早在他二十多岁时就已显露。 彼时倪瓒还是无锡富户子弟,家里庭院种着几株梧桐树,他见树皮上有积尘,便命仆人每天用浸过香料的软布擦拭枝干,连树皮纹路里的污垢都要细细抠出。 仆人劝他“树要接地气,擦得太勤会伤根”,他却不听,执意要“让树也干干净净”。 没过多久,几株梧桐树果然因树皮被磨破、根系受损而枯死,倪瓒见了竟不心疼树,只皱着眉说“脏东西沾多了,死了也干净”。 倪瓒的画,最讲究“简”与“空”,这恰是他心灵洁癖的投射。 他的代表作《渔庄秋霁图》,全画只分三部分:近景是两株枯树、一块巨石,中景是大片空白代指湖水,远景是淡淡的几抹远山,没有飞鸟,没有渔舟,连水波都只用极淡的墨线轻轻勾勒。 他在画上题诗“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笔墨清淡得像能透出纸背的风。这种“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画风,鲜少有人知道,这份“干净”的背后,是他连朋友来访都要彻夜守在门口的偏执; 有回画家徐贲来他家做客,夜里徐贲咳嗽了一声,倪瓒竟一夜没睡,天不亮就派仆人满院子找痰迹。 仆人实在找不到,只好用树叶蘸着唾沫糊弄他,他见了仍嫌脏,亲自盯着仆人把树叶埋到三里外的荒地,回来后还反复洗手,说“沾了痰气,得洗干净”。 倪瓒的洁癖,还让他在乱世中得罪了不少权贵。元末张士诚割据江南时,他的弟弟张士信听闻倪瓒画名,派人送重金请他画一幅《江村渔乐图》。 倪瓒见了使者,当场撕了绢布,把银子扔出门外,说“我倪瓒的笔,只画山水,不替权贵描眉画眼”。后来他在太湖边偶遇张士信的船队,张士信记恨前事,让人把他拖到岸边打了一顿。 倪瓒趴在泥地里,任凭污泥溅满衣襟,却始终紧闭双唇——事后朋友问他为何不辩解,他说“跟这种人说话,会脏了我的嘴”。 即便后来因得罪其他权贵被抓进监狱,他的洁癖也没改:狱卒送饭时,他非要让狱卒把碗举到与眉毛齐高,怕狱卒的唾沫溅到饭里。 狱卒被惹恼了,索性把他绑在厕所隔壁,让他连着几天闻粪臭味,倪瓒虽难受得吃不下饭,却仍不肯低头,说“宁受臭,不沾脏”。 而那桩“请赵买儿却通宵洗澡”的事,发生在他五十多岁时。当时他已离开无锡,暂居苏州,或许是晚年寂寞,或许是想试试“俗世滋味”,便托人请来金陵有名的歌姬赵买儿。 赵买儿不仅能歌善舞,还以爱干净闻名,当时不少文人都愿为她掷千金。可到了倪瓒住处,赵买儿刚进门,就被倪瓒拦住,让仆人备热水,逼她先洗了一遍澡; 洗完进屋躺到床上,倪瓒又凑过去,从她的脖子开始,一寸寸闻皮肤的味道,闻至腰间便皱起眉,说“还有汗味,再去洗”。 赵买儿无奈,只好又洗了第二遍、第三遍,直到天快亮时,她实在累得站不稳,坐在床边哭; 倪瓒却只是皱着眉,扔给她一包银子,让她赶紧走,还吩咐仆人“把她碰过的床褥、枕头全烧了,房间用艾草熏三遍”。 此事后来被杨维桢写进《东维子文集》,与《野获编》的记载相互印证,足见倪瓒的洁癖绝非传闻。 1374年,倪瓒在太湖船上得了痢疾,当时身边只有一个老仆人,连口干净的水都找不到。他一生追求洁净,最终却在污秽中咽气,死时连块干净的绢布都没来得及盖。 可讽刺的是,他那些“干净”的画作,却穿越了六百多年的时光,如今仍藏在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方。 《容膝斋图》《虞山林壑图》每次展出,都能引来无数人驻足,人们赞他的笔墨“清逸淡远”,却也会想起那个为了干净、连歌姬都不敢碰的怪人。 倪瓒的一生,就像他画里的空白,看似简单,实则藏着极致的偏执。他的洁癖是枷锁,让他一辈子活得孤独、拧巴,连基本的人情往来都做不好; 可也是这份洁癖,让他在乱世中守住了艺术的纯粹,画出了别人画不出的“干净”。 中国人讲“中庸之道”,倪瓒却走了极端,可正是这份极端,让他在“元四家”里站稳了脚跟,成为文人画史上绕不开的名字。 主要信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倪瓒的洁癖与清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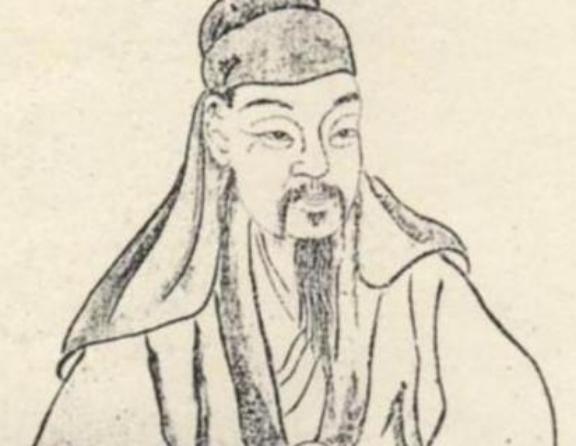
![谁说男人不会哄女人的?这可太会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286881951953198765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