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老舍的父亲战死,母亲决定和大姑子一起过。她打牌、吸鸦片,脾气还不好,可是母亲却不生气,还把她供了起来。等她死后,有个远房侄子来争遗产,母亲也不阻止。 马氏出生在北京德胜门外土城黄亭子村,那地方几户人家都姓马,靠三亩薄田过日子。祖辈是正黄旗庄稼人,农忙时连牲口都雇不起,女人得跟着下地干活。马氏从小就这样练出结实身板,习惯了苦日子。她嫁给舒永寿,生下五个孩子,大女儿嫁小官,二女儿嫁开酒馆的,日子还算凑合。1899年2月3日,她生下小儿子舒庆春,就是后来的老舍。那年她41岁,生产时差点出事,孩子差点冻僵,大女儿抱在怀里才救回来。次年夏天,北京城乱套,义和团起事,联军进攻。舒永寿守正阳门,中枪战死。马氏抱着周岁儿子,面对空荡荡的家,从此独自拉扯孩子。 联军进城那天,北京满城搜掠,马氏带着孩子藏起来,士兵两次闯院子,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咬牙扛过去,开始靠洗衣缝补养家。舒永寿死后,马氏把丈夫的寡姐接来同住。这寡姐整天躺炕上,抽鸦片烟,烟枪点着,屋里一股呛味。她爱叫人来打牌,牌桌上甩牌砸桌子,输了就骂街。脾气坏到家,饭菜不合口就推碗,衣服扔地上不管。家务她一指头不沾,全扔给别人。马氏从不计较,每天烧水端茶,伺候得像长辈。寡姐嫌粥凉,马氏添柴重热,从不说重话。每个月初七领抚恤钱,马氏先称二两烟土给她,确保分量足。 寡姐这样过了几年,到舒庆春上中学时才去世。马氏哭得伤心,像丢了亲姐妹,泪水直流到坟地。灵堂没撤,一个远房侄子冒出来,说有权继承财产,指着破桌椅要带走。马氏没争,点头让人搬,还把寡姐养的肥母鸡塞给他。邻居说她傻,马氏只说这是积德,不值一提。她觉得命里该着,没受婆婆气,就得忍大姑子。寡姐的坏脾气没动摇马氏的忍耐,她总劝孩子,这是旧社会的规矩,得咽下去。 马氏继续过苦日子,靠给人洗衣缝补维持。双手常年泡碱水,红肿裂口,指甲缝嵌灰尘。她在院墙上用碎瓦片划杠记账,赊烧饼三组,水钱五组,月底摸墙算得准。送水汉推车过胡同,倒两桶水划一道,从不欠账。她教孩子,手脚勤快就有出路。舒庆春一度逃学,她摔搓衣板,逼他抄三字经三遍,从此他认真念私塾。马氏帮邻居接生、刮痧、剃头,从不收钱。院里石榴树和夹竹桃,她年年浇水,枝叶茂盛,夏天开花。 孩子们长大,马氏供他们上学。舒庆春后来成作家,回忆说写文章像洗衣,得搓出亮色。她纳千层底布鞋,从开春护到腊月,针脚密实。街坊敬重这个满族妇人,她不懂大道理,却总在井边洗衣时分享经验。马氏的性格软硬结合,庚子年后兵变内战,她护孩子不慌,从无路中找出路。她的泪往心里咽,这种劲头传给儿子。马氏活到84岁,1942年去世,那时舒庆春不在身边。他继承了她的倔强,写书时常记起她的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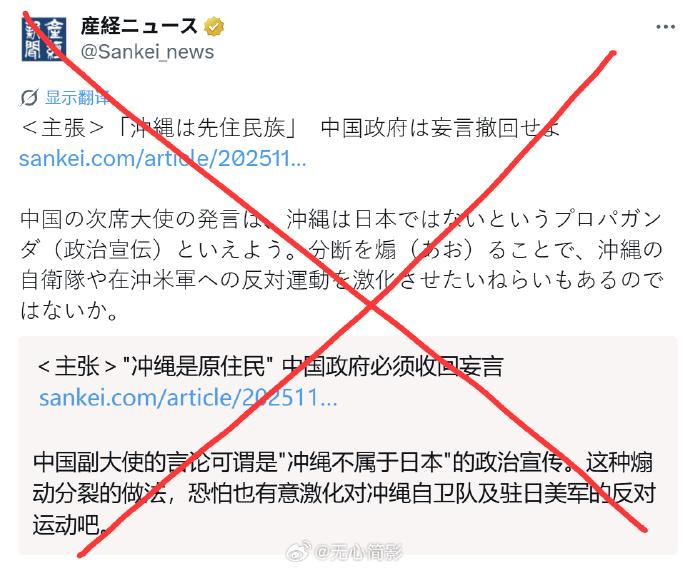


用户10xxx98
旗人有铁杆庄稼的,好象一月2两,老舍先生正红旗下自传体写的,那个姑太太,也有点儿钱傍身的,老舍的大姐嫁了个世袭四品武官之家,老公与公公都是连马也不会骑了,亲家太太爱虚荣,对大姐很坏,又骂又打的。老舍他们家族与亲戚邻居都是在旗的,认识所谓红带子黄带子,总之,汉人回人都不敢怼他们的,他们居在满族人居集处。这些个都是中下层旗人,因大多不事生产,所以二百多年过去,日子也开始变得拮据起来。小说未写完,老舍先生就自杀身亡了。这部小说我是在听书平台喜马拉雅上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