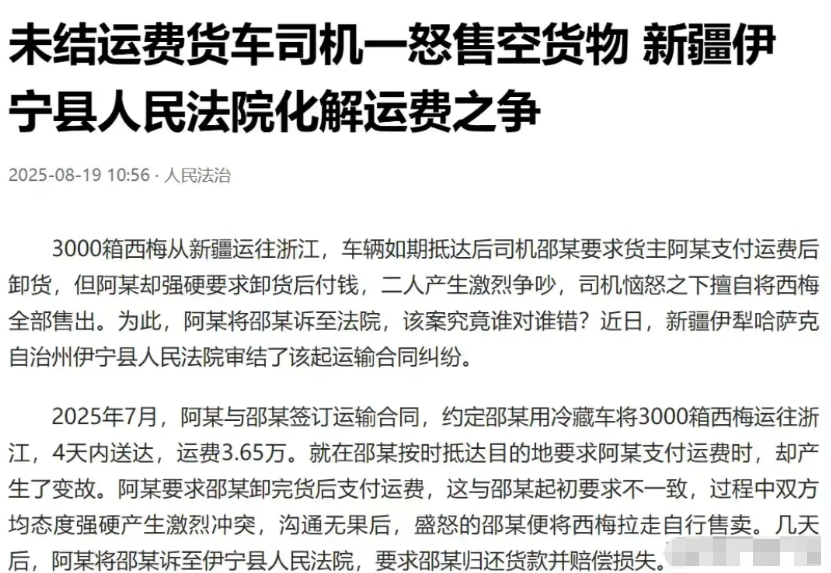浙江杭州,一28岁男子去同事家吃饭,期间参加线上工作会议,直至23点31分才结束会议。不料,下线仅六分钟,男子便猝然倒地,经抢救无效离世。事后,家属坚持认为他长期超负荷工作,直至最后一刻仍身处工作状态,因而申请工伤认定。然而,当地人社部门却做出不予认定的决定,理由是其发病时已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家属对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继续提起申诉。 8月21日,极目新闻报道了一起因劳动者在非传统办公场所、非标准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亡而引发的工伤纠纷案件。 据悉,2025年5月21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但对于28岁的区域经理张伟(化名)来说,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张伟是温州公司驻杭州萧山区的区域经理,负责管理一支庞大的外卖骑手团队,他的工作节奏,用其妹妹张悦(化名)的话来说,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办公”。 早上6点,当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时,张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的手机和电脑就是他的移动办公室,无论是在家中、宿舍还是咖啡馆,工作指令永不间断。 这天下午,张伟来到一位同事家中,既是朋友间的聚餐,也顺便聊聊工作上的事。 晚上8点,一场线上工作会议准时开始,作为区域负责人,张伟需要向上级汇报近期工作,并与其他区域的同事协同下一步计划,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1点31分,张伟才从线上会议室退出。 之后,张伟和同事开始用餐,想借此放松一下,然而,仅仅6分钟后,晚上11点37分,意外发生了。 张伟毫无征兆地突然倒地,不省人事,同事惊慌失措,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 救护车呼啸而至,将张伟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但一切为时已晚,5月22日凌晨,医院宣布张伟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为“呼吸心跳骤停”。 医生向后续赶来的家属表示,这种情况可能与长期过度劳累、身体透支有关。 张伟的离世,对他的家庭而言犹如晴天霹雳,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是全家的经济和精神支柱,父母是淳朴的农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正在读书。 在处理完后事之后,张伟的家属与公司进行了沟通,公司方面虽然对张伟的离世表示遗憾,但并不认同这是在“工作时间”内发生的意外,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支付9万余元的补偿。 对于这个结果,家属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张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直至去世前一刻仍在参加线上会议,其死亡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于是,家属向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2025年8月14日,人社局出具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是,张伟是在会议结束、开始用餐后发病的,这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 8月20日,面对这一结果,家属不服,依法提起了申诉,再次提交了材料。 目前,人社局暂未回复。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呢? 1、人社局认为,张伟发病时间不在“工作时间”,且事发地点在其同事家,不符合工伤条件。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 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指用人单位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或完成特定任务的在岗时间,但是,张伟病发的时间是在晚上11点多,且发生在参加会议之后6分钟,伤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 而且,“工作岗位”通常指用人单位固定的办公场所,但是,张伟事发时在同事家中用餐,不属于其惯常的“工作岗位”。 因此,张伟的病亡时间,既不是在工作岗位,也不是在工作时间,当然不属于工伤。 2、张伟的家属认为,张伟的死亡虽然不是在单位及传统工作时间,但其病发时正在为了工作,属于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合理延伸,依法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方面, 对“工作时间”应做合理性延伸解释。 张伟参加工作会议刚结束6分钟,其身体和精神仍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后的持续期,与工作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和连续性,不应机械地以“退出会议”这一刻将其后的时间割裂出工作范畴。 另一方面,对于“工作岗位”不应局限于固定的物理场所,而应根据其职责性质来确定。 张伟作为区域经理,随时随地工作是常态,在同事家亦是进行工作会谈和线上会议,已经临时性地转变为他的“工作场所”,理应认定为在“工作岗位”上。 因此,张伟的死亡符合工伤的条件。 3、不得不说,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可能采取了相对保守和机械的认定标准,不一定准确。 接下来,张伟家属可以继续申诉,在申诉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提起诉讼,争取合法权益。 同时,即便最终认定为非工伤,但张伟家属仍可以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以张伟死亡与工作有直接因果关系为由,主张死亡赔偿金等赔偿。 对此,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