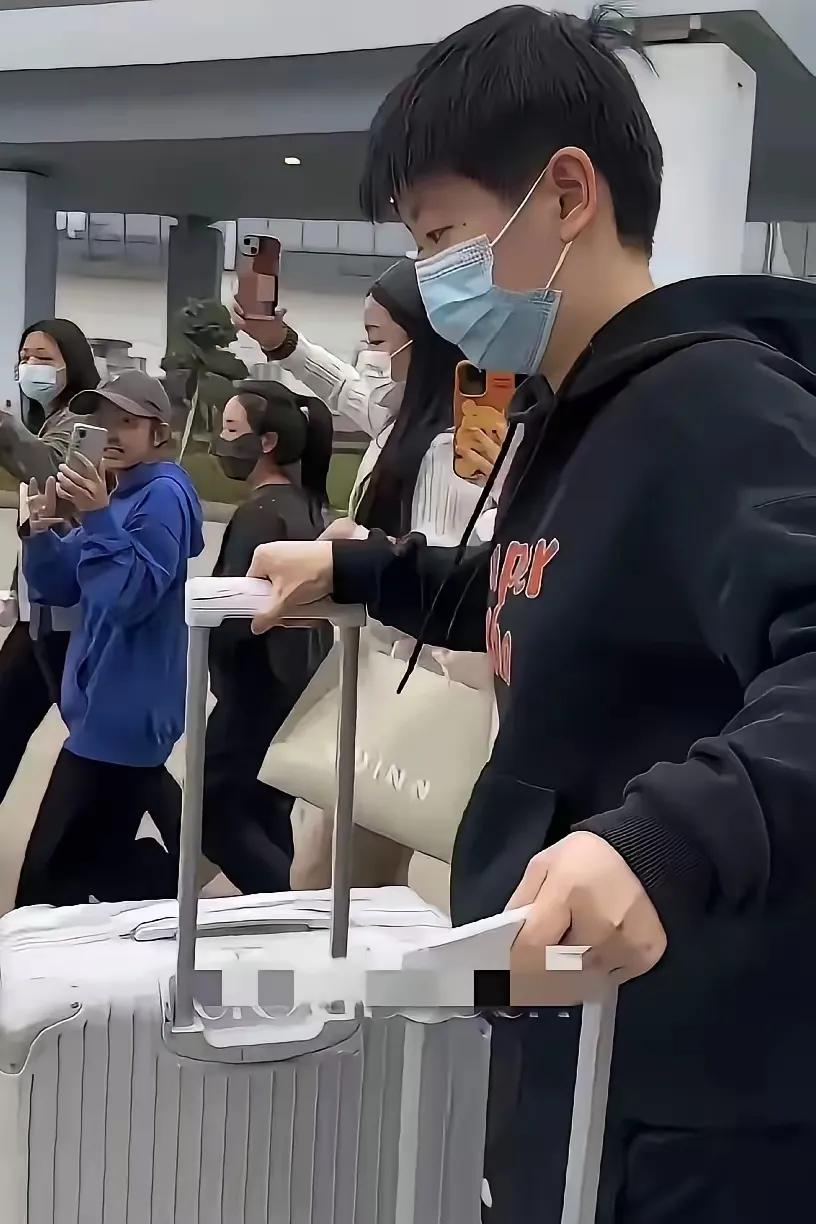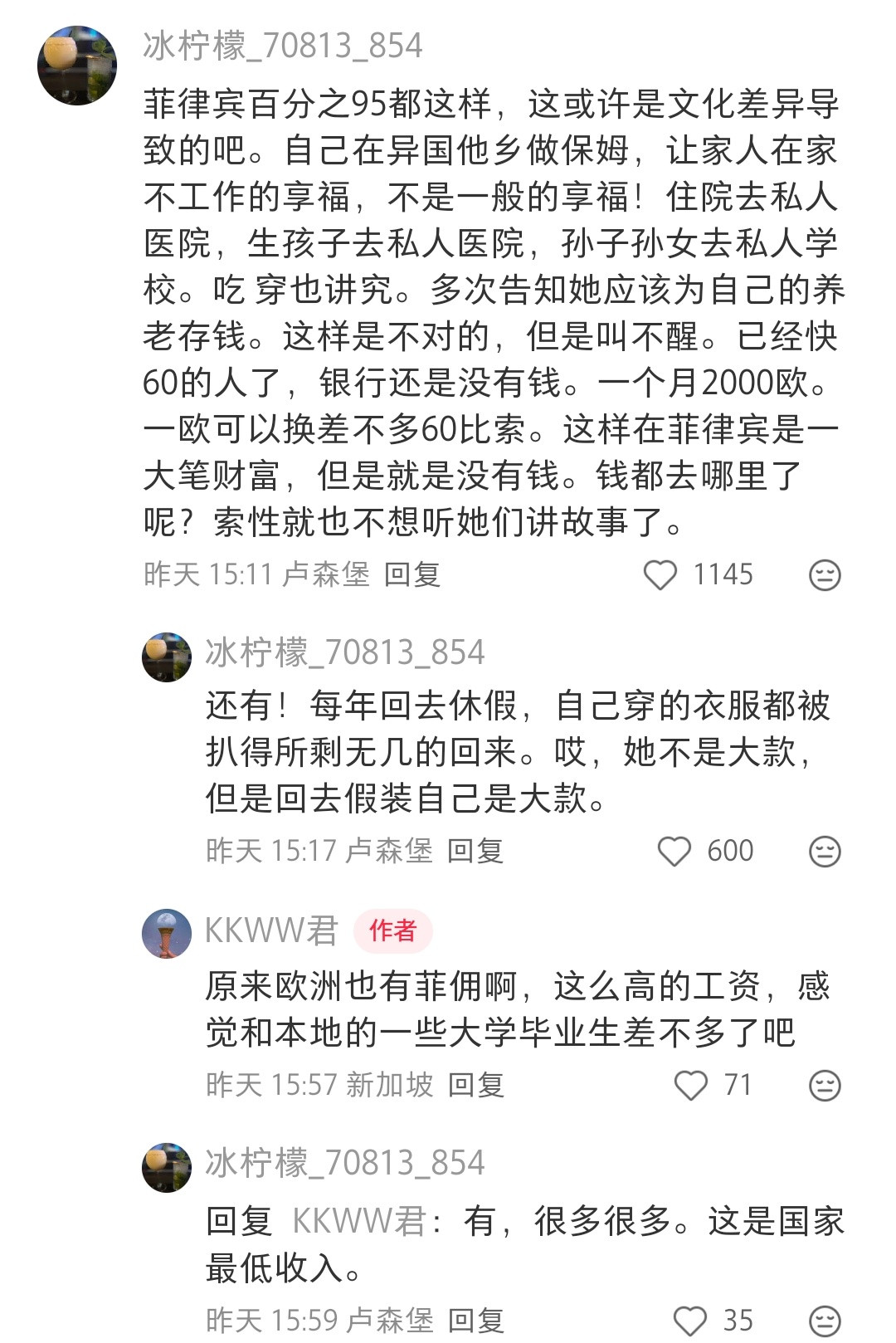51年洪学智妻子寻女无果,到老乡家歇脚,不经意的交谈间,妇人突然惊呼:“是你啊!当年就是你把孩子留给了我呀!” 1939年的抗日战场,那是真的在“玩命”。 1939年在敌后行军,很多决定不是“选更好的”,而是“选还能活下去的”。 洪学智率抗大分校向敌后转移时,队伍要躲追兵、绕封锁线,白天不敢走大道,夜里赶路也不敢点灯。 张文那时抱着大女儿,孩子还很小,饿了要哭、冷了要哭,一哭就可能把整支队伍暴露出来,在那样的环境里,一点声音都可能引来扫荡,牵连的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一群人的命。 张文是母亲,但她也是部队里的一员,她要跟着队伍转移,最难的是她明白“孩子哭”不是孩子的错,可后果却要大家一起扛。 于是她在山西阳曲县一个小村子里,做了一个决定:把襁褓里的女儿,托付给当地一对农民夫妇。 临别时,她把孩子头上那顶带红五星的小帽子,摘下来留作信物——那是她能留下的、最直观也最不容易弄丢的标记,她当时大概是想着,等局势稳一点、打完仗,就回来接。 但战争不是按人的愿望走的,一转身,很多事就再也由不得个人安排,张文离开后,孩子在村里被收养,日子一过就是十二年。 收养孩子的农妇叫白银翠,她自己也有孩子,家里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很拮据,可她还是把这个红军留下的娃,当成自家骨肉养。 为了让孩子有奶吃,她把自己的幼子托给远亲照顾,自己把奶水留给这个孩子,这种选择放在今天都很难想象,更何况是在战乱年代:粮食紧张,野菜糠饼是常见的饭,冬天柴火不够,孩子病了也未必有药。 白银翠给孩子起名“红红”,不是为了好听,而是为了让孩子将来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几年日子有多苦,很多细节不是一句“艰苦”能带过去的,粗粮要省着吃,孩子长身体,却不能断口粮;躲扫荡、躲轰炸时,大人抱着孩子往窑洞、山沟里钻,夜里不敢点灯,咳嗽都要压着声。 白银翠自己能忍的都忍了,能省的都省了,尽量让孩子不觉得自己“被丢下”,在她眼里,这不是“帮别人养孩子”,这是把一条命接过来,接住了就得负责到底。 张文那边并不是没有牵挂,只是她在部队里辗转,生活也不可能稳定,联系不上、回不去,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支撑:孩子还活着吗?过得好吗?有没有挨饿受冻? 这种想念,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回音,想得再多也无法确认。 到了1951年,洪学智要赴朝作战,临行前他交代张文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嘱托,其实背后是多年积压的亏欠:战场上可以把命交出去,但回到家,心里那块空缺一直在。 对张文来说,这既像命令,也像一个家庭终于能做的补课,张文回到山西找人找村。 可十二年过去,村名可能改了,住户搬迁,知道当年情况的人也未必还在,她只能靠当年的零碎记忆一路问:哪一年、哪个方向、附近有什么地标、那户人家姓什么。 她敲门、打听、再走,很多次都是空欢喜,找孩子这件事,在当时没有今天的户籍联网、没有信息化登记,靠的就是腿和嘴,靠一遍遍解释“我当年把孩子托付给人家”的经历,靠别人愿不愿意相信你。 转机来得很偶然,她在阳曲县一个村子里,跑了一整天没结果,天快黑了,想着先讨口水喝,便进了一户人家。 女主人端来热水,寒暄几句,张文忍不住,把心里压了多年的事说出来:1939年冬天,她抱着孩子行军,最后不得不把女儿留给当地人,还提到了那顶带红五星的小帽子。 话说到这里,对面的农妇手突然停住了,她抬头盯着张文,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然后声音都变了:“大妹子,是你啊!孩子当年就是你留给我的。”这户人家,正是白银翠家。 两个母亲当场哭成一团,但真正难的不是相认,而是接下来怎么让孩子接受,那时的红红已经十二岁,站在一旁怯生生地看着,反而往养母身后躲。 对她来说,穿军装的张文,是突然闯进生活的陌生人,而白银翠才是她从小喊“娘”的人,孩子的反应非常现实:她不是不想认亲生母亲,而是她的安全感、依赖感都在养母那里。 白银翠的做法让人佩服,她心里当然舍不得,养了十二年,怎么可能不疼?可她还是把孩子推到张文面前,说这孩子应该跟亲娘走,亲娘是干“大事”的,去北京读书比留在山沟里有前途。 这话听起来朴素,却很重:她把自己最舍不得的放开了,而且不是放开就撒手,而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路。 张文也没有粗暴地,把孩子“带走就算了”,她住下来,陪孩子说话,慢慢让孩子熟悉自己,弥补那十二年的空白。 同时她也给白银翠夫妇一个交代:孩子跟他们去北京读书,但养父母永远是孩子的亲人,往后要常来常往,要照顾两位老人。 这个承诺,后来也确实兑现了,临走那天,红红终于喊了张文一声“妈”。 这一声对张文而言,不是“身份确认”,更像是把十二年的悬空落回地面,回到北京,洪学智见到女儿,这个在战场上见惯生死的人也红了眼眶,抱着孩子很久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