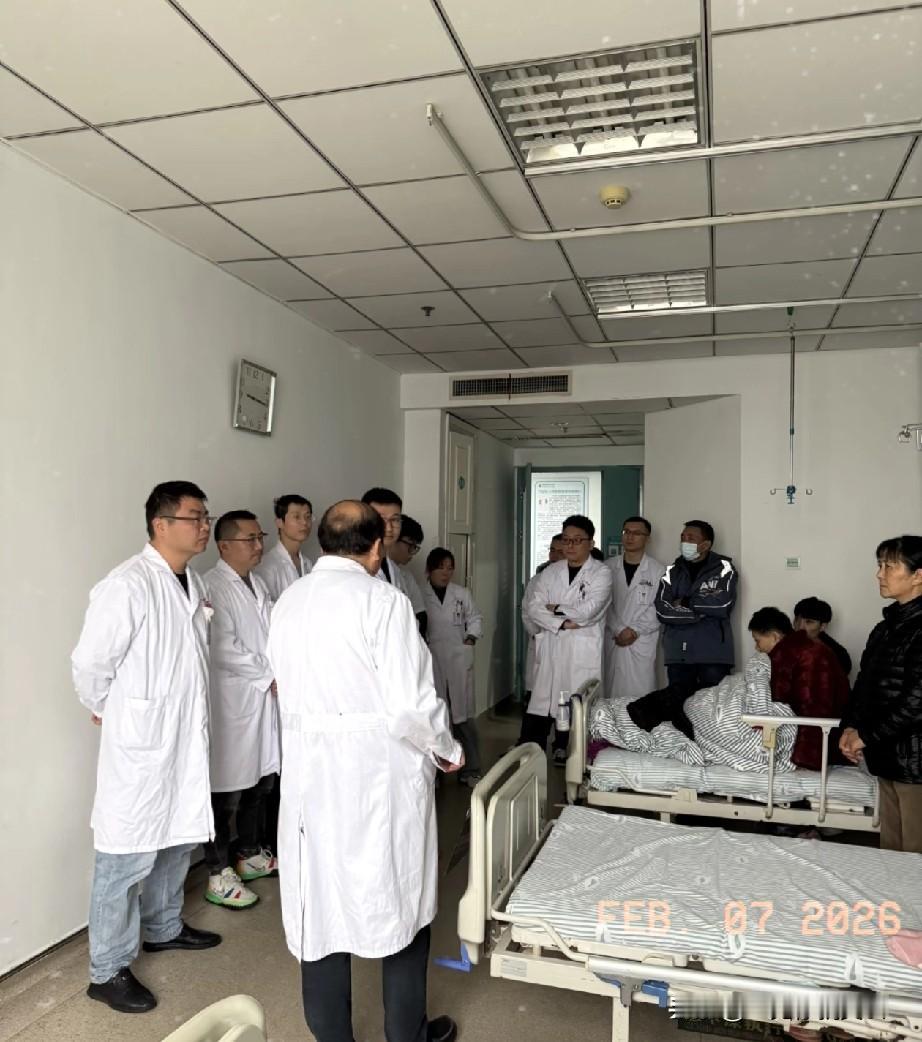1995年,东莞市殡仪馆内送来了一具已经有味道的女尸,火化工人何亚胜正打算把她推进炉子里火化,却惊讶的看见女尸的脚动了一下! 1995年,东莞的夏天闷得厉害,殡仪馆那种热不是太阳晒出来的,是人多、炉子热、空气不流通,混在一起的一股潮湿味。 火化间外头排着等候的车辆,推车的脚步声、铁门开合声来回不断,忙到让人连喘气都觉得奢侈。 何亚胜那年22岁,是殡仪馆的火化工人,那天他站在运尸车旁边,按流程准备把一具“无名尸”送上去。 尸体盖着布,手续上写得很清楚:已经由相关人员确认死亡,送来火化,对殡仪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没有家属、来路不清、处理也就按规矩走。 他手都已经搭到传送带按钮附近了,按下去,车就会往炉口移动,可就在那一瞬间,他盯着布下露出来的一只脚,突然觉得“好像动了一下”。 不是大幅度的抬腿那种动,就是很轻、很短的一下抽动,幅度小到一眨眼就可能当成错觉。 很多人遇到这种场面会本能后退,甚至喊人,因为太像恐怖片,何亚胜没有,他先是愣住,然后把布掀开一点,凑近看。 再后来,他干脆蹲下去,把耳朵贴在那具身体的腹部位置,想确认有没有呼吸或肠鸣那类细微动静,贴上去那几秒,他听到了很微弱的起伏感,不明显,但不像完全的“静”。 他立刻停了所有流程,喊人、打电话,把人往医院送,殡仪馆到医院那段路不长,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每一分钟都在赌,因为那具身体已经到了临界状态:稍微再拖一会儿,真的可能救不回来。 后来确认下来,这个差点被送进炉子的女孩叫陈翠菊,当时18岁,贵州榕江人,她来广东打工并不特殊,那几年南下的人很多,家里凑路费、孩子出来闯、寄钱回去,是不少农村家庭的指望。 可现实也很硬:身体吃不消、水土不服、在工厂里病倒,往往就意味着工作没了、住处也保不住,你没有亲戚朋友接应,很容易一下掉到城市的缝隙里。 陈翠菊后来被发现时,已经是严重营养不良和脱水的状态,极端虚弱的人,有时会出现类似昏迷甚至“假死”的表现:体温低、呼吸浅、心率微弱,肉眼不易察觉,若现场条件差、判断仓促,就可能被误判。 她最终会出现在“无名尸”的流程里,倒下了没人认识,送来的人也只按“发现尸体”处理。 等进了医院之后的情况更难,医生看到她的第一眼被震住:瘦到几乎只剩骨架,皮肤干裂,意识不清,合并酸中毒、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风险很高。 护理也很棘手,长期流落在外的人身上往往有污垢、溃烂、感染,处理起来既辛苦也让人心理上很难受。 很多护工会退缩并不意外,工作条件太差、风险太大、气味和脏污也确实超出一般人承受范围。 最后扛下来的,是医院里一些护士和医生,她们得给她清理、翻身、擦洗、处理皮肤破损,喂流质、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一点点把生命体征拉回来。 家属后来也联系上了,对贵州的家庭来说,去一趟东莞要钱也要路,家里卖猪卖粮凑车费,医院方面据说也有减免和同事捐助,让人能回家、能继续活下去。 如果故事到这里,其实已经足够让人感慨:一条命从火化间门口被拉回来,靠的是一个工人多看一眼、敢停手、敢多确认;靠的是医院没有把人当成“麻烦”,而是当成病人处理。 但这件事后来还有后续,陈翠菊“死而复生”的消息,当年引发过关注,后来有一位画家陈仲濂被这件事触动,写信提出资助她学习绘画。 对一个几乎被城市吞掉的女孩来说,光“活下来”并不等于“能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技能、拥有一条能立足的路,才算真正离开原来那种命运。 她之后的十年,并不可能是轻松的逆袭,一个识字不多、底子薄的人学画,最先遇到的是基本功:握笔、构图、临摹、色彩、耐心。 学艺的过程也往往很苦,手抖、画坏、被退回重来,都是常态,但她如果能坚持下来,就说明她确实抓住了那次“被拉回来”的机会,把它当成了第二次生命。 后来她回到东莞,去殡仪馆看当年的救命恩人,行大礼、送画卷的桥段,在不少转述里都有,那幅《旭日东升》里画到殡仪馆运尸车的细节,也很有象征意义:对别人来说那是死亡的工具,对她来说却是“把她从死亡边缘带走”的起点。 所谓奇迹,很多时候并不是天降好运,而是有人在自己本可以按规矩走完流程的时候,愿意多负一点责任、多花一点心思。 对陈翠菊来说,那一点点“多做的动作”,堆起来就是一条命、也是后来完全不同的人生。 信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