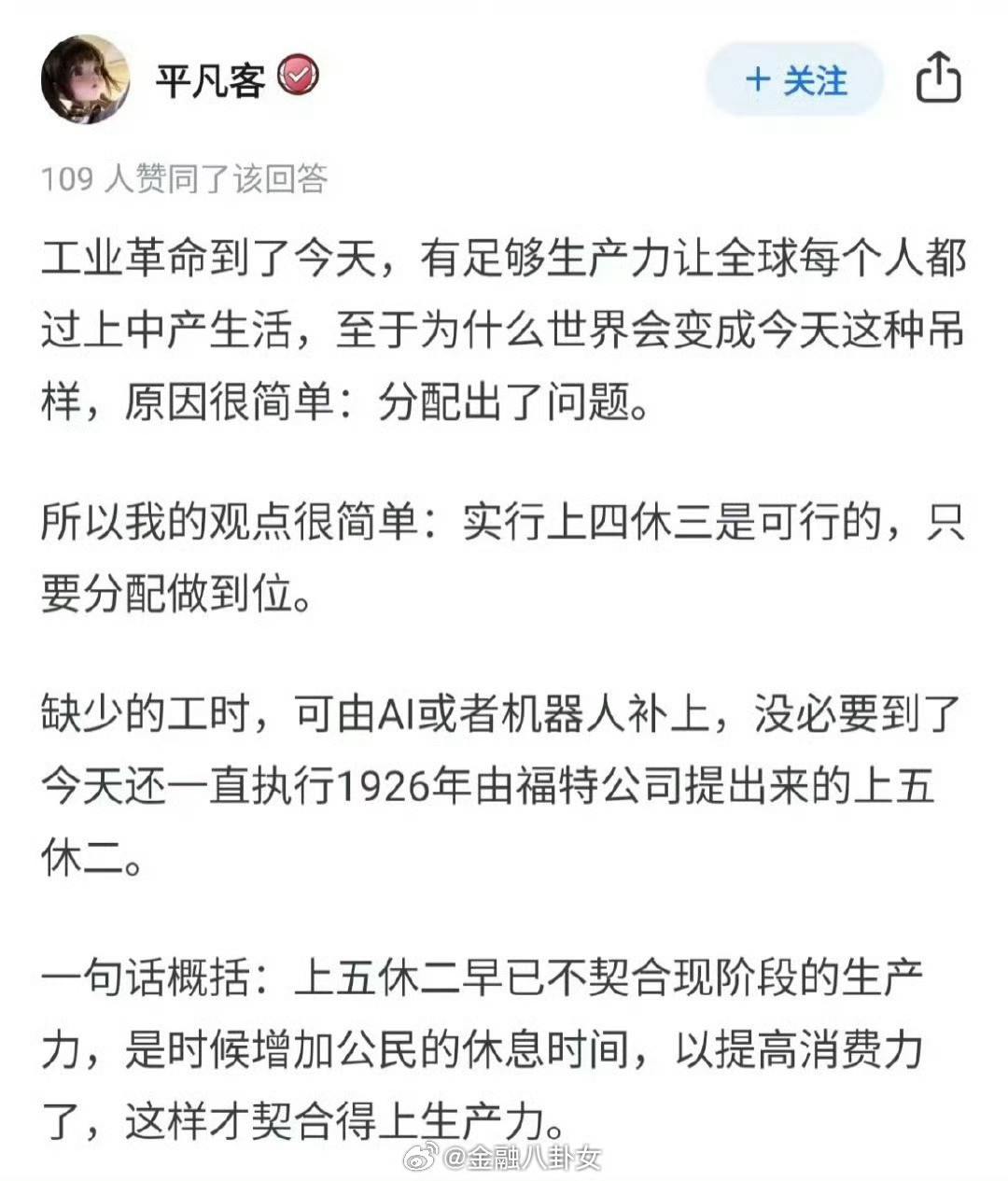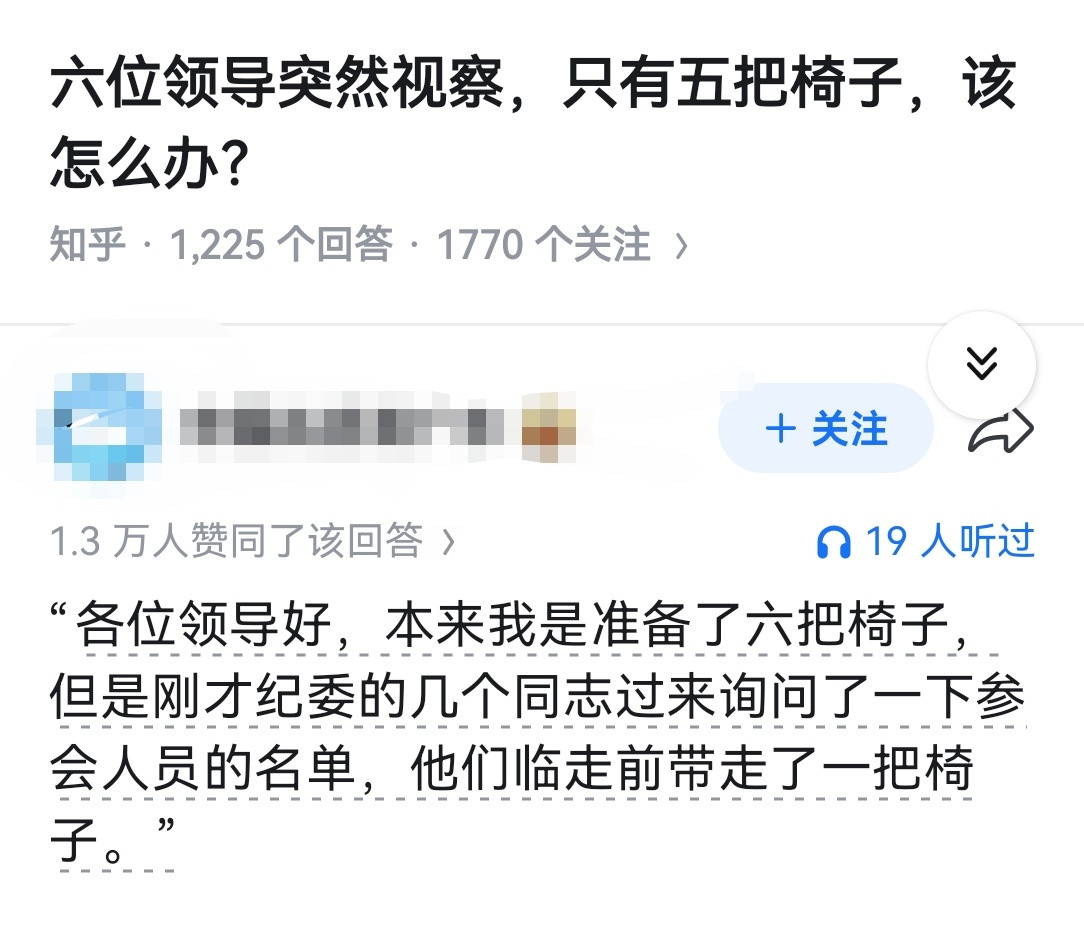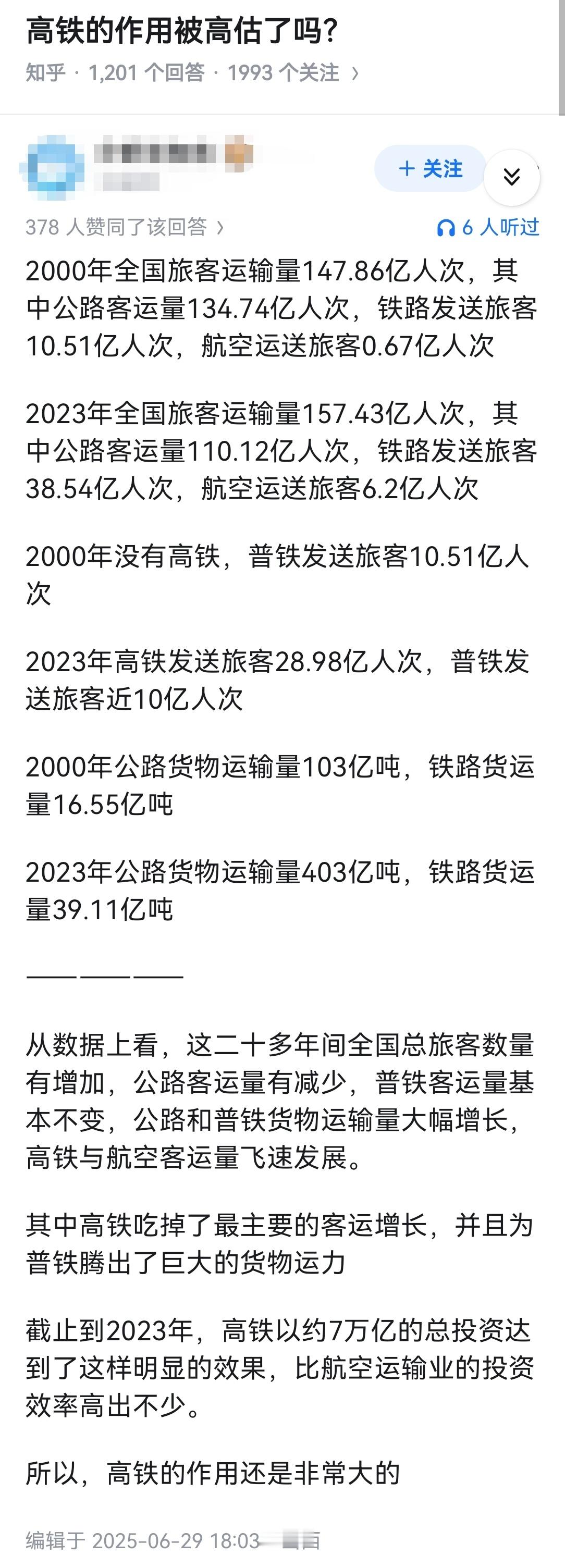那会儿气温刚过零上,尸体已经开始发硬、变色,干部们蹲在坑边,掐着表算时间。 老百姓不愿意干,说“他们烧了我家房,还让我埋?”干部没讲大道理,只指着村头咳嗽的孩子:“尸臭一散,病倒的可是你娃。” 挖坑的人里,七成是戴脚镣的犯人。有个叫杨玉立的,抢着往最臭的港里河大坑里跳,后来减了三年刑,裁定书现在还在莱芜档案馆。 衣服都差不多,灰布褂子,粗布鞋,连个名字都没绣,只有吐丝口井底一具年轻尸体怀里,半块干粮上留着牙印。 没立碑,没登记,没通知家属。但那年夏天暴雨连下十天,地没烂,田没荒,庄稼照长。 六千人,就沉在弹坑、战壕、废井里,和山东的土混在一起。 土不说话,只记得谁在寒风里,一锹一锹往下埋。 冻土之下,尸体,时间,还有几把旧铁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