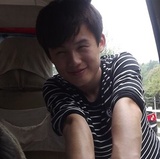四野后代联谊会,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按父辈的军衔排座次。 东北炖菜的香气飘满了整个包厢,酒杯轻轻碰着,屋里全是聊当年勇的嗡嗡声。 突然,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一道缝。 一个穿旧中山装的老头,默默地走了进来。他谁也没看,径直走到主桌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轻轻放在桌子正中央。 信封发黄,上面浸着一片暗红色的血迹。 组织者刘煜滨端着酒杯的手,在半空停住了。他死死盯着信封一角那个“绝密”的戳印,整个屋子的嘈杂声好像瞬间被抽走了。 “我父亲,没军衔。”老人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桌上。 刘煜滨没说话,起身,从旁边搬了把椅子,稳稳地放在主桌最显眼的位置,对着老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那天,一封迟到了几十年的绝笔信,被当众打开。一个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独自引开敌人,最后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的无名英雄,活了过来。 全场没人动筷子,一桌子热菜,从头到尾,凉透了。 散会后,刘煜滨追上那位老人,只问了一句:“我能做点什么?” 老人没说话,只是把一块旧怀表塞到他手里,含着泪,点了点头。那怀表早就停了,但攥在手里,沉甸甸的。 从那天起,这群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彻底变了。 聚会不再是喝酒叙旧。他们自掏腰包,成立了一个史料小组。有人跑档案馆,一查就是一整天;有人驱车几千公里,去寻访当年的战场遗迹;那位英雄的儿子,揣着父亲的怀表,跑了十几个省,只为找到一个还记得父亲名字的战友。 为了给那位无名英雄追认烈士,刘煜滨带着材料,一次次去跑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有人不解,问他们图什么。 刘煜滨把那封带血的信封复印件拍在桌上:“我们是英雄的后代,不能让英雄连个名字都没有。” 几年后,烈士证明书发下来的那天,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纪念馆里抱头痛哭。 如今的联谊会,规矩也改了。 开场前,所有人会对着那封装裱起来的带血信封,举起右拳,默哀一分钟。 至于座位,也不再看父辈。刘煜滨指着前排的空位说:“谁为这些无名英雄做的事最多,谁就坐这儿。” 这,成了他们唯一的新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