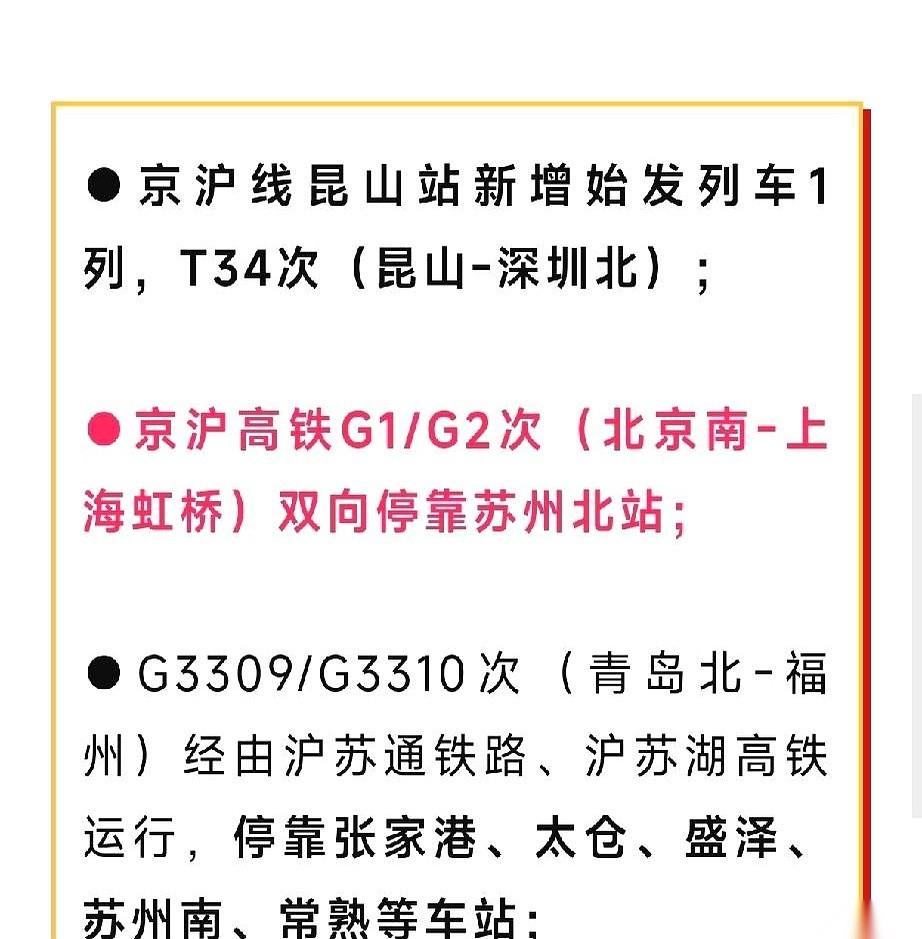上午我在县城老街河西边散步,一位坐电瓶车上的 “老妇女” 向我招手,问我玩不玩,有 50 一次和 100 一次的,我很诧异。 我后退半步打量她,蓝布衫领口洗得发白,电瓶车筐里塞着个磨起毛的棕色相机套,露着半只灰毛线织的兔子,不像坏人。可老街两旁全是酱菜缸冒香气、老相机铺擦镜头的,哪有这种奇怪交易?我摆摆手说不玩,她却往前凑了凑,车把晃了晃,车座上的竹编筐子掉出个玻璃弹珠:“不是你想的那样,是陪我孙子玩,就在惠民桥洞底下。” 我心里犯嘀咕,腿脚却不听使唤跟着走——主要是好奇,也怕这老太太真遇上啥难事儿。桥洞底下铺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絮,一个戴厚眼镜的小男孩坐在小折叠椅上,手里攥着个掉漆的海鸥相机,镜头盖还扣着,眼睛盯着我,却有点发直。 “孙子眼不好,医生说再过俩月可能就看不清了,就想拍遍老街的铺子。”她抹了下眼角的皱纹,“50块陪他拍一个小时,100块还能帮他把胶卷送巷口老陈的相机铺洗出来。以前都是我陪,可我这腿上周扭了,走不动路。” 我摸出100块递过去,小男孩立刻笑了,厚眼镜片后眼睛亮得像星星,把相机塞我手里:“拍酱菜铺的大缸,缸上有裂纹,像爷爷的手。”我举着相机陪他走,拍酱菜铺王阿婆用木勺翻缸,拍老陈擦相机镜头的专注样子,拍老街墙上掉漆的“为人民服务”标语。他每拍一张就脆生生报数,手有点抖,我就帮他扶着相机柄。 两个小时后我把相机还给老太太,她塞给我一包刚称的酱萝卜:“洗出来的照片,下周来拿。”我摆摆手走了,阳光落在青石板上,酱菜的香气飘过来,暖乎乎的。 下周我再去老街,桥洞底下空了,老陈说老太太带孙子去北京看病了,临走前把洗好的照片塞给了他,其中一张是我低头帮小男孩调相机的样子,背面用铅笔写着:谢谢叔叔陪我看老街。
上午我在县城老街河西边散步,一位坐电瓶车上的“老妇女”向我招手,问我玩不玩,
好小鱼
2026-01-22 21:55:16
1
阅读: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