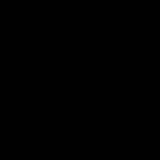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彼时汤飞凡已随中央防疫处辗转到昆明郊外,原本深耕沙眼病原研究的他,早已因战事中断研究,投身前线救护。 淞沪会战中,他就在离火线几百米的救护站连续奋战二十多天,炮火一次次逼近,他始终坚守岗位,亲眼见惯了伤员因感染溃烂、高烧不退的绝望。 西方的技术封锁加上滇缅公路被炸断,走私而来的青霉素在黑市上价格高得惊人,普通军民根本无力承担,卫生兵们只能用盐水煮纱布、撒木灰处理伤口,勉强维持却收效甚微。 向李约瑟表明决心后,汤飞凡立刻着手筹备研究,可摆在面前的是近乎空白的条件。 没有现成的菌种,他就发动团队全员四处“寻霉”,从发霉的食物、衣物到废弃物品,一点点筛选可用的青霉菌株,最后竟在一只旧皮鞋上找到了合适的菌株。 没有精密仪器,他就带着大家动手自制,发酵罐、提纯设备全靠土法拼凑,实验室不过是简陋的平房,通风差、温度难控制,只能靠人工反复监测调整。 战时物资匮乏,研究原料更是难寻,汤飞凡和团队四处筹措,把能找到的葡萄糖、玉米浆都集中起来,后来原料告急,就尝试用本地易得的原料替代,一点点摸索适配的发酵条件。 昆明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为了保持发酵所需的稳定温度,大家轮流守在实验室,夜里裹着厚棉衣蹲在设备旁,时不时添柴升温,不敢有丝毫松懈。 提纯环节更是棘手,青霉素浓度极低,杂质难以去除,他们反复试验不同的提纯方法,熬了无数个通宵,只为提高药效、降低毒性。 研究过程中,意外和困难接踵而至,菌株培养常常因环境问题失败,好不容易得到的发酵液纯度不够,多次试验后药效仍不稳定。 汤飞凡从不气馁,把每一次失败都记录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破局的执着。 他不仅自己扎根实验室,还联合樊庆笙、朱既明等科研人员协同攻坚,众人分工合作,有人负责菌株优化,有人钻研提纯技术,在简陋的条件下搭建起完整的研究链条。 1944年,经过无数次调试改良,中国首批青霉素终于在昆明问世,虽然是粗制产品,药效却十分显著。 有一次滇西远征军一名排长被弹片所伤,伤口感染高烧濒死,前线医院紧急求援,汤飞凡带着刚试制的青霉素连夜翻山越岭赶往战地,及时救下了这名排长。 消息传开,战士们都把这种药称作汤老板的长生酒,这简单的称呼里,满是绝境逢生的感激。 汤飞凡没有独占技术,反而把配方和土法操作流程整理成手册,用蜡纸油印后分发给西南、西北各防疫处,无论谁来要都慷慨提供,分文不取,他深知战时救命要紧,多一处能生产,就能多救一批人。 到抗战后期,他们已能批量生产青霉素,虽产量有限,却为前线救护、后方防疫提供了重要支撑,挽救了无数军民的生命。 后来中央防疫处迁回南京,汤飞凡把培育成功的菌株小心翼翼保藏在零下70℃的干冰罐里,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一挂就是十年,只为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份研究基础上,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成功试制出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随后实现工业化生产,彻底结束了依赖进口的历史。 汤飞凡的坚持,不仅是冲破技术封锁的科学壮举,更藏着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 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以实验室为战场,用专业能力对抗困境,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烽火中的中国撑起了一道生命防线。 那些土法炮制的设备、反复试验的痕迹,都见证着绝境中不屈的科学精神,这份跨越时空的坚守,始终值得铭记。 参考资料: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第一支抗生素:青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