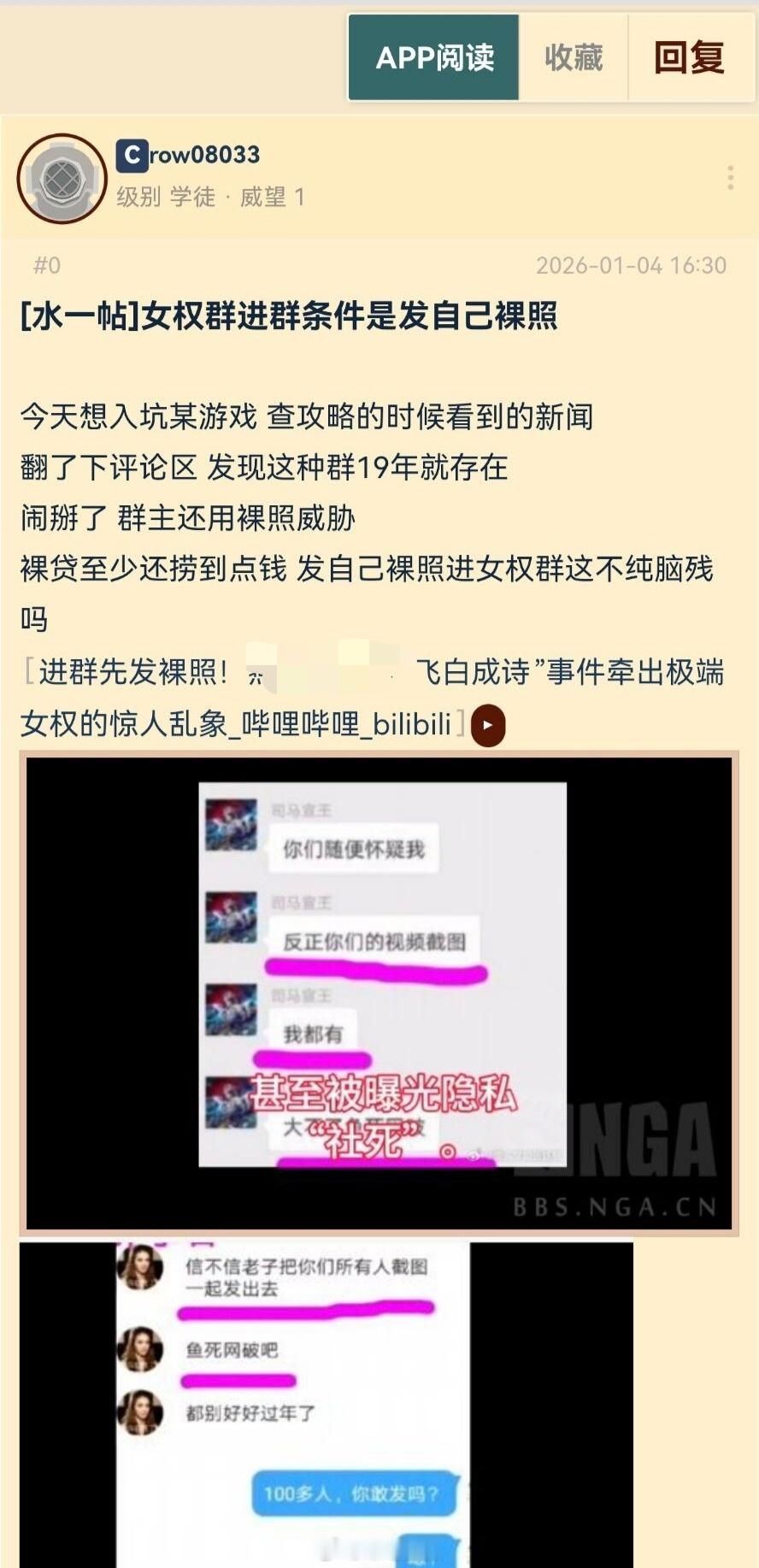我的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姑娘,我是老大。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外面偷偷找了个小三,还生了个弟弟,此后父亲竟公然不回家,工资也不给我母亲,我们母女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为生,那种艰苦的岁月就无法描述了。 母亲在纺织厂当挡车工,三班倒的活计熬得她眼窝子总陷着,可她下班后总往家背回个沉甸甸的布袋子。起初我们以为是厂里发的边角料,打开才发现是些碎布头、旧棉线,还有台缺了个脚的旧缝纫机——是她从废品站淘来的,机身锈得厉害,踏板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像只哮喘的老猫。 “娘要学做衣裳。”她把碎布头摊在炕上,用粉饼在布上画样,“厂里李姐说,会做衣服能接私活,一件小孩袄子能挣五毛呢。”可她白天盯机器盯得眼睛发花,晚上穿针引线时,线头在针眼外绕三圈都进不去,急得额头冒汗,就把线头放嘴里抿抿,再眯着眼凑到油灯下——那时候我们家舍不得用电灯,就靠盏煤油灯照亮,灯芯爆出的火星子,映着她手上的老茧一闪一闪。 我们姐妹四个也跟着忙活。我负责把碎布头按颜色分类,二妹学着剪样子,三妹和小妹蹲在地上捡掉在缝里的棉线。有回母亲接了个急活,给邻村张屠户家的胖小子做周岁棉袄,要绣只喜鹊登梅。她熬了两个通宵,右手食指被针扎得全是小红点,血珠渗出来,她就往嘴里吮吮接着绣。可临交货前,小妹贪玩碰翻了浆糊碗,棉袄前襟沾了片黑渍,母亲看着那片渍子,眼圈一下子红了,却没骂小妹,只是把棉袄泡在大盆里搓,搓到后半夜,手冻得像红萝卜,终于把渍子搓淡了些,又在旁边补绣了朵小梅花盖住。 那时候谁能想到,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光能捻出细密的棉纱,还能绣出比朝霞还艳的花呢?张屠户来取棉袄时,摸着那只扑棱棱像要飞起来的喜鹊,非要多给两毛钱,说:“大妹子,你这手艺,赶得上城里裁缝铺了!”母亲攥着那两块七毛钱,手都在抖,当晚就去供销社给我们买了半斤水果糖——那是我们头回吃带糖纸的糖,甜得舌头都要化了。 后来母亲的活越来越多,她把缝纫机修得锃亮,踏板踩得又快又稳,嗒嗒嗒的声音成了我们家夜里的钟。她教我们认针脚、辨布料,说:“女人手里有门手艺,就像走路带着拐棍,再滑的坡也能走稳当。”我们姐妹四个出嫁时,嫁衣都是母亲亲手做的,红缎面上绣着牡丹,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连婆婆们都夸:“看这手艺,就知道闺女是在疼惜里长大的。” 如今母亲八十多了,眼睛花得穿不上针,却总爱坐在缝纫机旁,看我们姐妹四个围在一起做活——我给孙女缝口水巾,二妹给孙子绣书包,三妹和小妹比着做虎头鞋。母亲就笑眯眯地说:“你们看,当年那些碎布头,现在都变成金疙瘩了。”阳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也落在我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布料上,暖烘烘的,像极了那年她第一次给我们分糖时,糖纸在油灯下闪的光。
王石离婚,5亿家产要被分走一半?这可不是电视剧。王石个人资产估计在5亿到10
【33评论】【2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