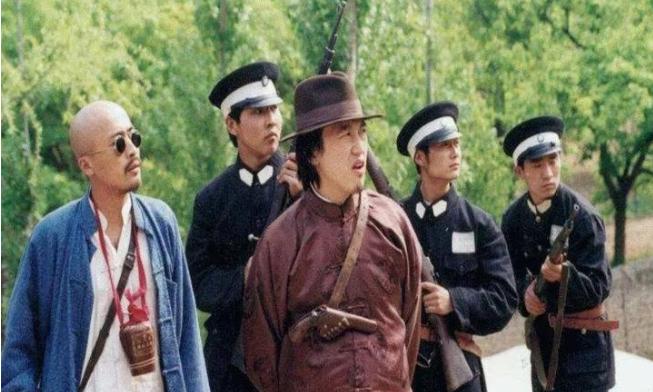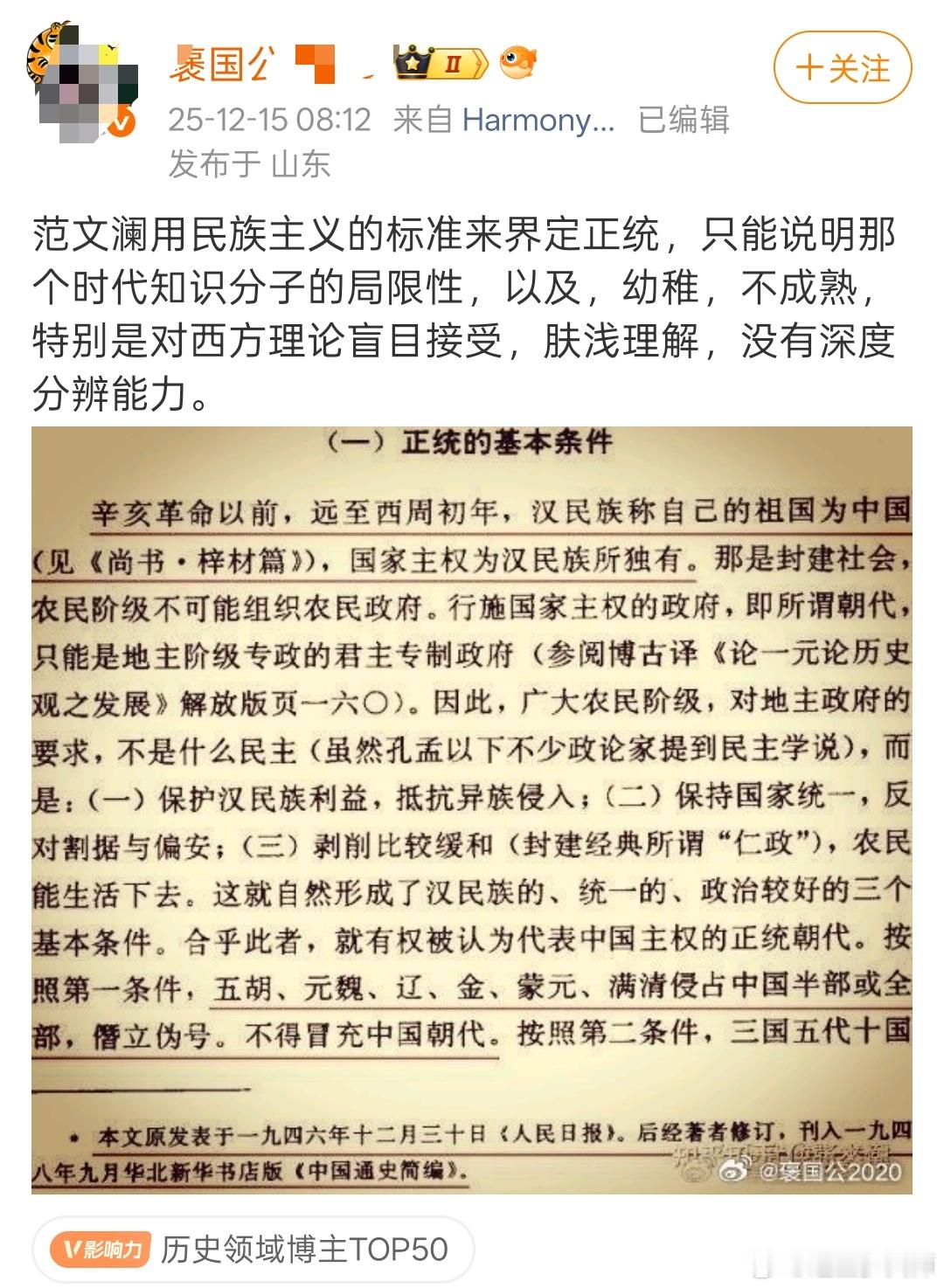[微风]1913年3月20日晚10:40,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身中三枪生命垂危。在医院他对于右任说:我身体很痛,估计是活不成了。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都有大量的存书,委托老兄把它捐给南京图书馆。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贫无钱,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黄兴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为我照料。 早年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时,宋教仁就养成了两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一是在生活上极为苛刻,但裤兜里总装着银角子,路边见到饿肚子的湖南老乡,就悄悄往人家袖口里塞;二是对书籍有着近乎洁癖的爱惜,看书前必先洗手,遇到书角卷起都要亲自修补,甚至为了买书不惜饿饭省下官费。 即便后来做了民国的农林总长,他在北京的日子过得比“庙里的菩萨”还干净,曾有记载,他为了推行农林政务,公务宴请的茶水费全是从自己干瘪的腰包里掏。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离职之时,这位前任总长没带走大洋金条,随身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两千多册书,袁世凯曾为了拉拢他,让人送去一张五十万银票的支票,被他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对于宋教仁来说,能让他兴奋的不是银子,而是那个关于“三角凳”的政治设想:总统的位置,必须要靠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条腿撑着才稳当,否则就要摔跟头。 恰恰是这种“穷酸书生”的固执,让他成了旧官僚眼中最可怕的对手。 宋教仁的“可怕”,不在于兵强马壮,而在于他那个装满了宪政思想的脑袋太好使了,他在日本期间主编杂志偷运回国,为了反驳日本对吉林延边的领土窥伺,他不是去喊口号,而是徒步踏遍东北边境,绘制了上万张地形草图。 甚至搞到了朝鲜王室的文书作为铁证,写出一本《间岛问题》,硬生生帮清政府保住了一块疆土,连老袁本人当年都不得不捏着鼻子夸他一声“国士无双”。 等到民国初建,他又把自己关了三天三夜,搞出了《鄂州约法》,到了1912年冬天,由于宋教仁带着国民党人在各地发疯一般地演讲,连直隶总督府的厨子都在偷偷传阅他的传单。 选举开票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傻了眼:国民党在国会狂揽392个席位,这哪里是选举,简直是把袁世凯权力的地板给抽了。 这种通过纸笔和演讲掀起的政治风暴,最终引来了3月20日晚上海北站的那三声枪响。 刺杀案的侦破过程,就像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闹剧,行凶者武士英,一个拿了1000块大洋就敢杀人的退伍兵,因为巡警在一个古董商人那里找到了他丢弃的枪套,瞬间让整个阴谋曝光。 线索一路从帮会头子应桂馨烧到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甚至在总统府的密电本里留下了“毁宋酬勋”这样触目惊心的四个字。 然而,这起被后世称为“民国第一悬案”的谋杀,后续走向却令人心寒,凶手武士英刚进看守所就吃了莫名其妙的毒馒头暴毙;中间人应桂馨以为立了功去讨赏,结果在火车包厢里被人割了喉;那位自作聪明的秘书洪述祖倒是躲进了青岛德租界,却在四年后被宋教仁年仅15岁的儿子一眼认出,揪住辫子扭送回国。 1919年,北洋政府特地从英国运来绞刑架处决洪述祖,似乎想用这种方式洗刷当年的嫌疑。 但这真的只是一场个人的邀功吗?当时《申报》连续三天的整版报道,已经让社会舆论沸腾,虽然北京方面通电要“追凶务尽”,可档案里那些消失的密电副本,却始终像车站煤油灯下被拉长的黑影,怎么也照不透。 宋教仁倒下的那个夜晚,原本是准备去北京推动他的农业贷款制度和地方自治法草案的,在他的蓝图里,土地的收益要归农民,地方要有财政权,孩子要有书读,可这一切都在枪响时刻终止了。 在那场震动全国的葬礼上,成千上万的长沙学生举着白幡,队伍中有一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那是宋教仁的寡母。 老人家怀里没有任何值钱的遗物,只有一沓儿子当年接济同学留下的借据,她唯一的依靠走了,留下的除了一屁股为了革命欠下的债,就只有那些没寄出去的家信。 许多年后,当1924年的一批宪法起草委员经过湖南桃源时,特意在宋家老宅前种下了三十一棵松柏,那是为了纪念宋教仁永远停留在三十一岁的生命。 直到七十年代,有日本学者去湖南考察,在一本破旧的《法学通论》里发现了一行手迹:“宪法如舟,民权为水,水涨则舟高。” 这段话没有被写进任何一部官方发布的约法文件里,但此刻读来,它比那些印在精装本里的条文更像是一种预言。 宋教仁这一辈子,虽然没能亲眼看到他梦寐以求的“法治大厦”真正建成,但他却像个孤独的守门人,自己变成了那块最硬的石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的人相信枪杆子,有的人相信金钱,只有他到死都相信那些薄薄的书和规则的力量,他以为他把书捐给了图书馆,其实他是把关于文明政治的火种永远留给了后人。 主要信源:(百年悬案——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