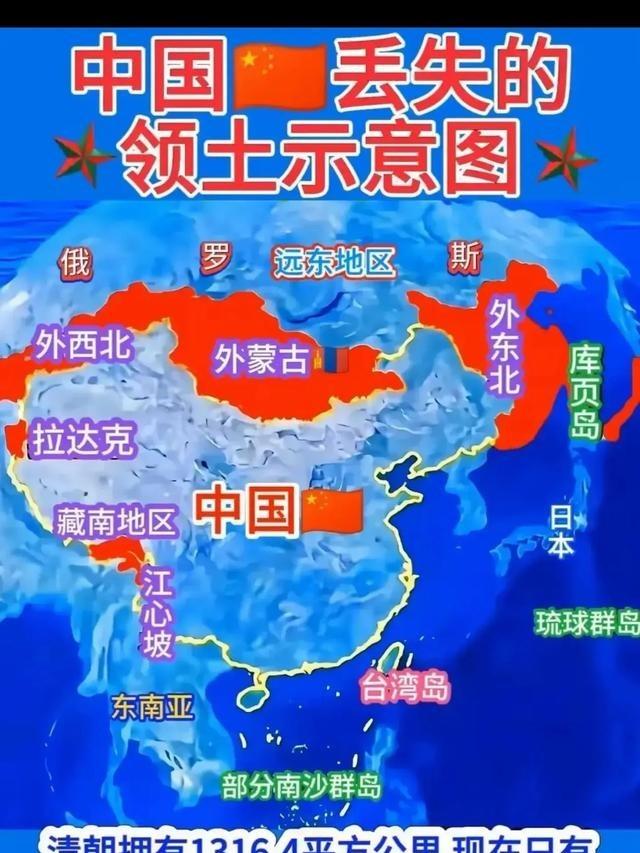谭嗣同就义那年,父亲谭继洵已经七十二岁。 这位前湖北巡抚,亲自北上为儿子收尸。千里颠簸,扶柩南归,把“朝廷钦犯”接回浏阳老家安葬。棺木落地时,他提笔写下那副名联: “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字字都是父亲的煎熬。他理解儿子的选择吗?未必。他认同儿子的道路吗?不敢。但他用这副挽联告诉世人——我儿子不是罪人。 在当时,这是掉脑袋的举动。一个旧式官僚,用最传统的方式守护了最离经叛道的儿子。 谭继洵七十有二,早已不是叱咤官场的巡抚。 他辞官归乡不过两年,一辈子浸淫晚清官场,信奉儒家礼法,忠君守制,是根正苗红的旧式官僚,一辈子没做过半分出格事。 他为官四十余年,从知县做到湖北巡抚。 清廉自持,不结党不营私,治理一方百姓安稳,却也固守祖制,对洋务、变法始终保持距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他的为官信条。 这样的父亲,偏偏养出谭嗣同这般逆子。 谭嗣同自幼聪慧,却厌弃八股科举,偏爱经世致用之学,成年后游历大江南北,见山河破碎、百姓疾苦,一心要变法图强,性子烈得撞南墙不回头。 父子俩的矛盾,从来都在政见上。 谭继洵不止一次苦劝谭嗣同,朝堂暗流涌动,慈禧掌权、光绪势弱,变法就是刀尖跳舞,轻则罢官,重则杀头,何苦拿身家性命赌。 谭嗣同每次都犟着脖子反驳。 说国将不国,何谈身家,若能以变法救亡,流血又何妨。父子俩每次谈及此事,最后都是谭继洵叹气摆手,谭嗣同愤然离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谭继洵不是不懂儿子的赤诚。 只是官场沉浮半生,他见多了兔死狗烹,太清楚维新派的渺小,太明白慈禧的狠辣,他怕,怕儿子一腔热血,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这份怕,终究还是成了真。 戊戌变法百日而终,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瀛台,维新派四散奔逃,康有为、梁启超连夜逃往海外,唯有谭嗣同,执意不走。 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话传到浏阳,谭继洵当场跌坐在椅上,老泪纵横,只念着“傻孩子”。 没几日,谭嗣同被捕,判了斩立决。 罪名是“大逆不道,图谋作乱”,成了朝廷钦定的钦犯,菜市口问斩后,尸身弃于闹市,朝廷严令,任何人不得收尸,违者同罪,株连九族。 消息传来,谭家上下人心惶惶。 族人纷纷跪地劝谭继洵,保全家族要紧,钦犯的尸身碰不得,七十三岁的老人,却缓缓站起身,沉声说,我是他爹,为子收尸,天经地义。 他不顾众人阻拦,收拾简单行囊就北上。 彼时他已是罢官之身,顶着钦犯之父的名头,沿途官吏避之不及,没人敢提供车马便利,千里路程,他坐骡车、走土路,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腿脚不便,一路走得摇摇晃晃。 旁人都骂他老糊涂,为了一个逆子,要搭上全家性命。 谭继洵充耳不闻,只顾赶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儿子为国赴死,不是作乱,绝不能让他曝尸荒野,做个无家可归的孤魂。 到了京城菜市口,已是数日后。 谭嗣同的尸身孤零零躺在石板上,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无人敢靠近半步。谭继洵拨开围观人群,走到儿子身边,颤抖着抚上儿子冰冷的脸,泪如雨下,却没哭出一声。 他雇人擦拭尸身、置办棺木,官府派人前来阻拦。 谭继洵挺直佝偻的腰板,直视官兵,一字一句道,我乃前湖北巡抚谭继洵,为亲儿收尸,法不外乎人情,要抓要杀,冲我来。 官兵忌惮他昔日的官威,也知他年事已高。 更怕此事闹大引非议,竟真的不敢硬拦,眼睁睁看着谭继洵,将谭嗣同的尸身敛入棺木,护着棺木,一步一步离开京城。 扶柩南归的路,走了三个多月。 七十二岁的谭继洵,全程守在棺木旁,白日里盯着车马,夜里就睡在棺木边,生怕路上出半点差错,委屈了儿子。一路颠簸,他的身子越发孱弱,却硬是撑着没倒下。 终于到了浏阳老家,棺木落地的那一刻。 谭继洵望着棺木,沉默良久,提笔写下那副千古名联。没有激昂的辩解,没有悲愤的控诉,只有字字千斤的煎熬,道尽了一个父亲的无奈与倔强。 “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 他知道,天下人都在骂儿子是乱臣贼子,朝廷骂他谋逆,儿子的清白,他这个父亲认就够了。 为了收尸、为了这副挽联,谭继洵付出了代价。 朝廷震怒,革去他所有官爵,下旨将他软禁在家,永不叙用,昔日同僚好友避之不及,族人也多有怨言,可他至死,都没说过一句后悔。 他七十五岁病逝于浏阳,临终前。 还让家人把那副挽联挂在床头,看了又看,最后只留下一句话:吾儿嗣同,无愧于心,无愧于民 谭嗣同是刚烈的,是决绝的。 他以死明志,成了戊戌六君子之一,青史留名,可他也是幸运的,有一个看似不理解他,却拼了命守护他身后名的父亲。 世人皆知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 却少有人懂谭继洵千里收尸的煎熬。一个为国赴死,一个为子赴险,政见相悖,亲情却入骨,这便是历史最动人的模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