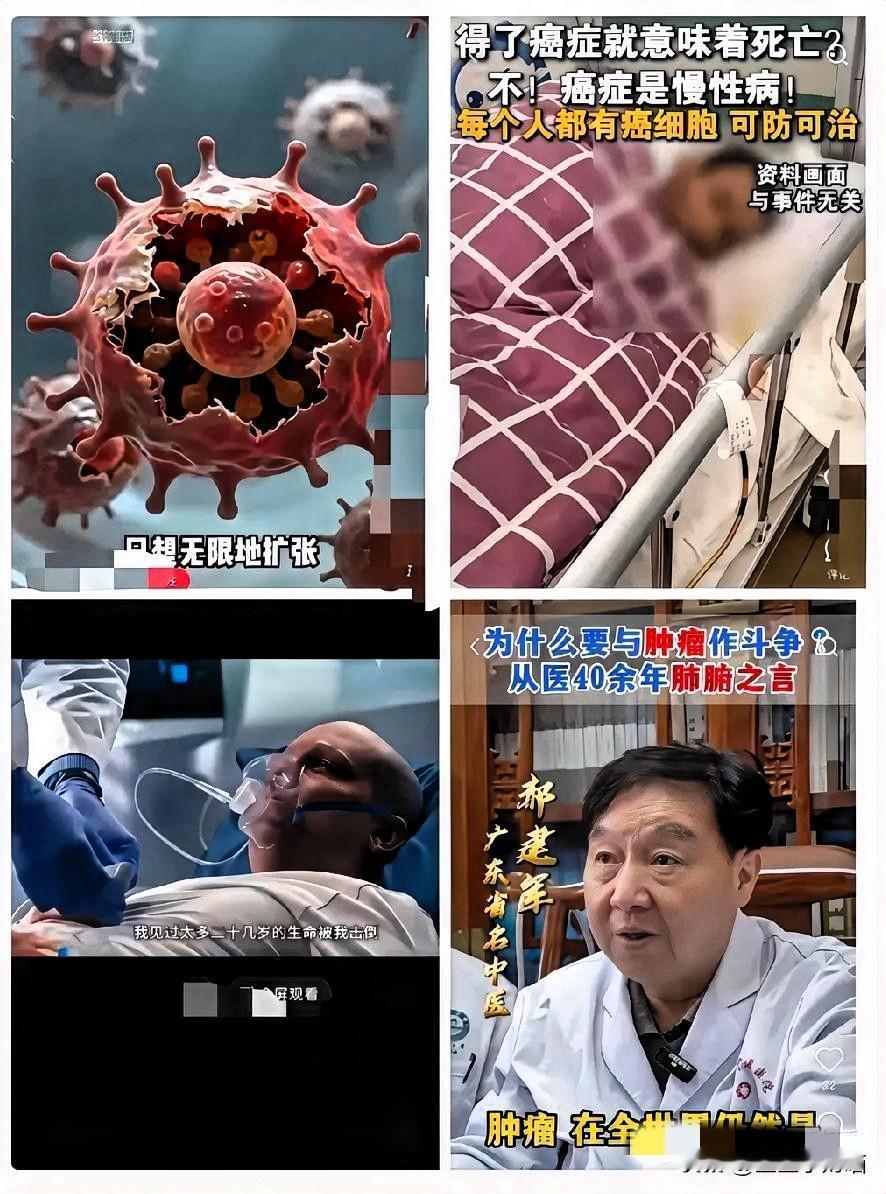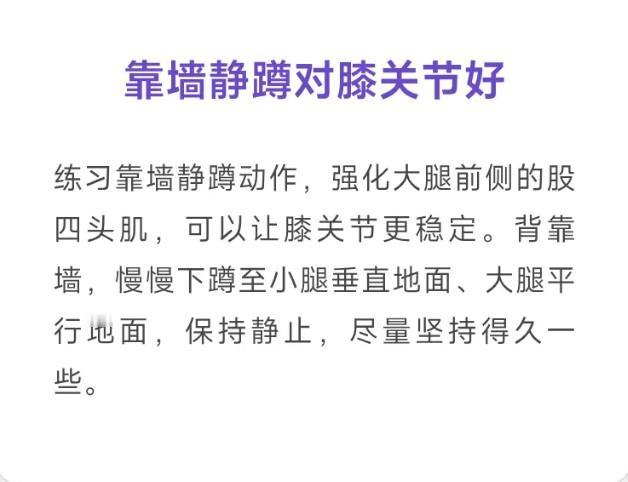拿掉滤镜。 天使的手掌纹路里,嵌的是防滑镁粉。 皮肤被氯水泡得发白起皱,指关节有老茧。 湛江农村那个下雨漏水的院子,突然装上了不锈钢大门。 这是全红婵的肉身。 福报? 太轻了。 世锦赛十米台,压水花那一下,现场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耳鸣。 她赛后咧嘴笑,牙套亮晶晶。 回村,给母校捐跳板。 有小孩怯生生摸她的金牌,冰凉。 她俯身说,不凉,是烫的。 这孩子不说励志废话。 她说,跳好了,家里就不愁。 她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耳光。 那些关于苦难与成功的廉价叙事,在她这儿哑火。 她训练量能精确到每天入水多少次,膝盖的积液抽过几回。 这是“自我”要的硬核数据。 而镇上的小卖部,现在把她的海报贴在“红双喜”香烟旁边——这是最生猛的中国式地标。 西方媒体分析她的转体力学。 他们不懂。 驱动她的不是公式,是几年前妈妈看病时,那张攥出汗的账单。 那是“本我”最原始的火山。 现在她给家乡修路,钱一笔一笔,像她跳水一样,砸下去就有回响。 所以别说她是天才。 天才是对规律最傲慢的侮辱。 她是一套精密运行的人间系统:用绝对的非人训练,达成绝对的人间愿望。 最后升华了? 不。 她让每个看着她的普通人,在某个憋屈的深夜,突然觉得自己那点难,好像也能在水花消散后,听见一声清脆的回响。 这就是我们共同要的,那一声“砰”。
72岁肿瘤专家患癌,抗癌一年病逝,他临终前的2个后悔,引以为戒张教授是国内著
【1评论】【10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