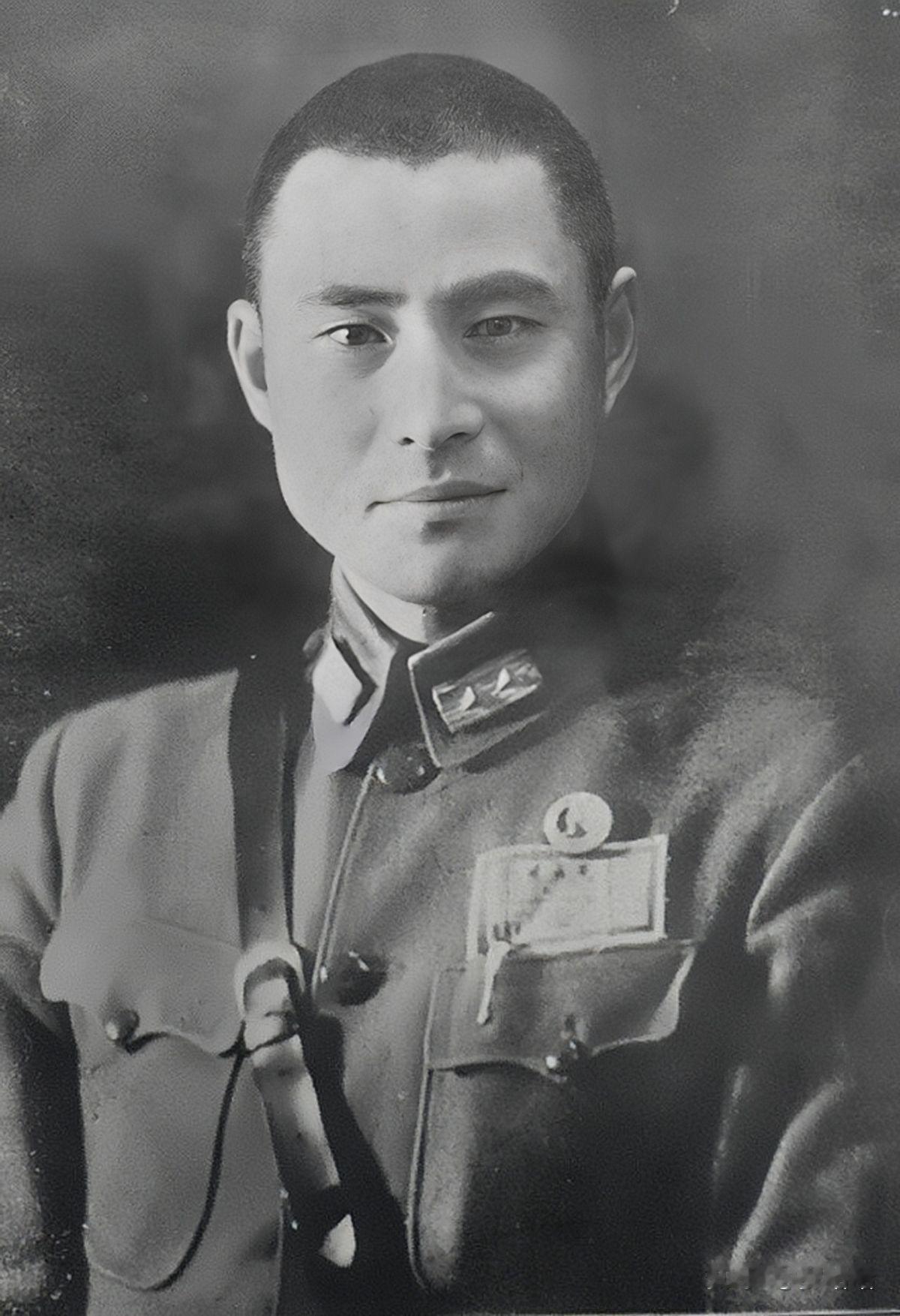[微风]1980年3月,邱岳峰吃了大量安眠药,被送往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虽然他是著名的配音艺术家,但没有政府机构或单位(上译厂)出面的追悼会。 1980年3月的上海龙华公墓,春寒料峭,在这个气氛凝重的大厅里,正上演着一场特殊的告别。这里没有官方发布的一纸讣告,也没有逝者生前单位出面的正式治丧委员会,但并不妨碍送别的人潮将灵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 工作人员准备的六百朵黄花瞬间告罄,紧急追加到九百多朵依然无法满足赶来的群众,那些甚至没有留下姓名的花圈层层叠叠,沉默地诉说着一位“无冕之王”在普通人心中的真正分量。 躺在这里的,正是被誉为“上译第一男声”的邱岳峰,对于当时来到现场的同仁苏秀而言,眼前的景象无需多言——观众络绎不绝的脚步,就是对这位配音艺术家最高的加冕。 虽然按照当时的行政定级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未能享受到与之匹配的官方追悼规格,但从好友韩非到普通影迷,所有人都明白,那个让银幕角色拥有灵魂的声音,彻底沉寂了。 邱岳峰的嗓音,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声”,早年间,他那略带沙哑的音质甚至一度被视为不够宽厚,很难成角儿。 然而,正如画家陈丹青后来的评价,在很多国人心中,邱岳峰的声音似乎比原版更具角色的神韵。 当他在美国重温《简·爱》或《凡尔杜先生》时,反而觉得原本的罗切斯特和卓别林“有点假”,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全是邱岳峰那种高贵、敏感又带着深沉悲剧色彩的声线。 这种艺术上的“点石成金”,源于一种近乎自虐的职业操守,自1950年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后踏入只有一栋旧洋楼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起,无论是作为第一代配音演员参与《团的儿子》,还是后来为四百多部中外影片献声,邱岳峰始终在黑暗中打磨着光芒。 他不仅能利用流利的俄语优势精准把握早期苏联影片的节奏,更为了对准一个口型、推敲一句台词的开合度,像苦行僧一般在暗房里反复度量。 连扫地、烧水这样琐碎的后勤杂务,他也能毫无怨言地日复一日坚持,正是这种在幽暗角落里的极致深耕,才孕育出了《大闹天宫》里肆意张扬的孙悟空,以及《尼罗河上的惨案》等无数经典译制片中那些有血肉、有呼吸的人物。 然而,银幕内的光鲜往往掩盖了银幕外的苍白与困窘,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邱岳峰一家七口人只能挤在十几平方米的逼仄斗室中,因为没钱买抗生素,大女儿在数月大时便不幸夭折,这成了这位父亲心中难以拔除的刺。 直到六十年代末,孩子还要长期睡在地板上,拿着二十年如一日未变的103元工资,他既要赡养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继母,又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像一张无形的网,将这位内向的艺术家紧紧勒住。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他留给长子邱必昌的,却是一句极具力量的教诲:“人生没有过不去的河,咬咬牙就能挺过去。” 这句话后来甚至成了儿子手机上的屏保,支撑着后辈度过人生的风雨,可令人唏嘘的是,说出这句话的人,最终没能渡过自己心中的那条湍流。 邱岳峰的内心其实远比外表看来得脆弱且丰富,历史问题的阴影迟迟不散,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被悄然替换,这些都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他的意志。 从六十年代起,他就深陷抑郁的泥沼,曾两次试图通过吞服安眠药来了结痛苦,幸而被抢救了回来,但他心中积压的委屈与那些无法排解的“罗切斯特式”的傲气,始终在寻找一个决堤的缺口。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80年不期而至,关于他和年轻女演员的流言在厂里散播开来,导致了家庭内部爆发激烈的争吵。 对于一个视尊严如命、性格内向敏感的人来说,这种羞辱感可能是致命的,在那个早春的三月,他再次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一次,尽管医院接到了“不惜代价抢救”的指令,但死神没有再给他回头的机会。 在《凡尔杜先生》中,邱岳峰曾配过这样一句台词:“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这似乎成了他一生的黑色谶语——他不仅是个杰出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好父亲、一个重感情的人,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他在一个粗粝的现实中保留了太多的柔软与浪漫,始终学不会对这个世界、对自己“无情”。 那场由演员组自发组织的追悼会上,每一朵无名的黄花,都是人们对他这段坎坷人生最温柔的痛惜。 信源:澎湃新闻《邱岳峰百年:他是中国配音事业的巅峰,也是难以弥合的伤口》 文汇报《他为什么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