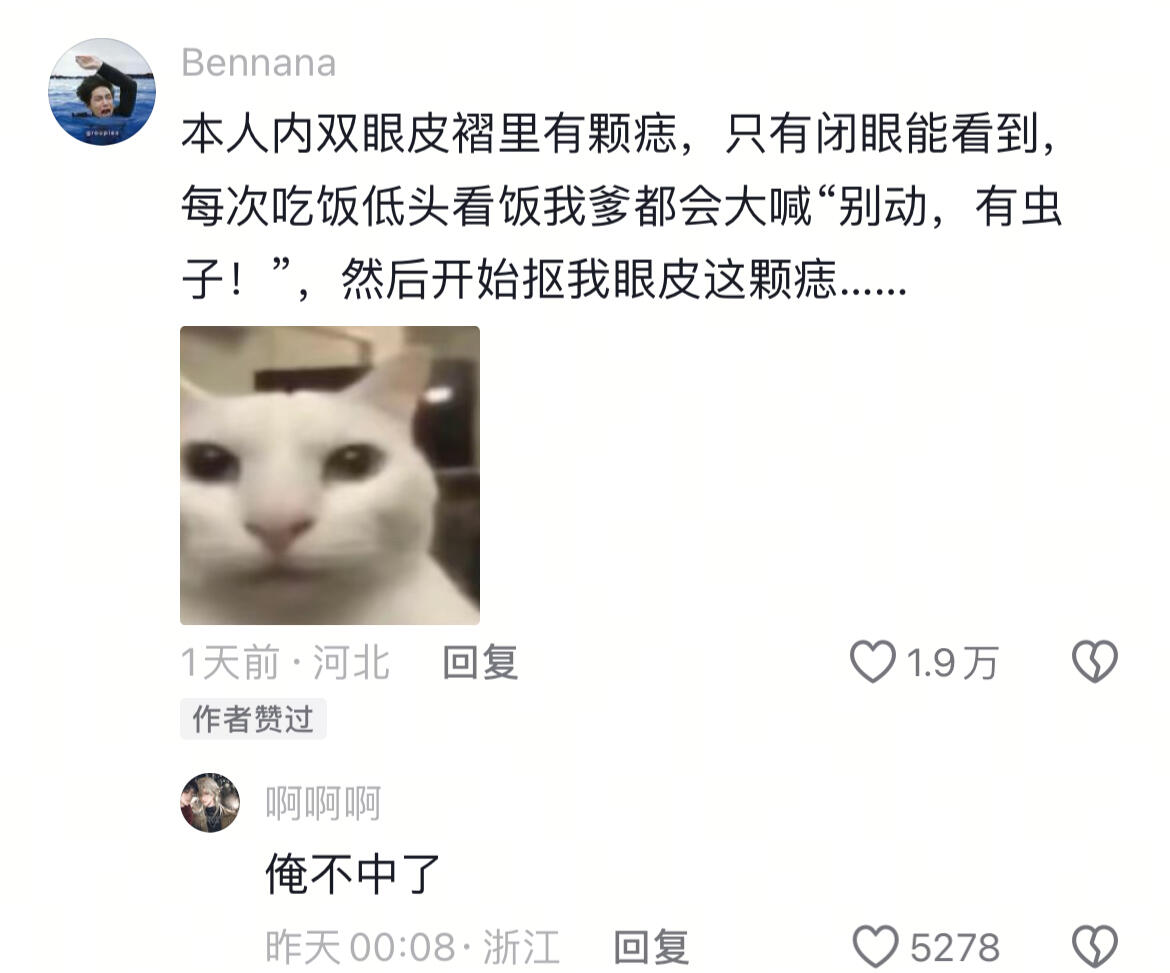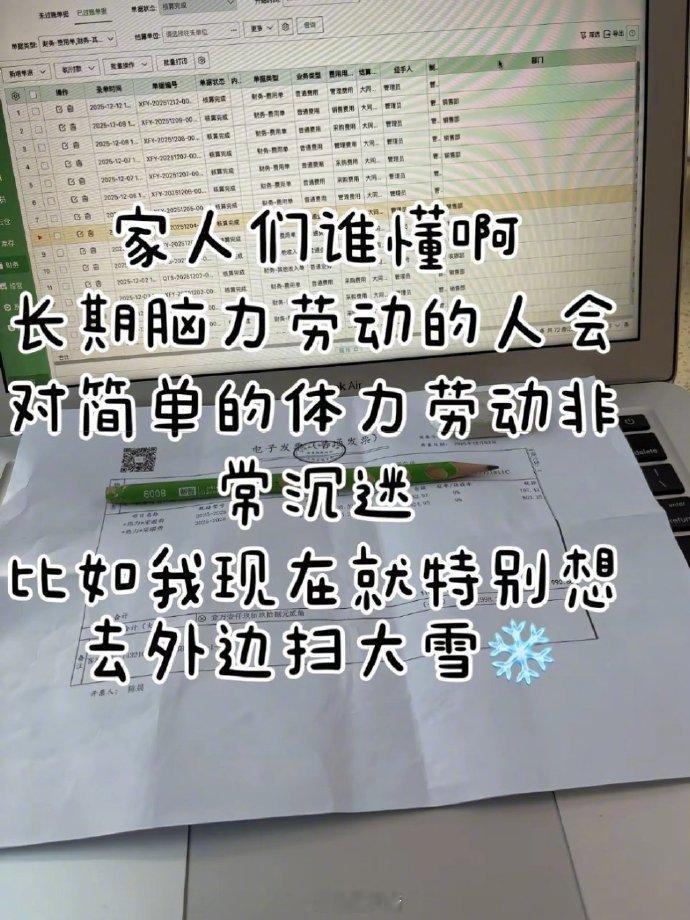李富贵上完厕所,刚进被窝,李冬芳就要他接着讲故事。 “那信是开春后收到的,”李富贵往被窝里缩了缩,声音裹着夜气发闷,“黄巧妹的字歪歪扭扭,说吃东西总吐,唯独馋酸菜,信纸上还沾着半片干枯的梧桐叶——那是她去后山摘酸菜时顺手夹进信封的。” 他没提自己信里都写了啥,只说黄巧妹娘很快托了媒人,门槛都快踏破了。 “她把第一个媒人送来的红糖扔在门槛上,糖块滚进泥里,黏了层黑灰。”李富贵的手指在被窝里蜷了蜷,像摸到了当年的糖渣,“她娘拿鸡毛掸子抽她后背,‘不嫁人,开春脱了棉袄,肚子藏哪儿去?’” 后来邻村来了个转业军人,穿四个兜的干部服,提着点心匣子站在她家院里。 “她没看那点心,盯着军人肩上的旧伤疤——跟李富贵胳膊上练单杠磨的疤有点像。”李富贵咽了口唾沫,“她说‘行’的时候,灶台上的酸菜坛子正咕嘟冒泡,像是在替她哭。” 寒假李富贵回老家,她特意从婆家溜回娘家,两人往村后的桐叶树山走。 雪刚化,山路泥乎乎的,她牵着他的手往自己隆起的肚子按:“宝宝,你爸爸回来了。”声音轻轻的,怕惊着肚子里的,也怕惊着树后躲着的风声。 “每次约会都要待一阵,”李富贵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总说‘轻点,别碰着孩子’,可那天风大,两人在山洞里待久了,她回来就发起高烧。” 盘尼西林打了七天,孩子没保住。 她躺在婆家炕上,盯着房梁上的蜘蛛结网,一句话不说。 李富贵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写信说要结婚了,信封里夹着两张电影票根。 “她没回信,”李富贵叹了口气,“后来听她娘家嫂子说,她把那信烧了,灰掺在喂猪的糠里。” 再后来,李富贵老婆走了,黄巧妹的丈夫也没了——听说她丈夫喝醉酒掉进水塘时,她正在给李富贵织毛衣,针掉在地上,断了两根。 “她娘让她来找我,”李富贵转头看窗外,月光把树影投在墙上,像幅模糊的画,“那夜她坐在炕沿,说‘是我命不好,不怪你’,可眼泪掉在炕席上,洇出一小片湿。” 有人说她是被爹娘逼的,可她后来总对李富贵念叨,“那时候你考大学比啥都重要”——像是在替自己,也替那个年代的身不由己找个理由。 那个年代村里姑娘未婚先孕,唾沫星子能淹死人;黄巧妹娘把晒谷场上的竹匾摔得震天响,“这脸我还要不要”;于是相亲对象的转业军人身份成了遮羞布,婚姻成了应急的补丁,可补丁下的伤口,在抗生素和眼泪里越烂越深。 如今两人住在老院里,她还是爱腌酸菜,坛子摆在窗台下,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里面泡着的红辣椒。 只是李富贵偶尔半夜醒来,会看见她对着空摇篮发呆——那摇篮是当年她亲手编的,竹篾都泛白了。 “冬芳,”李富贵的声音有点发颤,“你说,这故事里的人,是活得苦,还是……算有了个念想?” 被窝里的李冬芳没说话,只往他这边靠了靠,像是怕冷,也像是怕这故事里的叹息,从过去飘到现在。
这个故事还是有点儿邪门
【1评论】【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