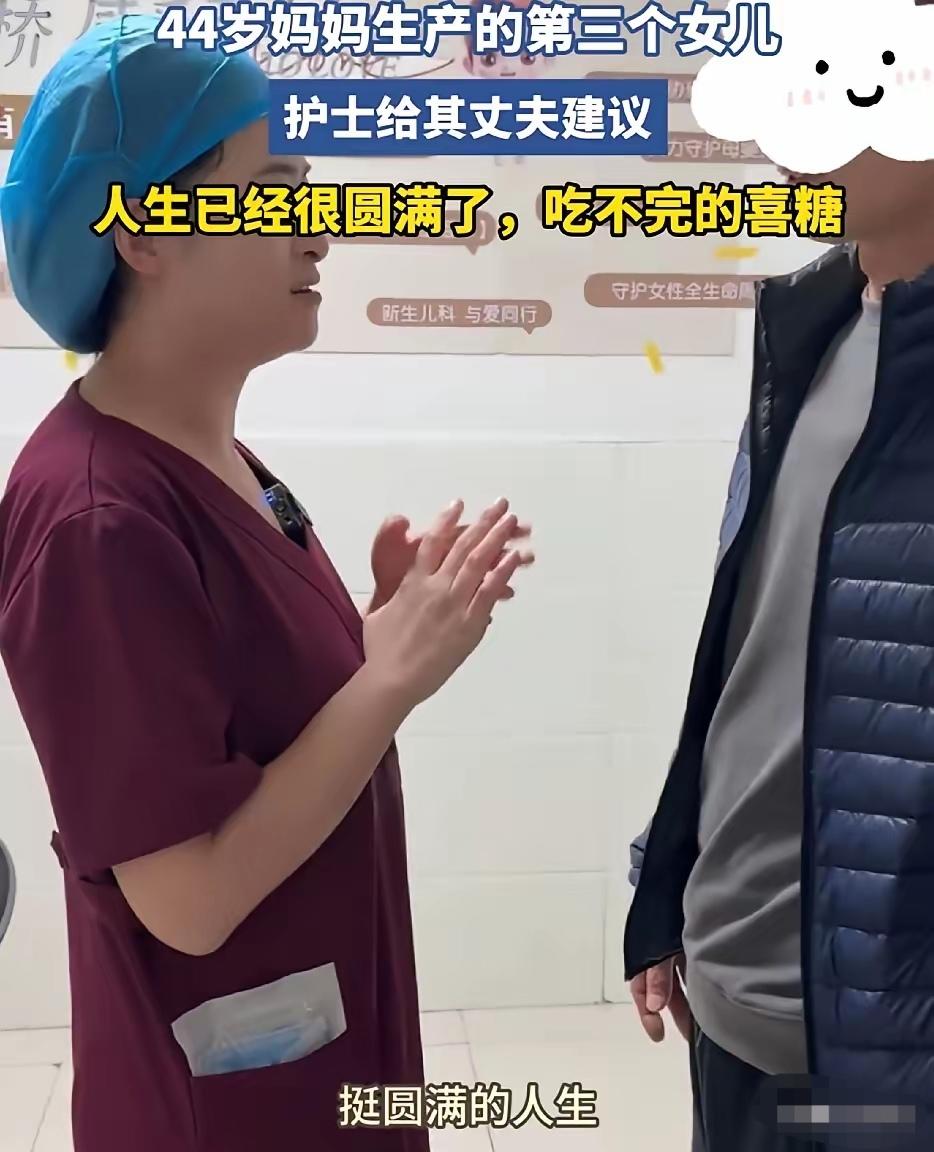逃荒路上我双腿致残,夜里爹娘带哥哥离去,我装睡目送他们走远 我的腿,就是在那个冬天废掉的。 其实不是突然的。逃荒的路走了三个月,从深秋走到隆冬。河北老家的黄土路,变成了河南地界坑洼的官道,又变成了不知名的、被无数双脚踩得稀烂的泥泞小径。一开始只是脚底磨出水泡,水泡破了,粘着粗陋的草鞋,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炭火上。后来天冷了,雪落下来,单薄的裤腿裹不住寒气,膝盖以下先是针扎似的疼,然后慢慢麻木,肿得像两根发面馒头,皮肤紫红透亮,有些地方破了,流出黄水,结成冰碴子。 爹试过背我。他宽阔的脊背像一堵温暖但摇晃的墙。可背不了太久。他自己也饿,一天只喝得上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掺着不知名的树皮草根。娘和哥哥沈禾,深一脚浅一脚跟在旁边,脸被北风吹得皲裂,眼睛里没了光,只剩下求生的本能。 我知道,我成了拖累。 那晚宿在一个破败的土地庙里。神像早就没了,只剩半个土台。四处漏风,雪粒子从破瓦的缝隙里钻进来,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庙里挤满了逃荒的人,呻吟声、咳嗽声、孩子的啼哭声混在一起,又被无边的寒冷压得很低,像垂死的叹息。 娘把我搂在怀里,用她仅存的一点体温暖着我冰冷的腿。爹和哥哥挤在旁边,一家人团在角落。爹从怀里掏出半块硬得像石头的杂面饼,掰成四份,最小最软的那块塞进我手里。我没吃,偷偷塞回娘的手心。娘的手颤抖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把我搂得更紧。 后半夜的寒风格外刺骨,我被冻得牙齿打颤,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爹娘以为我睡熟了,凑在土台边低声说话,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却每一个字都钻到我耳朵里。爹说“带不动了,再拖下去,四个都得死在这雪地里”,娘的声音带着哭腔,反复念叨“那是我的闺女啊”,哥哥沈禾年纪小,只小声问“妹妹不走,以后还能再见吗”。我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借着透进来的雪光,看清了爹攥着包袱的手背上暴起的青筋,那包袱里裹着他和娘仅有的几件破衣裳,还有早上没吃完的那点饼渣。娘的手指在我脸上轻轻滑过,动作里带着不舍,却又在触到我肿得发亮的腿时,猛地缩回了手。我知道,她是怕摸到那冰凉的、没有一丝温度的皮肤,就狠不下心走了。爹最后咬了咬牙,弯腰背起包袱,又伸手牵住哥哥的手。哥哥被爹拽着,一步一回头,眼睛里满是迷茫。娘站在原地,看了我好久,最后还是狠下心,转身跟着爹的脚步往外走。他们的脚步声很轻,怕惊醒我,却不知道我早就醒着,把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刻在了心里。雪粒子打在他们的破棉袄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直到彻底消失在土地庙外的风雪里。我躺在冰冷的草堆上,腿上的疼已经麻木了,可心里的疼却像刀子割一样,一下比一下厉害。我不敢哭,怕我的哭声会让他们回头,怕他们回头了,我们一家人就真的都活不成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冬天的河南,不止我们一家这样。1942年的饥荒连着战乱,地里的庄稼全被冻坏了,官府的救济粮被层层克扣,到了百姓手里,连一粒米都没有。无数逃荒的人拖家带口往陕西走,路上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很多家庭为了让家里的男丁活下来,不得不放弃女儿或者病弱的孩子。爹娘不是狠心,他们只是在生存和骨肉之间,做了最残忍的选择。哥哥是沈家的根,我是个腿废了的闺女,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这样的选择几乎是必然的。我攥着娘偷偷留在我身边的那小块杂面饼,感受着那点残存的温度,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哪怕是拖着两条废腿,也要看看天亮后的样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