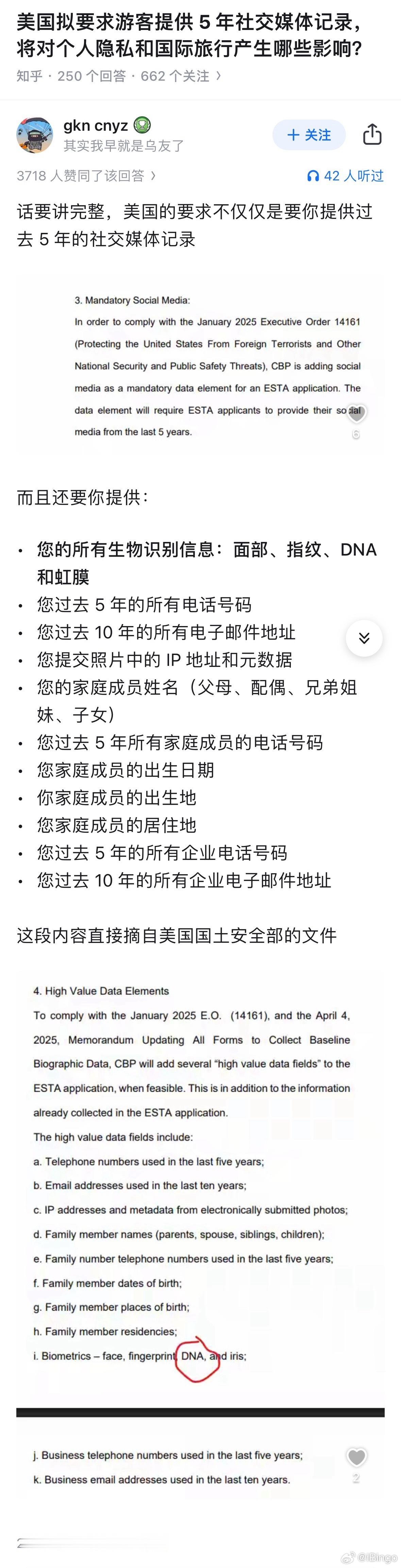这雨是半夜里来的。先是几滴试探地敲在窗上,疏疏的,像远客迟疑的叩门声。后来便放开了,哗哗的,把夜煮成了一壶沸水。我醒在床上,听那雨脚密密地踏过屋瓦,觉得这老房子都在雨声里微微地颤着。忽然记起后园那丛芭蕉——这时候,怕是被雨打得抬不起头来了罢? 天色是蟹壳青的时分,雨小些了,成了牛毛似的雾丝。我趿着鞋往后园去。石径湿得发黑,缝隙里的青苔饱饱地吸了水,绿得要从石头上淌下来似的。转过那堵爬满何首乌的矮墙,便看见了——那丛芭蕉果然还在老地方,只是模样全变了。 昨夜之前,它们还是骄傲地张着阔大的叶子,绿汪汪的,像要滴下油来。现在呢,高处的叶子都垂着了,叶心窝着一泓一泓的雨水,沉甸甸地往下坠。那绿也不同了,不是先前那种轻浮的鲜绿,是透透的、深深的墨绿,绿得有些苍老了。最大的那片叶子,不知何时裂开了一道长缝,从叶柄直撕到叶尖,像谁用无形的剪刀裁过。雨水顺着裂缝淌成一条晶亮的线,断断续续的,是芭蕉的泪么? 我立在檐下看。风来时,整丛芭蕉便懒懒地动,阔叶子相互摩挲着,沙沙的,夹着水珠滚落的嘀嗒声。那声音是钝的,闷的,不像打在屋瓦上那般清脆,倒像是谁在远处缓缓地捣着布帛。一滴蓄久了的雨水从最高的叶尖坠下,“啪”地打在低叶上,那叶子便猛地一沉,弹起时,溅开无数细碎的水星子,在晨光里亮了一亮,又熄了。 忽然想起《红楼梦》里宝玉的句子:“……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蕉叶上流不断的,不也是悠悠的愁么?只是这愁是植物的愁,没有缘由,也不求解脱,只是那么绵绵地、沉沉地坠着,把绿意坠得更深了。 不知站了多久,雨竟完全住了。云隙里透下一柱日光,正落在蕉叶的水洼里,亮得晃眼。一只麻雀飞来,偏着头瞅瞅叶子,又跳上叶柄,震得水珠乱跳。它啄啄这里,啄啄那里,忽然“叽”地一声,像是发现了什么无趣的东西,振翅去了。园子静下来,静得能听见积水从叶缘滴落的节奏——嘀,嗒,嘀嗒,渐渐慢下去,慢成一种就要停住的、让人屏息的等待。 转身要回屋时,听见身后轻轻一声“啪”。回头看去,是那片裂叶终于承不住水,彻底垂下来了,叶尖抵着泥土,弯成一个恭敬的弧度。别的叶子却渐渐舒展开了,在微风里缓缓地摇,摇出一片湿漉漉的光。昨夜那场急雨留下的痕迹,正从叶面上悄悄褪去,留下些亮晶晶的水路,像是不曾说尽的话。 我忽然觉得,这芭蕉的愁原不是真的愁——它只是静静地受着,雨来便承着,雨去便展着。那垂下的姿态不是颓唐,倒像是一种谦卑的、全然的接受。而我们这些看客,偏要替它生出许多感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