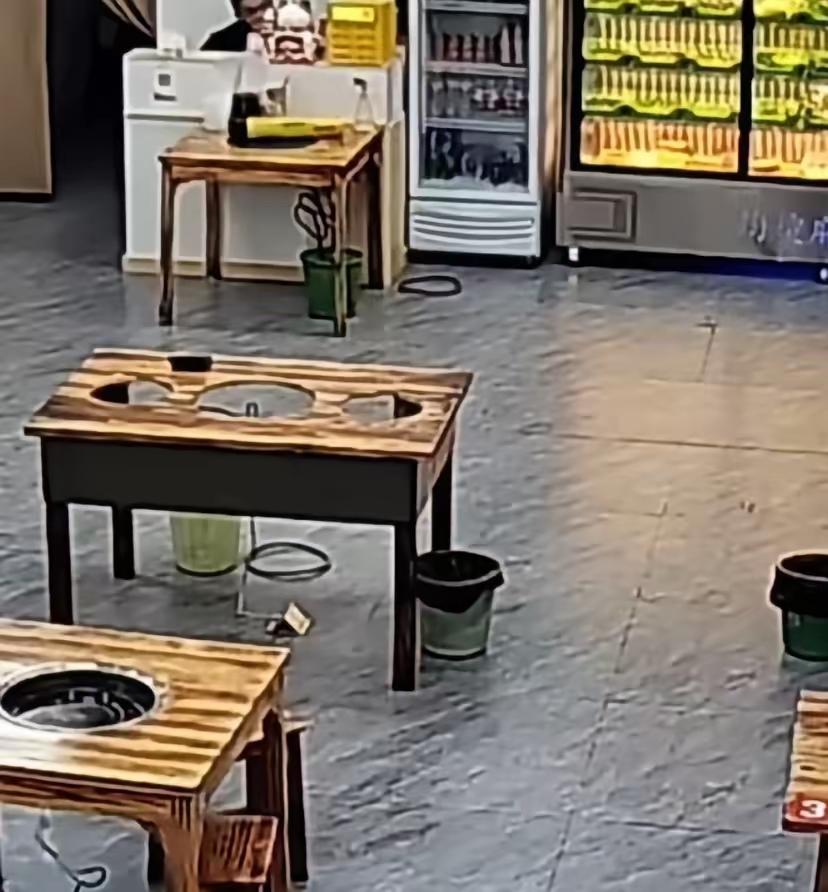老家有个男的以前家暴他老婆,她婆婆也添油加醋嫌她生了个女儿。后来有一次在大棚里干农活,男的又打她,她拿起地上的铁锹,把男的拍倒,叉断了他四根肋骨。因为我们两家的大棚离得不远,我爸妈听见声音过去拦着,她才没弄死那男人。 我们村东头那户人家,男人以前总打老婆。 不是偶尔吵急了动手,是隔三差五的,喝醉了打,没喝醉嫌她干活慢也打。 婆婆更绝,见天儿在门口指桑骂槐,说她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带把的,占着茅坑不下蛋。 女人话少,见人总低着头笑,旧外套袖口磨出毛边,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泥——那是常年在大棚里伺候菜苗留下的印子。 她女儿刚上小学,梳着歪歪扭扭的小辫子,总躲在她身后,眼睛像受惊的小鹿,见了男人就往妈妈怀里钻。 那天午后的大棚里,塑料膜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闷得像口密不透风的缸,她正弯腰给黄瓜搭架,男人扛着锄头从棚外进来,一脚踢翻了她脚边的水桶,水混着泥溅了她一裤腿。 “瞎了眼?”他骂着,扬手就朝她后脑勺扇过来。 以前这种时候,她会缩脖子躲,或者死死抱住头,等那阵疼过去。 但那天她没躲。 她退了半步,后腰抵上了立在埂边的铁锹,木柄被太阳晒得发烫,烫得她手心发颤。 男人的巴掌没落下,他被她眼里的东西吓了一跳——那不是以前的怯,是一种空,空得像被水泡烂的土坯,一碰就碎。 然后她就拿起了铁锹。 不是抡圆了砸,是平着推过去,像在铲地里的石头,“砰”一声,正拍在男人胸口。 他“哎哟”一声倒在泥里,还没爬起来,她又跨过去,铁锹头朝下,用那排尖尖的叉齿,死死压住了他的肋骨。 “别打我了。”她开口,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求你了,别打我了。” 我爸妈的大棚就在隔壁,听见动静跑过去时,男人已经疼得蜷成一团,脸色惨白,她还保持着压铁锹的姿势,指甲缝里的泥被挤出来,混着汗滴在地上。 我妈去拉她的胳膊,她手一抖,铁锹“哐当”掉在泥里,这才像突然醒过来,哇地哭了,哭得浑身抽,眼泪砸在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后来医生说,四根肋骨骨裂,不算重伤,加上她身上常年的淤青和邻居们的证词,警察没抓她,只让男的赔了她医药费——那是她嫁过来十年,头回从他手里拿到钱。 村里人说她疯了,一个女人家,下手这么狠。 我妈却总念叨,那天她拉架时,摸到她胳膊上全是老伤,新伤叠旧伤,青一块紫一块,连夏天穿短袖都得用袖子遮着。 “哪是狠啊,”我妈叹口气,“是疼怕了,疼到没处躲了,才敢拿起那把铁锹。” 后来路过他们家大棚,我总忍不住往里看。 男人伤好后再没动过手,见了她就躲着走;婆婆也不骂了,偶尔帮她带带孩子。她还是老穿着那件旧外套,只是袖口补了块新布,针脚歪歪扭扭的,像她女儿缝的。 泥土还是那个味,混着黄瓜藤的清香和塑料膜晒化的味道。 但我总觉得,那味道里多了点别的。 不是铁腥味,也不是汗味。 是一种松快气,像被压了十年的土块,终于裂开一道缝,漏进了点风。 后来我总在想,她举起铁锹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或许什么都没想。 或许只是突然想起,女儿昨天放学时,拉着她的衣角小声说:“妈妈,今天老师教我们画画,我画了个没有爸爸的家,这样你就不会疼了。” 那把铁锹,哪是用来打人的。 那是她给自己和女儿,铲出来的一条生路啊。
老家有个男的以前家暴他老婆,她婆婆也添油加醋嫌她生了个女儿。后来有一次在大棚里干
优雅青山
2025-12-15 13:09:01
0
阅读: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