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跟老公动手打了一架,他扇了我两个耳光,我把他耳朵打出了血,我活了四十多年了,还从没跟人动过手。一度我自己认为自己如果活在战争年代肯定是缩头乌龟,苟且偷生。这一架打完,我觉得自己还挺勇,倒不是说打架多光彩,是突然发现骨头里藏着点硬东西,以前总以为早被柴米油盐泡软了。 结婚十七年,厨房的酱油瓶换了五个,他总记不住拧紧盖子,我弯腰擦了无数次黏糊糊的灶面——以为日子就该是这样,软塌塌的,像泡发的面条。 周三傍晚六点半,客厅沙发旁,他把脏袜子扔在刚换的沙发套上,我说第三遍“扔进筐里”,他头也不抬刷手机:“你顺手的事。” 我把袜子甩他脸上,他猛地跳起来推我一把,“你发什么疯?”我没站稳撞翻茶几,玻璃杯“哐当”碎在地上,像我们之间那些积了又积的怨,突然就炸开了。 他的手扇过来时,我脑子里闪过的不是疼,是二十岁时妈拉着我的手说“丫头,别让人欺负到头上”,然后我的拳头就往他耳朵招呼过去——血珠从他耳廓渗出来的那一刻,我们都僵住了,我活了四十三年,连跟小贩争过一毛钱都要脸红半天,更别说动手打人。 以前总笑自己,要是生在战争年代,肯定是第一个举白旗的,躲地窖里啃红薯,苟且偷生,可现在摸着发烫的脸颊,突然想问:难道真的是我太懦弱吗? 结婚头几年,他晚归我会亮着客厅的灯等,他忘了结婚纪念日我会躲在被子里掉眼泪,后来连争吵都觉得多余——不是不想争,是觉得“算了”两个字更省事,省事到我真以为自己被磨平了所有棱角,把那个会跟男生抢篮球、敢爬树掏鸟窝的小姑娘,叠吧叠吧塞进了衣柜最底层,蒙上厚厚的灰。 直到这一巴掌扇下来,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捅进锁孔,“咔嗒”一声,我才看见衣柜里的自己,原来一直站着,没跪。 现在他睡客房,我们三天没说话,冰箱里的牛奶他喝左边那盒,我喝右边那盒,像两条刻意避开的平行线。 但我不后悔,不是因为打赢了架,是突然看清婚姻里不能只有“忍”,还得有“不”——说“不”的时候,腰杆是直的,比擦一千次灶面都直。 至于以后?等他愿意摘下耳机的时候,或许该说说那些没拧紧的酱油瓶,和我弯腰擦灶面时,偷偷叹的气。 今早做饭,酱油瓶还是没拧紧,黏糊糊的液体顺着瓶身往下淌,我没像以前那样叹气,只是拿抹布擦干净,把它摆得端端正正。 阳光从厨房窗户照进来,瓶身的反光在墙上晃出个小小的光斑,挺亮的——原来软塌塌的面条里,也能藏着一根不肯断的筋。
前几天我跟老公动手打了一架,他扇了我两个耳光,我把他耳朵打出了血,我活了四十多年
优雅青山
2025-12-14 10:08:53
0
阅读: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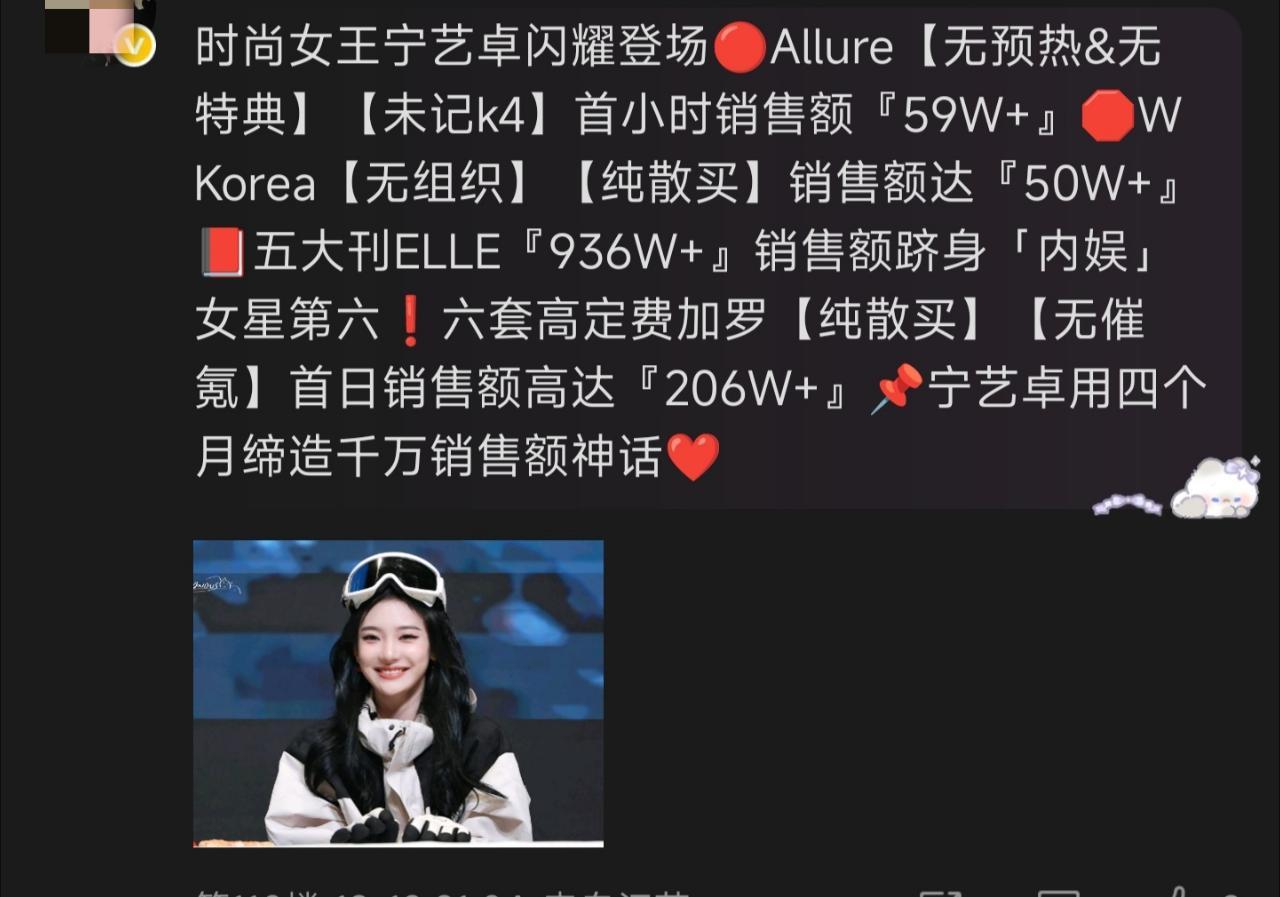




![心疼孙颖莎[哭哭][哭哭]莎莎的脸色苍白,一脸疲惫,这应该貌似是她国际比赛第一次](http://image.uczzd.cn/11941360649611968569.jpg?id=0)

